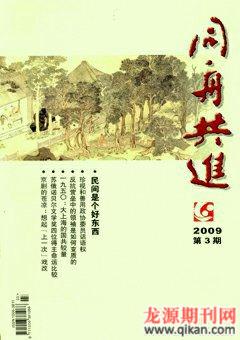1946~1949年邊區土改往事
胡 平

【彭真的擔憂與黎玉的堅決】
1946年夏天,中國各個解放區里地主富農大面積地不安、驚恐,或者擺出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架勢。這源于是年3、4月間,幾位共產黨的高級干部一次赴延安的工作匯報。他們是來自晉冀魯豫解放區的薄一波、來自華中解放區的鄧子恢、來自山東解放區的黎玉等。向中央匯報的中心意思是,如果還在農村實行抗戰時期的減租減息政策,廣大農民是不會滿意的。
1944年11月,在晉察冀邊區的一次報告中,彭真坦言邊區的“減租減息”已開始走樣:當減租減息斗爭充分發動起來后,左傾現象往往立馬抬頭。他所列舉的主要表現是,干部們對地主能否站在民族立場上反對日本侵略者多持懷疑態度;每當國民黨發動反共高潮,邊區部分地主產生動搖,即有部分干部擔心他們將與國民黨里應外合,主張將地主階級徹底消滅;許多干部認為統一戰線土地政策的溫和條文是錯誤的,他們在行動上拒絕接受以減租減息為主要內容的這一政策,或者還按蘇維埃時期的做法,沒收地主財產,允許農民不遵守佃租和抵押合同上的規定,不交租繳息,甚至一筆勾銷舊債,或是抵金未能歸還便索回押地……(胡素珊《中國的內戰——1945至1949年的政治斗爭》,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顯然,彭真是將此視為必須加以制止與糾正的左傾錯誤,而山東省解放區主席黎玉則“理解與支持”農民群眾的革命行動。
山東的許多村莊都實行了一種“七折八翻”的賠償方法:“七”,指過去七年中地主多收的租費或少付的工錢,算出總數后再乘以“八”,即日本鬼子打進中國的年數。如此算下來,有地主因多收20元租費而遭罰8000元,有農民因某年少給4元工錢而獲賠償1000元,甚至被打過一個耳光,也折換成了賠償100元……
地主想守住自己的地不是那么容易的。較典型的是莒南縣澇坡區,經過清算后,全區63戶地主在退出1221701斤糧食、7頭牲畜和537267元錢外,還交出4197畝地。不過幾天工夫,原來的黃世仁變成了“楊白勞”,“楊白勞”們若還錢不上,便只能靠賣地湊數了。到減租減息斗爭結束時,莒南縣許多村莊里已不再有地主,全縣至少有6000戶農民分到了土地。
山東境內,讓地主眉悸心驚的還有批斗和雇工要價獅子大開口,這在某種程度上令生產難以為繼。即使八路軍軍屬中的地主和富農家庭,也沒有享受經濟上的優惠待遇……由于害怕斗爭進一步升級,1944至1945年間,沿海地區有2000多名地主、富農取道海上逃離山東,另外有些人投奔了日本人或國民黨政權及其武裝團伙。多數地主雖留了下來,但一些人的思想并不穩定……
黎玉曾概括這些地主的破壞活動:
利用部分農民認為國民黨不久就會卷土重來的心理,散布謠言;奪回以前賣出或分出的土地;對于農民施以小恩小惠(如借點錢、種子、肥料等),以小利騙取農民的同情,暗中與農民商定不減租或少減租,表面上卻說按政府的規定減了;讓自己的兒子參軍,謀求軍屬的優惠待遇;賄賂村干部,給共產黨員施以“糖衣炮彈”……
對于地主富農惶惶如喪家之犬逃離山東,黎玉并不以為這是農民的過火行為所致。他將“過火行為”分為干部發動的與群眾要求的兩類,認為前一類要注意避免,后一類不但不可避免,而且十分必要。在一次報告里,他說:
如果你害怕群眾的左傾,想要控制他們,不敢發動群眾或給群眾的行動潑冷水,那你就是在向右傾機會主義靠攏。(轉引自胡素珊《中國的內戰》,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減租減息的成功,引發了包括山東在內的一些解放區農民變更土地所有關系的普遍要求。
以華北的晉冀魯豫區為例,據太岳區長子縣6個村的調查,減租減息斗爭結束后,已開始普遍沒收地主土地,“經濟上消滅地主富農”,而且進一步發展到“重重地打擊了中農,他們主張中農不分斗爭果實,只能亦在被推平之列”。(《晉冀魯豫局關于五個月來發動群眾的經驗向中央的報告》,1946年3月26日)
1946年3、4月間,薄一波、鄧子恢和黎玉等人向中央匯報后,由劉少奇執筆起草一個文件,中央又經過多次討論和修改,形成了正式文件。同年5月4日,中共中央以此作為黨內指示下達各解放區,這便是著名的《關于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簡稱《五四指示》。
指示的第一條開宗明義:“在廣大群眾要求下,我黨應堅決擁護群眾在反奸、清算、減租、減息、退租、退息等斗爭中,從地主手中獲得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指示要求各解放區在一場可以預見的大風暴來臨時,不能心口發虛、腳板作軟——
不要害怕普遍地變更解放區的土地關系,不要害怕農民獲得大量土地和地主喪失土地,不要害怕消滅農村中的封建剝削,不要害怕地主的叫罵和污蔑,也不要害怕中間派暫時的不滿和動搖;要堅決擁護農民一切正當的主張和正義的行動,批準農民獲得和正在獲得土地。對于漢奸、豪紳、地主的叫罵,應當予以駁斥,對于中間派的懷疑應當給予解釋,對于黨內的不正確的觀點,應當給以教育……
抗戰時期及勝利初期實行的減租減息政策,已開始轉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或者說,由削弱、限制地主制經濟的政策,變為消滅地主制經濟的政策。
【始料不及的土地政策轉捩】
即便是在黨內也有部分同志對這一轉捩始料不及,包括自由知識分子在內的同盟者更被蒙在鼓里。一年以前的1945年4月,黨的“七大”報告《論聯合政府》中說:
抗日期間,中國共產黨讓了一大步,將“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為減租減息的政策。這個讓步是正確的,推動了國民黨參加抗日,又使解放區的地主減少其對于我們發動農民抗日的阻力。這個政策,如果沒有特殊阻礙,我們準備在戰后繼續實行下去,首先在全國范圍內實現減租減息,然后采取適當方法,有步驟地達到“耕者有其田”。
半年后,周恩來在重慶公開重申:減租減息仍將是抗戰勝利后共產黨土地政策的主要內容,“耕者有其田”和土地國有化留待將來解決。(見《新華日報》1945年10月25日)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在軍事、經濟上占絕對優勢:國統區約占全國面積的76%,有近3.4億人口,控制著幾乎所有大城市和全國絕大部分鐵路,擁有幾乎全部的近代工業,而且有美國的全面援助;共產黨控制下的解放區,約占全國面積的24%,人口只有1.36億,近代工業幾近空白,基本上位于社會發展全面落后的農村,而且沒有外援。
雙方力量至為懸殊外,更重要的還有,飽受戰爭涂炭的中國,在8年艱苦卓絕的抗戰中,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共傷亡2100多萬人,占二戰各參戰國傷亡總數的2/5,財產損失和戰爭消耗折合1000億美金以上。尋求和平維護和平,對休養山河撫慰蒼生有利,對壯大共產黨的力量有利,對贏得國統區廣大的百姓和知識分子的人心有利。
1945年8月底,毛澤東帶著化干戈為玉帛的美好愿望,登上了赴重慶談判的飛機。在重慶冠蓋如云、酬酢紛綸的那些日子里,他通過記者告訴世界,未來的中國將是“自由民主的中國”,在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外,還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及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在場的《新民報》記者浦熙修注意到,重慶的氣候使他不如來時那樣容光煥發,但“他告別詞的聲音由緩而昂,最后使用了渾身力量在高喊”,大約傳達了他眺望中國未來前景的堅定力,宴會在一片“新中國萬歲!”“蔣主席萬歲!”的口號聲中結束……(《山城昨夜綺筵開,毛澤東辭別重慶》,《新民報》1945年10月9日)
周恩來半年之后于重慶發言:“孫中山之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必須順序而進,非可倒置者”,“中國目前為發展資本主義階段,要保護私有財產,十年二十年內絕不可能實行社會主義”——因此,共產黨的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不會改變。

然而,1945年冬天,蔣介石開始踐踏《雙十協定》。1946年上半年,毛澤東已經明白,蔣介石是他同時也是中國革命終生的敵人。和平只是一紙空文,雖“英雄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但首先將和平投入到血泊中去的是蔣介石。
許多歷史研究者認為,對中共土地政策的突然轉捩的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炮火如悶雷一樣已經隱隱響起在地平線上的內戰本身。“共產黨人從未正式宣布戰爭是他們改變土地政策的原因,但他們在1946年開始表明態度,只有土改才能動員農民擁護他們反對國民黨。這一因果關系看起來十分清楚”。(胡素珊《中國的內戰》)
其實,早在1945年底,毛澤東本人已在一篇文章中道破了這一關系——
我黨必須給東北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利益,群眾才會擁護我們,反對國民黨的進攻。否則,群眾分不清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優勢。
(《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
《五四指示》是這一因果關系的邏輯結果。在這一指示作為黨內指示下達各解放區的第九天,《中共中央關于暫不在報紙上宣傳解放區土地改革的指示》便下達了。該指示規定:
在各地的報紙上,除公開宣傳反奸、清算、減租、減息的群眾斗爭外,暫時不要宣傳農民的土地要求、土地改革的行動,以及解放區土地關系的根本改變,暫時不要宣傳中央一九四二年土地政策的某些改變,以免過早刺激反動派的警惕性,以便繼續麻痹反動派一個時期,以免反動派借口我們政策的某些改變,發動對于群眾的進攻。
地主的命運,仿佛成了風向標……
【自由知識分子對國共的“圈點”】
內戰打響之后,1946年7月19日,中共中央下達了《關于向民盟人士說明我黨土地政策給周恩來、董必武的指示》,大意是“向他們說明我黨中央正在研究和制定土地政策,除敵偽大漢奸的土地及霸占土地與黑地外,對一般地主土地,不采取沒收辦法。擬根據孫中山照價收買的精神,采取適當辦法解決之,而且允許地主保留一定數額的土地。對抗戰民主運動有功者,給以優待,保留比一般地主更多的土地”。
不久,中共中央制訂出了一種擬予公布的土地政策,這便是《為實現耕者有其田向各解放區政府的提議》。提議為草案稿,供各解放區討論提出意見。草案稿里,與地主直接有關的政策非常具體,比如:
凡屬地主的土地超過一定數額者,其超額土地,由政府發行土地債券,并以法令征購之……
由地主保留免于征購之土地之定額,由各解放區政府根據各區情況規定之,大概以等于當地中農每人所有平均土地的兩倍上下為適宜……并應注意地主保留之土地的質量,不能全保留好地,亦不能全保留壞地……
凡因實行土地改革而使生活困難之地主家庭,有適宜作公教人員者,政府應酌情錄用之……
今天,將已經下達黨內的《五四指示》與這份擬公布的土地政策對照起來看,后人會有這樣的印象:一邊是以斗爭為猛藥,攻農村之沉疴;一邊是以疏導為文火,消社會之積弊。一邊深文周納,決不掉以輕心;一邊示予外人,詳而備之……
從上述對內對外兩種文件來看,這些暫時還不想讓其知道的人,主要仍是知識分子——準確點說,是投奔了國民黨的右派知識分子與投奔了共產黨的左派知識分子之間的中間派,即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而當時的“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可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大本營。
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不滿并敢于公開抨擊國民黨的專制、腐敗與黑箱政治。從章伯鈞、羅隆基、梁漱溟、章乃器、張東蓀、儲安平、王造時等民盟代表人物身上,后人可以發現,他們身上既有中國士大夫傳統的憂國憂民情懷,又多有人文主義與民主憲政的學養背景。由于他們的存在,蔣介石不得不同時面對兩個戰場——一個戰場上,他被槍林彈雨愈來愈掏空了體力;另一個戰場上,他被越來越沉重的輿論拖垮了心力……
但這并不意味著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共產黨就“不圈不點”。1947年3月8日的《觀察》上,發表了該刊總編輯儲安平的《中國的政局》一文,他像是政治上的風水先生,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民盟在未來的“風水”,均不看好。
抗戰勝利后的這一年來,解放區里斗爭、清算地主階級的繪聲繪色的報道和各種傳言廣為流布,其勢日漸洶洶,不少知識分子開始思慮。
【持續兩個月的和平土改】
1946年上半年,數千名地主,其中多是中小地主攜婦將雛,灰頭垢面,從蘇北解放區逃到了上海、南京,一時間被各媒體稱之為“難民潮”,使得滬寧兩地的許多知識分子日漸相信那些傳言。他們惕懼不安,并作了強烈反應,主要是擔心解放區的農村情形只是龐大冰山之一角。
1946年8月1日,以自由知識分子為智庫的《大公報》發表社論,強調現在全國人民想要兩樣東西,一是想讓共產黨保證履行它在抗戰期間許下的不進行激烈土改的諾言;二是想要國民黨政府貫徹限制私人資本和平均地權的民生原則。
此時,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共產黨是尊重的。這固然因為兩黨對壘中,在共產黨的日益壯大的精神后方,由周恩來聯系著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始終是一支獨步風云的方面軍。此外,在英雄未立、天下失序時期,誠如錢賓四先生所言:
在百萬大軍作國運存亡的大戰爭中,一布衣學者發表一番意見,可以影響整個國際向背,如魯仲連之義不帝秦。(《國史新論》)
如祝勇先生所說:
戰亂與動蕩,幾乎可以使文人與政治家平起平坐,他們身處體制之外,可憑個人意氣干預政治,亦可蔑視政治權力,卻不必受制于體制內的運作。(《英雄何為氣短》)
這年12月,《五四指示》下達黨內大半年之后,陜甘寧邊區公布了《政府征購地主土地條例草案》。依該條例,地主家庭可擁有的人均土地是中農家庭人均土地的1.5倍,超過這一數量的土地都要賣給政府。那些在抗戰期間有貢獻的地主,可以保留兩倍于一般中農人均土地的土地。富農的土地不屬征購范圍。由鄉政府、鄉農會與地主共同商定土地征購價格……
12月24日,新華社延安電訊:在延安以北約160公里處的綏德縣賀家川村,通過政府征購的方式,首次成功地實行了和平土改。從11月25日開始的9天時間里,政府不但結束了征購土地,全村61戶無地或少地的農民,還在邊區銀行的資助下,用7200斤糧食,買到了近1500畝土地,平均一畝地還不到5斤糧食,這遠低于邊區政府自己規定的土地價格,等于白送。那么先前地主賣給政府的,也就等于白送。兩輪白送的土改,自然是和平土改。
充溢著和平空氣的,并不僅僅是賀家川村。據有關資料,在《五四指示》下達初期,各解放區的地主獻田達到了33200余畝。(見《大眾日報》1946年8月24日)獻田的地主中,大抵是三種情況:出身于地主家庭的革命軍人、干部,以力促家里人向農民獻田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場。所謂“識時務者為俊杰”的開明紳士,如走進了《毛澤東選集》的李鼎銘先生。一些地主說蠢也蠢,大浪滔滔已卷去了褲衩,還站在水里捉上衣的虱子——他們只獻出少部分土地,其中多是差地、遠地,保留的土地又以好地、近地居多,或者獻田給關系不錯的個人,期待風頭過后再將地收回來……
新華社電訊里不會再提到的是,這種幾近于兩頭白送的和平土改,大約只開展了兩個月,便在許多地方被批判為右的傾向,1946年10月后就偃旗息鼓了。
【從地主家庭走出來的康生讓地富階層喪魂失魄】
拙著《禪機:1957》(廣東旅游出版社1998年版)里,康生給我的印象如下——
他像是這樣一個人:黨內太平時,他病病歪歪,只有閉門摩挲古玩,或者吟風弄月;黨內一有風吹草動,他便精神硬朗得能在結結實實的水門汀上扎個窟窿。
這次,康生是在1946年12月中旬結束他自延安整風后的沉寂。他帶著7個人,去了離延安以西約160公里的隴東,了解這里的土改情況。在隴東呆了5個星期后,他回到延安,第一次公開露面是在中央黨校。他發表了一篇措辭激昂的演講,批判在整個隴東彌漫著一股對地主妥協與溫和的氣氛,主張喚起民眾,無須劃定任何框框,一切由著農民處理,這樣才能徹底解決土地問題。
次年3月,康生奉命考察山西土改。
康生在晉西北臨縣郝家坡村住了近四個月。他帶來的土改新標準是:第一看歷史,不但要看一個人現在有多少土地、財產,而且要查他家歷史上起碼三代以內的土地、財產及有無剝削的情況;第二看政治,農民的政治表現,集中反映在群眾對其態度里;第三看生活,即要看一個人的家中生活狀況怎樣。
在康生的精心指導下,僥幸沒有被拔高為“地主”、“富農”成分的中農,其地契拿在手里,也隨時可能變成一只飛掉的鳥兒。在晉綏老區,據河曲、保德、興縣三個縣的統計,在土改沒收征收的總土地中,抽動中農的土地一般要占到45%以上,在河曲、保德的部分村子,甚至達到了80%以上。在屬于半老區的五寨、神池、方山、中陽、崞縣、靜樂、朔縣、山陰等8個縣,這個數字平均統計下來,是36.1%。(見《土改整黨中幾個基本數字的估計》,晉綏分局秘書處1948年)
工商業者也受到嚴重侵犯。康生有一個提法:在向地主作斗爭的同時,決不能放過“化形地主”。在他眼里,如同穿破衣服裝窮,地主亦會披掛起一副商人打扮,企圖金蟬脫殼。據晉綏5個分區10個城鎮的事后統計,在原有2603家商號中,“因土改、征收營業稅、懲治經濟反革命擴大了范圍而停業者756家,占總戶數29%”。“最嚴重者,如朔縣農民進城大鬧三天,全市被沒收的500多家中,有240家是正當的工商業”。(《關于土改工作與整黨工作基本總結提綱》,1949年1月30日由晉綏黨代表會議通過)
【蔣介石的最后一線機會被徹底沖垮】
1947年春,胡宗南部進犯陜北。3月18日,中共中央撤離延安,并分為兩撥:一撥為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三位書記,率黨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留駐陜甘寧邊區,指揮西北和全國的解放戰爭。另一撥由劉少奇、朱德兩位書記和一部分中央委員,組成以劉為首的中央工作委員會,經晉綏解放區進入晉察冀解放區,7月初抵達西柏坡,并于同月17日,受中央委托,在此召開了規模空前的土地會議,后被稱為中國共產黨全國土地工作會議。
在日趨激烈的戰爭環境中,召開這次中共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討論土地問題的會議,突出地顯示了土地改革在中國革命中舉足輕重的位置。
會議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其中較能體現其特征的內容有——
“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第一條)
“廢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第二條)即無論大、中、小地主,一般地主與惡霸地主,頑固地主與開明地主……一律沒收私有土地。
“鄉村農會接受地主的牲畜、農具、房屋、糧食及其他財產,并征收富農的上述財產的多余部分”。(第八條)所謂“其他財產”,指來自“砍挖”運動中的地主、富農的浮財和底財。
“廢除一切鄉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債務”。(第四條)一風吹了的,不僅有地主、富農、高利貸者放出去的貸款,還有農民之間的債務,農民與工商業者之間的債務。一般地說,總是貧雇農向中農借貸的多。
“為貫徹土地改革的實施,對于一切違抗或破壞本法的罪犯,應組織人民法庭予以審判及處分。人民法庭由農民大會或農民代表大會所選舉,及由政府所委派的人員組成之”。(第十三條)在土改運動中,貧雇農不但擁有行政權,而且很大程度上還握有司法權。
……
蔣家王朝在大陸生存的最后一個機會,仔細想想,是被全國土地工作會議給嘩嘩地沖進了馬桶的。
這次會議后,一些口號響徹大江南北:“解放軍打到哪里,我們就支援到那里!”“前方需要什么,我們就送什么!”
據不完全統計,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至少有260萬以上分到土地的農民參加了解放軍,保證了我軍源源不斷的兵員補充。此外,協助野戰軍和地方武裝作戰的民兵,也達到了220多萬人次。
日后,高級將領們這樣贊嘆農民對于解放戰爭的貢獻:“我軍勝利的主要因素,在于我軍士氣日盛。這是因為我們是正義自衛的戰爭,士兵都是翻了身的人民,他們為保衛他們的翻身果實而戰,因此在戰斗中莫不奮勇向前,以一當十。”(劉伯承語)“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陳毅語)……
【毛澤東認定:左傾思潮已成為土改的主要危險】
這次會議閉幕前,劉少奇作了結論報告。其中一個非同小可的意見是,在分析以往土地革命未能徹底的諸種原因中,“黨內不純”被視為首要的、“帶基本性質的原因”。報告稱:
縣以上干部,地主、富農家庭出身者占很大百分比;區村干部及支部委員里,中農是主要成分;中農、貧農出身的區村干部,完全不受黨內黨外地主、富農影響者不多;老根據地地主、富農,完全與我干部無親朋聯系者,幾乎沒有;本地地主、富農出身的干部,在土改中多少不一對地主有些包庇……地主、富農出身的干部,好的也有,毛病不多一般還好者也不少,但在土改中他們大多同情地主……
(劉少奇《關于土地會議各地匯報情形及今后意見的報告》,1947年8月4日)
“出身”,這是該報告中用得最多的一個詞。但看干部是否可靠只看他的出身,此種方法大可商榷。
1953年,高崗在他寫的一份被認為是具有詆毀性的材料里,透露劉少奇出身于湖南寧鄉縣一個破落地主家庭,但在1951年土改時,劉的家庭成分被定為小土地出租。劉少奇即使是出身于地主家庭,相信人們也決不會懷疑他歷來堅定捍衛革命的原則性與純潔性,會因此而減弱幾分……
康生原名張少卿,也出身于地主家庭。其父張發祥,有土地一千余畝,橫跨山東省南部的膠縣和諸城縣。父親還討了一名小妾。張家設了一名賬房管收租事宜,一名仆人跑腿,一名長工種蔬菜,此外,還雇了五名婦女烹調洗曬,以及照料服侍康生和他的三個哥哥……(參見約翰?拜倫、羅伯特?帕克《康生傳》)
正是這位從地主家庭走出來的、飽受溺愛嬌慣的張家幼子,在1946年至1947年間的山西、山東,讓一切聽說了他名字的地主、富農甚至中農,肝膽欲裂,喪魂失魄。
1947年春夏之交,各解放區的土改復查中已經出現的左傾思潮,在全國土地工作會議后繼續蔓延,并在這一年的11、12月間,達到了頂點——
雖然在《中國土地法大綱》里清楚寫明,鄉村中一切土地,“按鄉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但各解放區在分配土地財產時,無一將地主、富農與農民同等對待。前者分到手的土地,不是比后者少,就是土地質量貧瘠,位置偏遠。在許多地方,土地的占有形態變成了“倒寶塔形”,即貧雇農占地最多,最好。中農一般。地主、富農最少、最次。
然而,有地可分、還能夠靠勞動吃飯,吃不了干飯能喝上一碗粥的地方,便是地主、富農的香格里拉了。在另外一些地方,“對地主實行‘掃地出門……甚至在驅趕時,不讓其帶走任何財產,叫做‘凈身出走”。或者,“讓地主給原來的雇農(也有給貧農的)當長工,說是‘叫老財也嘗嘗咱們過去的苦”……
(張永泉《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更嚴重的是,因為對地主、富農斷其生路,引起了一些地方人心的恐慌,“不僅地主、富農逃亡,而且連中農甚至貧農也逃亡。例如在晉綏的懷仁三區,全家逃亡和個人逃亡的有128戶,其中,中農就有86戶;左云三區逃亡234戶,其中,中農就有92戶,貧農17戶”。(《晉綏五分區代表團關于土改整黨工作綜合報告》,1948年10月)
此種混亂局面大約一直延續到1948年1月。本月里,毛澤東起草了《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認定左傾思潮已成為各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的主要危險。據此精神,任弼時代表黨中央,在西北野戰軍前線委員會擴大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講話闡述了六個問題:一、根據什么來劃分農村階級;二、應該堅定地團結全體中農;三、對地主、富農斗爭的方法;四、對工商業政策;五、知識分子和開明紳士問題;六、打人殺人問題。該講話全面闡明了正確的政策,頗為尖銳地批判了各種左傾錯誤,此后經黨中央批準,作為指導土地改革的正式文件印發全黨。“對提高大家的政策水平,糾正土改中‘左的錯誤傾向,保證土地改革的健康進行,起了重要的作用”。(江澤民《在任弼時誕辰九十周年紀念座談會上的講話》,原載1994年4月25日《人民日報》)
隨著“平津戰役”的勝利,1949年的春節來到了。
在中國南北方的農村,每到春節,都流行幾副對聯,其中一副最為地老天荒:“土生萬物由來遠,地載群倫自古尊。”
這已是太久遠的往事了……
(作者系文史學者、南昌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