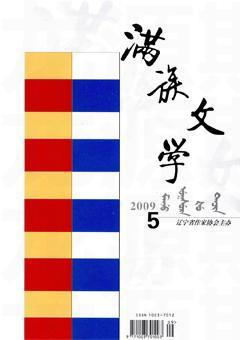關于丹東新時期文學起飛的記憶
[滿族]路 地
關于丹東新時期文學起飛的記憶,雖已時隔三十余年,仍覺清晰如縷。
“文革”十年,猶如一場惡夢。“四人幫”為患,不僅擾亂了社會秩序,也戕害了人們的思想靈魂。他們殘害文人的手段是極其殘忍的。一是羅織罪名,實施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使其致殘致死;再是強制推行“三突出”,“必寫階級斗爭”、“必寫走資派”的謬論,誰敢抵制即遭“批倒批臭”。遂使作家如履薄冰,人人自危,只好罷手停筆,造成全國文壇凋敝敗落。如此禁錮人們的思想達十年之久,歷史上是罕見的。
遼寧的文學形勢也如全國一樣,二十余種文學期刊停辦,作家也都停筆。丹東也是一樣,百花凋零,一片慘象。
新時期伊始,面對這樣令人心傷的局面,應該怎么辦?只能是主動出擊,重新起步。我們的作法可歸納為三個字:“早”“破”“立”。這不是理論的指導,而是現實的需求。
盡早辦起~張文藝報。作者們從十年的噩夢中走出,一時難以辨明寫作方向。在這關鍵時刻,于1978年5月9日辦起《鴨綠江》文藝報,發表新老作者的作品,以為“實驗田”。這在省內是率先之舉。本報在發刊詞中,強調批判“四人幫”,提倡“雙百”方針,提倡“兩結合”,提倡“題材、體裁、形式、風格多樣化”。這一“強調”三“提倡”,在文藝形勢尚未明朗的時刻,并非易事。
園地一經開辟,作品不斷涌來。市屬四縣三區皆有來稿,報紙一派興旺景象。此報由1978年5月9日至1980年7月4日,二年多時間共出26期,共發表作品452篇(含演唱作品53篇),有469人次的作者亮相。可謂一石投下,攪動了一潭死水,涌起文學的清波。于是又抓住時機,于1980年10月,將《鴨綠江》文藝報改為《杜鵑》文學期刊。這在省內也是早的。
盡早舉辦一期大型讀書學習班。1978年10月20日至11月8日,用20天時間,邀20余名青年作者參加。時間長,人數多,學習班應怎么辦?尚無經驗可循。我們要把它辦成一期撥亂反正的學習班。由于“四人幫”將許多書籍誣為“封資修”予以封存,作者長時間無書可讀。即選古今中外一些名著作為課本。如魯迅的《一件小事》、都德的《最后一課》、《話本》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杜鵬程的《工地之夜》、劉心武的《班主任》等二十余篇作品,要求學員認真學習和討論。作者們見書如見親人,爭相閱讀,并集中幾天安排討論。作者如夢初醒,推開了被“四人幫”閉鎖的文學之門,開闊了作者被封閉的文學視野。這是第一步。第二步要求作者“打開生活的倉庫”,讓作者在小會上談生活,有選擇地到大會上講述,幫助安排作品構架。第三步,發給稿紙分頭寫作。對成稿有選擇地到大會上群議群幫,協助修改。在討論過程中,使作者懂得創作必須從生活出發,從生活感受出發,我們稱之為“請現實主義回來”。同時對結構、構思、情節、細節、人物、主題、語言、描寫、開頭、結尾等,一一涉及,灌輸文學基本知識,向文學的本體靠攏。這次讀書會使作者感到異常興奮。共寫出二十余篇作品,效果明顯。此次學習班因是新時期省內首次,《遼寧日報》給予報道。此后,這種學習班每年都舉辦一兩次,有時與報社或縣區文化部門聯手舉辦,逐步將撥亂反正任務及重新振興文學的任務,推向全地區。
發動了一次大討論。編輯部收到一篇短篇小說《婚禮上的花圈》(張甲田著),因文學技巧不高,題目也扎眼,有人不主張發表。但因文中送、受花圈的雙方,都是被“四人幫”扭曲心靈的男女青年,有一定認識價值,決定發表。借“他山之石”發動一次討論。結果來稿較多,共二十余篇,很是熱烈。從中選擇正反兩方面的文稿同期對比發出,共發三期六篇文章,雙方意見已經擺明,批判了“四人幫”,活躍了文藝思想。
盡早辦《鴨經江》文藝報,最早辦讀書班,及時發動一次討論,大破“四人幫”的謬論,大立文學的本真,這幾步是走對了,使我們增強了信心。
1976年4月5日丙辰清明節,廣大群眾為悼念周總理,自發舉行了“天安門詩抄”萬人集會,悲痛之聲驚天。以此為先導,以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運動為動力,相繼在文學界出現了稱之為“傷痕文學思潮”、“反思文學思潮”及“改革文學思潮”。“傷痕文學思潮”是傾訴人們心靈上遭受的深切創痛;“反思文學思潮”是理性地思索產生創痛的社會根源;“改革文學思潮”是表現痛定思痛、奮起創業的革命精神。
丹東新時期文學的起步,基本上與全國文學思潮的腳步相契合。但是丹東是一個地區,不可能呈現三種思潮遞進的形態,只能總體上趨同于全國文學思潮。關鍵詞:“趨同”“全國”“思潮”。
上海《文匯報》1978年8月11日發表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此前有劉心武的《班主任》),由此起步,迅速出現了“傷痕文學思潮”。丹東1978年6月6日在《鴨綠江》文藝報發表王中和的短篇小說《爆發》,表現一位人稱“老镢頭”的老貧農,為反對“四人幫”破壞農村經濟、毀壞兒子前途的罪行,自己寧愿坐牢,也要當面與“首長”作斗爭的悲壯故事。由此打破堅冰,催動了我市“傷痕”“反思”文學思潮的拓展。此類作品,1978年發4篇,1979年發11篇,1980年發9篇,1981年發3篇,共27篇,平均每年發10篇,篇數是可觀的。現依其內容簡要分述如下:
對“文革”的叛離。在毛澤東逝世后的數年間,“文革”仍是個“偉詞”,雖在人們心中對其漸趨否定,但卻沒有見諸文字者。首見文字的是文學。張濤的小說《媽媽石》(見1979年12月《鴨綠江》文藝報),作品寫一個被愚弄的學生,為加入紅衛兵,竟絕情地將“右派”媽媽的“反動言論”給予揭發,由此媽媽被批斗含冤死于山石旁。這個悲慘故事是對紅衛兵運動、亦即“文革”的叛離。這著實是需要膽識的。
對階級斗爭等政治口號的顛覆。小說《五更分二年》(張濤),寫一個愚忠的老貧農在大年夜持火槍出外徹夜蹲守,誤以雪人為階級敵人,以至凍僵(被救活)的故事。《血染的鈕扣》(張濤)中,寫一個善良的姑娘,只因生于富農家庭,硬被誣為“仇恨毛澤東思想”偷竊鈕扣而被打成反革命以至逼瘋(鈕扣被鴨子吞了)。另如愛國華僑的女兒,一個愛國青年,被誣為里通外國而被斗跳樓的《傻子與小姐》(王中和),因學大寨大搞浮夸風,使青年農民致死的《無言淚》(楊楓)等。其他如表現領導干部“民主派”,“五類分子”子女,抓生產的老工人、老貧農,以及作家、畫家、歌唱家等被整被斗的《躲藏的懷念》(佳娜)、《靈魂有影》(宋長江)、《含淚的微笑》(賀業安)、《歌聲》(長詩,羅林)、《懺悔》(汪秀清)等,反映了生活的諸多方面均受到了毀損。
對深重創痛的療救。作家們的思想,并不在“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層面上止步,而是及時延伸,提出了對傷痛予以療救的課題,這是作家的遠見。張甲田的《被追悼者的復活》、張倫基的《大路相逢》,表述的
都是你曾整了我,我又整了他,三方相遇時以“這不是哪一個人的過錯”而消弭前嫌,共同攜手投身“四化”大業。讀之令人振奮。
對“改革文學思潮”的類比。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一發表,就有人呼喚“希望喬廠長到本廠工作”,喬光樸其時風光無限。而我市作家吳文泮的《忍辱負重》的主人公王建樹一出場,卻是“好人被壓”的形象。王建樹是“摘帽右派”,被選為生產隊長,遇到了重重壓力步步坎兒。搞副業就批你“重副輕農”,搞農業機械化就批你“唯生產力論”;公社先是給工廠貼封條,后又把機器給拆毀;妻子鬧離婚,公社搞批判,省里來人整材料……卻始終未被壓力整倒。待他將生產隊改造為由窮變富、名聲遠播時,他已心力交瘁了。還有張正的《夜半錘聲》中的老工人頂住壓力,甘愿夜里干活也要完成定額,等等。他們都是喬光樸的兄弟,他們都是丹東改革春潮的弄潮兒。
在重大的歷史變革面前,應當如何面對?這是擺在每個作家面前的重要課題。丹東作家對此的態度毫不含糊:敢于面對,敏于捕捉,深于思索,勇于表現,能與全國的文學潮流同步。他們做得很優秀。
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發布粉碎“四人幫”的通知;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1979年初,全國第四次文代會召開;
同年召開全國編輯工作會議……
中央在肯定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的批判價值之后,及時提出作家不應沉湎于悲痛之中,而應振奮起來,給讀者以向上的精神力量。
對此,我們立即著手轉型。轉型對我們并非難事。從辦《鴨綠江》文藝報起,對發表的作品,就有所“配置”,以免顧此失彼。此間共發表二百余首詩,五十余首歌曲。都是歌頌型的;另有《挑糞大嫂》(張其卓)等5篇報告文學,還有評論23篇,皆為批“四人幫”,談文學、評作品的文章。所以說轉即轉。從1981年5月《杜鵑》第3期起,轉入正軌。本期重點發表反映工人生活的《架子工與紅衣女郎》(張言軍)并同期加評,以示提倡。另有軍事題材的作品及報告文學等。同時組織作者深入農村、工廠采訪,寫報告文學和詩報告,連發二個特輯。由于及時采取措施,端正刊物方向,提高了刊物質量,多次受到省市有關部門的肯定和表揚。
我們還辦過一種不花錢的學習班。利用每周晚上兩小時,邀市內作者二十余人,一起讀書討論。根據國內文學界短篇不短及我市作者泥實于故事的問題,學習班所定主題為:研討小說的精短和倡導空靈。共用十余個周末,收到了效果。作品在刊物上發了三個“小小說特輯”。上海有二位編輯來丹東讀了“特輯”后說:“中國水平”。
1986年經省、市委宣傳部批準,將《杜鵑》改刊為《滿族文學》,并將市級刊物提為省級(先為省民委、后為省作協主辦),國內外公開發行,實屬特例。
如果,文學老人有年齡,大約十年左右為一個年齡段。“文革”十年,彼長此消;新時期頭十年,此長彼消。然而,后者要付出成倍的努力。
文學的進程是需要導引的,導引得順乎規律,必然走向繁榮。否則將會減速。
作者是需要培養的,既需要班會式的授課,更需要個別輔導,以促使作者梯次成長。培養作者不力,則會減員。
丹東文學創作形勢于八十年代中出現了高峰期,各層作者達七八十人,創作勢頭正盛。涌現張濤、王中和、于德才、林和平、王金力、王鳴久、張忠軍等作家,走向國內文壇。丹東文學成就,位居遼寧文學界的前列。評論家李作祥在《丹東文學風景素描》一文中說:“一派生機,令人刮目的丹東文學風景”,“整個遼寧文壇,已經明顯地感到并清晰看到了丹東文學風景的光彩了”。
幾點體悟:
一、遵循市委正確的領導。丹東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李長仁,在《為杜鵑培土澆水》一文中指出:(1)“要繁榮創作,關鍵在于解放思想”,“沖破陳舊腐朽的東西”,以適應四化建設的需要。(2)“把握時代的脈搏,反映人民的意愿,是文藝的天職”。強調文藝工作者要“發揮個人才智,鼓勵不同的創作風格”,以滿足人民多方面的精神要求。(3)“加強文藝評論,大興爭鳴之風”,“要貫徹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辮子的‘三不主義”。(4)“要刻苦鉆研文化科學知識,深入四化建設的火熱斗爭,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不斷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文化素養和藝術技巧”。領導對文藝工作者提出的指導思想,是正確的、全面的,為廣大文藝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創造了寬松環境,解放了文藝生產力。事實證明,市委對我們新時期伊始所采取的各項舉措都給予支持,使我們感到順風順水,步履輕捷,勇往直前。
這里說說“十七年”(1949-1966)。建國后有百花盛開的春天,創作有繁榮的景象。但自“反右”后,“左”的束縛抬頭了。如只能寫十七年,不能寫歷史;只能寫工農兵,不能寫知識分子;只能寫英雄人物,不能寫“中間人物”;只能寫重大題材,不能寫“家務事兒女情”;寫詩只能寫“大我”,不能寫“小我”等。且一有風吹草動,就從文藝界開刀,一次次的“折騰”,弄得作家謹小慎微,明哲保身。新時期以來,文藝形勢一片大好,文藝工作者精神振奮,思想活躍。但也曾有“評《苦戀》”、“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之風吹來。有的市聞風而動,對刊物實行“自查”,查出幾十條,弄得編輯人員感到緊張,只有等待挨“折騰”。而丹東市委領導說:我們不存在大問題,要求進行自我教育。一句話穩住了陣腳,避免了由于“折騰”所造成的“內耗”。
二、丹東是人杰地靈、出人才出作品的“良港”。丹東的地域文化,大致可歸納為古代歷史文化、江海文化、山林文化、邊疆文化、滿族文化、移民文化(中原文化)等的交融交匯,是一種混合型的地域文化。“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久之使丹東的作家及其作品,浸染著一種率勇、靈秀、樸慧、敏厚的獨特的風格特點,潛流在作家的作品深層。
三、丹東有一定的文學創作基礎。丹東1945年第一次解放,1947年第二次解放,1954年并省,幾經變動,影響了文學發展的連續性。六十年代后,中青年作者隊伍形成,創作水平逐年提高,出現了二個“高坡”。一是兒童文學“高坡”。出版書籍有:吳夢起的長篇《青春似火》,王禾的中篇《隔壁鄰居》、《少年狩獵隊》,李述寬、岳長貴的中篇《大櫓的故事》,王禾、王元喜的中篇《捉狐貍》等。二是短篇小說“高坡”。如吳夢起出版短篇集《楊春山入社》和《方士信的道路》,李光偉、張賢久的《愛》發于《人民文學》,姚翠萍的《高山楓葉紅似火》發于《中國婦女》,還有張倫基的《兩個會計》和《最后出場的人物》等。另有姜士彬的二個組詩發于《詩刊》,李鴻璧的散文發于《人民日報》。其他文學形式的作品也有成就。如唐慶雄的小說,佟疇的詩等。
四、有一個出色的編輯部。我們編輯部初由四五人,遞增至七八人。大多未在報刊作過正式編輯。但他們有熱愛編輯工作的
熱情,有團結奮斗的優良作風。編輯部定有三條:一是作好編輯工作,二是多讀書多寫東西,三是造就個人的正直人格。經過一段實踐,逐步提高了編輯業務能力,都能獨當一面,都能寫作品寫評論,形成了一個“重思想、重藝術、重探索、重韻味”的有統一審美標準的群體。編輯部受到了同行的贊許。編輯部的同志們在丹東這片文學沃土上,都留下了閃光的足跡。
最后說說我自己。我原在省作協《文學青年》、《鴨綠江》任編輯,受過較嚴格的訓練。《文學青年》主編柯夫,是國內一流的主編,能在短短幾年內把《文學青年》打造成與上海《萌芽》齊名的、月發行二十萬份的一流刊物。柯夫要求編輯甚嚴。從組稿、提稿、改稿、校對、發行等,都須“達標”。我是他訓練編輯的受益者,不僅要完成詩歌組(只我一人)任務,還要隨時到小說組、評論組頂崗。我任責編的一篇黑龍江省作者田軍小說《一幅畫》,被茅盾主編的全國青年小說選選中,東北只此一篇,說明茅公對我責編能力的認可。1980年3月在省第三次作家代表會上,我是大會表揚的四個編輯之一。1987年中國作協授予“對我國文學事業繁榮發展做出貢獻”的老編輯榮譽獎勵。再者,當年曾制定一份十年讀書計劃: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西歐文學及文論、文學史等,選其主要者通讀,并做了大量筆記、卡片(“文革”中遺失),閱讀中深入地領會了什么是文學?大致摸索到文學的“四至”,對編輯工作受益匪淺。再次,我有深刻的教訓。“文革”前寫詩近百首,后出詩集時能選人的詩不足十首,其余都是“配合任務”之作。這對一個作家來說是切膚般的教訓。1978年秋,省首次作家集會上,我說了“文藝為政治服務”口號有弊端的話,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對,后也遭到一些有形無形的冷對。我就這么硬頂著。拙詩有句:“我是一棵晚熟的稻子”。“晚熟”也“熟”了,自會明辨些是非,減少些盲目性。1979年初,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上鄧小平致《祝詞》中表明:取消“文藝為政治服務”口號,代之以“二為”。我確有減壓后的喜悅。拙文有云:“新時期十年我是從痛楚地總結教訓起步的,從尋找真誠的自我起步的。從揣摩文學規律起步的。”這就是我投身丹東新時期文學起步時的思想基礎。在撥亂反正的關鍵時刻,除懷著對“四人幫”的義憤之外,還勉勵自己要有熱情,更要有開創精神。我想,我是盡力了。一位市委前領導后來說:“看來路地那些主張還是對的。”這一句話,使我感到知足了。拙文中說:“我任主編,憑知識與業務能力工作,憑公心、正氣工作,多彎腰做事,少沾名利,注重團結,發揮大家的積極性。”當作者叫一聲“老師”時,心頭頓生暖意。其實,我知自身存在缺點,在培養作者的過程中,諸作者的友誼也在重塑著我,友誼長存。1988年8月離休。回頭想想,覺得自己也許是一個“學科帶頭人”,也許是一個及格的“志愿者”。
憑借記憶,資料不足,錯處難免,敬請指出。
2009年2月20日至3月18日
[責任編輯張素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