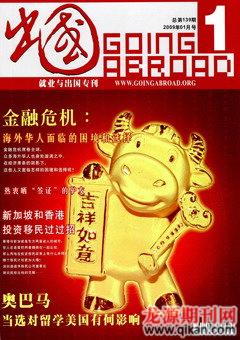品味歐洲之一 蘇維埃的“歷史”絕不可以“預測”
郭 瑩
對于如何執行黨的路線方針,蘇聯人的諷刺是:“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緊跟黨中央的方針路線,一步一個腳印地前進。若原地踏步,那是對黨的不忠誠;若疾步冒進,同樣是得蹲大牢的反動派。”蘇聯人深一步的嘲諷還有:“紅色蘇維埃不僅未來是不可以預測的,更重要的是,蘇聯過往的歷史‘絕不可以預測。”此言怎講?因為前蘇聯的斯大林時代、赫魯曉夫時代、勃列日涅夫時代……每個時期所公布的蘇聯歷史都是截然不同的版本。紅場閱兵式上蘇共中央領導人的合影,今天并排著8位,天知道幾天后同一張照片上,可能僅幸存7位甚至6位了。
前蘇聯時期思想管制之殘暴舉世聞名,各種出版物均受到官方宣傳機構逐字逐句的審查。于是,普通百姓不得不利用口頭文學的方式來宣泄對現實的不滿,蘇聯帝國時代,各類流言及政治諷刺段子滿天飛,不計其數的民眾曾困講或聽政治諷刺而被關入集中營。“什么是最幸福的時刻”諷刺段子,即揭露出生活在恐怖之中蘇聯人的命運。蘇聯人最幸福的時刻,那就是,秘密警察深夜敲門后喝道:“薩沙你被捕了。”主人忙驚慌地辯解道:“薩沙住在隔壁。”
猶太人,在前蘇聯時代的境遇頗為不濟。于是,猶太人的黑色段子是:一位猶太老太婆,每天堅持往政府辦公室申請出國護照。官員被糾纏得不耐煩了,申斥老太婆道:“你為何決意離開我們偉大的蘇維埃祖國,逃到西方去?”老太婆哭訴說:“鄰居每天碰面總惡狠狠地咒罵我說‘等著瞧吧,哪天蘇聯滅亡后,你們這些猶太雜種就會吃二遍苦,遭二茬罪。”官員聽后大笑著安慰老太婆道:“你放心好了,偉大的蘇維埃將永生。”老太婆當即驚恐地聲嘶力竭起來:“這正是我的噩夢。”
還有一則關于蘇聯社會主義大家庭的諷刺。前蘇聯時期,作為小兄弟的越南政府,有天向蘇共中央發報請求經濟援助。電報上書:“我們這里經濟一片慘淡,請求老大哥速拉小弟一把。”蘇共中央書記回電“我們這里同樣捉襟見肘,正在勒緊褲腰帶,你們還是好自為之吧。”電報剛傳出去,下一分鐘即收到越南的回電,只有一行字:“速支援褲腰帶。”越南人氣憤的是,我們這里眼看著斷頓了,蘇聯人居然還配備有褲腰帶,簡直太奢侈了。俄國人嘲笑說:“以往蘇聯與越南千真萬確是兄弟關系,因為朋友可以選擇,而兄弟則無法選擇。”
到了蘇聯帝國強弩之末時代,社會上的政治氣氛逐漸寬松起來,講、聽政治笑話的刑期也由10年減少為5年。最后一任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統治時期,民眾對于第一夫人賴莎的拋頭露面頗不以為然,因為戈夫人之前,蘇共總書記于公眾場合下都是“鰥夫”,紅色蘇聯的第一夫人們皆處于“地下”狀態。于是,民間諷刺段子如下:有人詢問一對夫婦誰在家里說了算。妻子說:“我們家丈夫是頭。”丈夫馬上幽默地應對:“不錯,在家我是頭,可太太是脖子,頭到哪里都得聽脖子的指揮。”
勃列日涅夫的愚人節時代
月亮如今為何混沌不清?蘇聯版的考據是,全因勃列日涅夫感冒病菌的污染。話說當年勃列日涅夫視察升天火箭,患了流感的他,連續啊嚏、啊嚏地沖著火箭唾沫飛濺。結果,載著勃氏感冒病菌的火箭升天后,細菌迅速擴散,導致月亮淪落為“感冒月亮”。
俄羅斯人如此評價前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他是個愚木疙瘩。”及“他是個徹頭徹尾的呆瓜。”
勃列日涅夫于1964年至1982年執掌蘇聯帝國,其翻譯霍德列夫近年出版的回憶錄中提到“勃氏是一個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知識貧乏者,他對于任何事物都采取搪塞的態度。”諸如:“我們將研究研究”或“我們考慮考慮”,成為這位超級帝國元首的口頭禪。若無演講稿,勃氏更是連一句完整的話也吐不出來。
民眾諷刺這位念稿書記的段子有:
勃列日涅夫聽到有人按門鈴,他走到門前,戴上眼鏡,掏出演講稿,高聲照本宣科道:“外面是誰?”門外,勃列日涅夫的親密戰友、波德戈爾內同樣掏出講稿,結結巴巴地朗誦出:“是我,波德戈爾內同志……”
這個笑話還有另外一個版本。勃列日涅夫沒有聽到應答,又朗誦了一遍講稿后,仍舊沒音訊。他不得不打開房門,看到來人后不滿地責問:“波德戈爾內同志,剛才你為什么不應聲?”波德戈爾內驚慌地回答:“我把講稿忘在家里了……”
1979年,勃氏私下會晤美國總統卡特。他如常呆板地誦其準備好的講稿,當念到圈掉的段落時,不知所措的總書記然轉過頭去一臉困惑地請教翻譯道:“我還要往下念嗎?”勃氏的貼身警衛梅德韋杰夫,在其回憶錄中記述了有趣的一幕,蘇共政治局委員要求同總書記保持一致,于是,著裝也最好能同首長如出一轍。1981年11月7日上午9點50分,勃氏踏入列寧墓檢閱臺的休息室,政治局委員及黨政軍要員已恭候多時。勃氏環視向他點頭哈腰的眾官僚一番后發問:“噢!你們都戴禮帽,就我自己戴皮帽!”眾人立即應聲道“總書記,我們這就換上皮帽。”說著,每一位政治局委員立刻變戲法般地頭頂皮帽了。
當年莫斯科奧運會開幕式上,勃氏到場致歡迎辭。倒霉的是,他將秘書撰寫的發言稿忘在大衣口袋里了,待上了主席臺竟然窘得張口結舌,傻呆了一陣后,勃氏終于開口了。不過其歡迎辭相當短促費解,因為他只是連續將俄文字母“O”(讀音“噢”)念了五遍:“噢!噢!噢!噢!噢!”原來,這老兄將奧運的五環標志當成了5個俄文“O”字母。此后,蘇聯人便戲稱勃氏為“O書記”。另次,勃氏的單角相聲獻丑于阿塞拜疆。1982年9月,勃氏到這個邊疆衛星國視察,在阿塞拜疆黨員大會上致祝賀詞。這次勃氏掏錯了秘書為其準備的另一份講稿,當他威嚴地朗誦這份文不對題的講稿時,盡管勃氏自己絲毫沒察覺有何不妥,但臺下聽眾卻對總書記風馬牛不相及的胡言亂語騷動起來。最后,還是秘書趕緊替勃氏換了一份講稿,他才醒悟自己剛才張冠李戴了。
1982年11月10日夜晚,勃列日涅夫如常地服下安眠藥后昏睡起來,這一覺再也沒蘇醒。當警衛人員清晨請總書記起床時,發現他的身體早已僵硬。勃氏跟斯大林一樣,直到歸天,他才總算“因健康原因”“辭掉”黨的第一把手的重任。
檢討文化,作家的慢性自殺
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后,當年即頒發《出版令》,禁止不同政見的刊物出版。1922年成立文學和出版社管瑰總局,全面展開對新聞、出版及文藝作品的意識形態檢查。回顧蘇聯歷史上控制人民思想意識的機構先后有:捷爾任斯基始創的特別委員會(契卡),后有格帕烏(政治管理總局),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部,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蘇聯的文藝政策實行的是胡蘿卜加大棒,歌功頌德者,可以享受優越的政治地位及生活待遇,持不同政見者則被關押或流放。
思想、言論和出版備受之下,蘇聯知識界,逢迎權勢者有之愛惜羽毛者有之;扛枷鎖起舞者有之;揮刀白宮者有之。在蘇聯70年的統治時代,數不勝數的自由思想的載體,識精英,被迫流亡海外。20世紀俄羅斯先后誕生過5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們是:普寧、蕭洛霍夫、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和布羅茨基,其中只有一人即蕭洛霍夫得到官方認可。并于1941年獲斯
大林文學獎。對比之下,其他4位文學家則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蕭氏是否真正是聲名鵲起作品《靜靜的頓河》的原創者,備受爭議。一位白匪軍官太太,就曾公開指責蕭某剽竊了她丈夫的手稿。當然,前蘇聯政府及后來的民主俄羅斯政府,皆對這種指控予以嚴厲的駁斥。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斯捷爾納克,1955年在小說《日瓦戈醫生》寫成之后,寄給了蘇聯的《新世界》雜志編輯部。但編輯部很快退回了原稿,并附了一封措辭嚴厲的譴責信:“你的小說的精神是對社會主義的仇恨……首先是你對十月革命頭10年的看法,旨在說明這場革命是個錯誤,而對支持革命的那部分知識分子來說,參加革命是場無可挽回的災難,并且以后發生的一切都是罪惡……”帕斯捷爾納克,并不覺得自己的作品犯下了如編輯部所指責的錯誤。1956年6月,他把手稿寄給意大利的一位出版商。對方為這部思想深邃的作品所震撼,馬上用意大利語翻譯出版。隨即小說的英譯本和法譯本也在歐美各國風行一時,全世界發出了一片贊嘆。人們普遍認為在《戰爭與和平》之后,還沒有一部作品,能夠在精神上為一個如此廣闊和如此具有歷史意義的時代,作出如此精彩的概括與寫照,《日瓦戈醫生》是一部不朽的史詩。1958年,鑒于《日瓦戈醫生》所取得的藝術成就和世界性影響,瑞典文學院再次考慮授予帕斯捷爾納克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幾經周折,終于獲得通過。但為了淡化時局的影響,獲獎理由并沒有直接提及這部小說,只說表彰他在“當代抒情詩創作和繼承發揚俄羅斯偉大敘事文學傳統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這里的“敘事文學傳統”,即指他的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帕氏獲悉自己得獎后,很快致電瑞典文學院,表達了其喜悅之情:“無比激動和感激,深感光榮、惶恐和羞愧。”
然而,接下來發生的事卻變得十分微妙。莫斯科《真理報》撰文指出:“反動的資產階級,用諾貝爾獎金獎賞的不是詩人帕斯捷爾納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而是社會主義革命的誣蔑者和蘇聯人民的誹謗者帕斯捷爾納克。”一時間氣氛猶如黑云壓頂,那些從未讀過這部小說的人,也開始批判起帕斯捷爾納克。緊接著在11月4日,蘇聯政府授權塔斯社發表聲明,如果帕氏出席頒獎大會并不再回國,蘇聯政府對他絕不挽留。帕斯捷著作家又按官方的口吻進行了檢討“《新世界》編輯部曾警告過我,說這部小說可能被讀者理解為,旨在反對十月革命和蘇維埃制度。現在我很后悔,當時竟沒有認清這一點……我仿佛斷言,一切革命從一開始在歷史上就注定是非法的,十月革命也是這種非法的事件之一,它給俄羅斯帶來災難,使俄羅斯的精英和知識分子遭到毀滅。”
法國存在主義文學家加繆曾評論說,《日瓦戈醫生》這一偉大的著作,是一部充滿了愛的著作,它并不反蘇,而是具有一種普遍性的意義。英國幾十名作家聯名表態:《日瓦戈醫生*是一部動人的個人經歷的見證,而不是一本政治文件。小說之所以在理解上引起人們這么大的分歧,可能主要是由于帕斯捷爾納克堅持個性化寫作的結果。他不服從于任何政治觀念,只追求以自己的理性判斷來反映個人的生活,因而被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教條下的蘇聯政府所不容。帕斯捷爾納克的委曲求全終于起了作用,加上世界輿論的幫忙,他得以留在自己的祖國,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小村莊里,直至1960年5月30日病逝。
對于一個看重人格的知識分子來說,他的檢討無疑開始了一場慢性自殺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