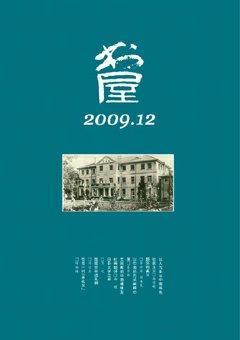“正常時代正常人,非正常時代非正常人”
眉 睫
許君遠(1902—1962),河北安國人,現代作家、著名報人、翻譯家,1928年畢業于北京大學英國文學系,與廢名、梁遇春、石民、張友松等同學。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北平文藝界較為活躍,經常在《現代評論》、《新月》、《北平晨報》、《華北日報》等發表小說、散文、文藝雜談,深得丁西林、陳西瀅、楊振聲、沈從文等人賞識,被一些文學史家稱為“京派代表人物”。后轉入報界,深得張琴南、陳博生、張季鸞、胡政之等稱贊、提攜,先后在《北平晨報》、《天津庸報》、《大公報》、《文匯報》、《中央日報》等擔任編輯、編輯主任、副總編輯,為《大公報》第二代中高層負責人之一,也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代表,曾一度在北平中國大學、上海新聞學校、暨南大學擔任講師、教授。1945年曾以《益世報》特派員身份參加聯合國成立大會。1946年至1953年,擔任上海《大公報》編輯主任、資料組長。1953年后在上海四聯出版社、文化出版社、新文藝出版社擔任編輯室副主任等職,著有小說集《消逝的春光》、散文集《美游心影》,譯有《斯托沙里農莊》、《老古玩店》等,主要作品后人輯為《許君遠文集》(許杏林、許乃玲編)、《許君遠譯文集》(許乃玲編)等。
許君遠因他的興趣愛好、知識背景和人生歷程,而成為一個作家、報人和翻譯家。在這三個方面,他都堪稱自成一家。只不過,當作家是他的夢想,當報人是他的工作,而當翻譯家是他的業余愛好。
作為作家的許君遠,生前出版有小說集《消逝的春光》和散文集《美游心影》等。《消逝的春光》里的小說大多具有鄉土味,反映故鄉的人情、風物,極具新文學草創時期的某些深厚、樸素的味道。《美游心影》既有普通游記的藝術感,又融入了一個中國記者的觀感,非常具有“通訊”的特色。同時,許君遠還有不少抒情散文、游記小品,也自具一格,頗可一讀。此外,許君遠還有一些散文非常接近“梁遇春體”,很見他的性格、情趣。
作為報人的許君遠,曾寫有大量“特寫”、“時評”、“通訊”等,可以說,這些文章是他的本職工作。遺憾的是,許君遠的這類文章,終其一生不曾結集出版。而許君遠對他的一些新聞作品還頗為自得,他曾說:“我采訪表面上的社會新聞,并訪問一些學術與慈善機構,寫為報告式的‘白描。最初原是一種試驗,不意《世界日報》、《小實報》也競起模仿。在抗戰軍興以前,‘特寫文章遂蔚成風氣,始作俑者應該是我。”因此,收集許君遠的“特寫”、“時評”、“通訊”等,結成《許君遠新聞作品集》出版,或許也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
作為翻譯家的許君遠,至少翻譯出版了四種著作:《印度政治領袖列傳》(內中甘地、尼赫魯的傳記系許君遠個人創作)、《斯托沙里農莊》、《老古玩店》、《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都曾風行一時,廣為流傳。其中,《老古玩店》影響最為巨大,版本也最多,至今仍在印行。目前,還有學者專門寫論文研究《老古玩店》的翻譯特色和影響,可以說此書洵為經典譯作。《斯托沙里農莊》(原版為豎排繁體本)經由筆者整理,易名為《北斗星村》,列入“中外百部兒童文學經典系列”,即將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此外,許君遠還有不少單篇或短篇的翻譯作品,已由許君遠之女許乃玲整理成《許君遠譯文集》(內容較為齊全)。1949年以后,許君遠的散文、小說以及新聞作品,都不曾出版或再版,然而他的翻譯家身份,以及他的翻譯作品卻在翻譯界留傳了下來。
以上或許屬于編者“自話自說”。且從其他方面讓讀者來了解許君遠其人其文。許君遠曾在1942年5月寫下《五四之歌》。在那個特定的年代寫出這樣的詩歌,在許君遠一生的作品當中是不多的。我們從中可以看出他對“五四”的深厚感情。許君遠作為“五四”時期的文學青年,可以當之無愧地被稱作“五四之子”。那么,時人又是如何看這個“五四之子”的人和文呢?
1929年春至夏,許君遠在河北省立第十師范(即通縣師范)擔任教員,時張中行在該校讀書。后來,張中行在《流年碎影》中回憶說:“他是英文教員,名汝驥,安國縣人。我沒聽過他的課,可是印象卻不淺。來由還不少。其一,他長得清秀,風度翩翩,一見必驚為罕有的才子。其二,據說他寫過小說出版,是魯迅給他寫的序。其三,他由南國北返,途經某地,與一妙齡比丘尼相悅,有情人竟成為眷屬。還可以加個其四,是不久前聽唐寶鑫同學說的,是他上課,不知怎么就扯到《西廂記》第四本第二折的‘看時節只見鞋底尖兒瘦,念完,他讓臺下同學想象這鞋底尖兒瘦的形狀,然后寫真式地畫出來。更有意思的是他也不甘寂寞,拿起粉筆,在黑板上也畫一對。這是講課的浪漫主義,我幸或不幸,沒有聽到看到,如果聽到看到,以后進京入紅樓,上林公鐸的唐詩課,聽講陶淵明,就不會感到奇怪了吧?”
那么對于這個“五四之子”的文學成就,有無大作家進行評定呢?且看一例。1935年11月,沈從文作《讀〈中國新文學大系〉——并介紹〈詩刊〉》一文,為許君遠等漏選進《中國新文學大系》鳴不平,文中說:“魯迅選北京方面的作品,似乎因為問題比較復雜了一點,取舍之間不盡合理(王統照、許君遠、項拙、胡崇軒、姜公偉、于成澤、聞國新幾個人作品的遺落,“狂飆社”幾個人作品的加入,以及把“沉鐘社”、“莽原社”實在成績估價極高,皆與印行這套書籍的本意稍稍不合)。”可見,當時許君遠的文學成就,在魯迅等人看來還不能躋身《新文學大系》,但沈從文卻認為他達到了這樣的層次。順帶提一筆,許君遠在沈從文尚未成大名之時,于1928年在天津《大公報》中發表《國畫改革與趙望云》,該文中便稱沈從文是天才。他說:“如果人讓我說誰是中國藝術界的天才,我將不遲疑地回答,在文學有沈從文,在繪畫有趙望云。這兩位怪杰的出身有許多相似之點,人間的疾苦他們嘗到的最深,所以表現出來的也最充實。”
不過,說許君遠是作家,是報人,是翻譯家,并不能概括其人。從許君遠的整個一生來看,他是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而且,他在各種知識分子群體當中,是一個比較耐人尋味的人物。他不是一個革命斗爭型的知識分子(雖然,他也有過一些抨擊社會的激烈舉動),也不是一個消極避世或純粹興趣主義的知識分子。因此,他不是很顯露,也不是很保守。他的存在,可以說是自身影響力不夠,也可以認為是當時的許多知識分子采取的一種較為一般人理解、接受的存在方式。對于自己的人生和所處時代的不斷變化,許君遠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他曾兩次寫自傳,一次是在相對比較自由的時代,一次是在思想禁錮的非正常時代。
1947年,許君遠發表自傳之一章《糊里糊涂地進了新聞界》,文中說:“《晨報》是我的啟蒙學校,《大公報》是我的研究院,……假定我不走這條路子,官場的逢迎丑態也許早把我窒息死,假定我不進《大公報》,則抗戰期間留居故都,也許做了很煊赫的偽新聞官,今天也許被判十年八年的徒刑。便是不做偽官,也許走了李子撝兄的后塵,抱病故都,同愁苦奮斗而死。”
1956年,許君遠又在一份上交的“自傳”材料中回憶道:“在北大讀英國文學,成天鉆在‘象牙之塔里讀小說,寫小說,只想成作家,做教授,除了文學以外,不知道還有另外的天地,這便是我忽視政治的原因。便是在報館,我還是‘興趣主義,總是注意有刺激性的社會新聞,忽視關鍵性的政治新聞。……1946年我重回《大公報》任編輯主任,因為當時恐怖籠罩上海,我對許多進步分子總是特別照顧(如方蒙),對潛伏的特務分子則竭力主張開除。不過我這種正義感是盲目的,只是不滿現狀的一種表現方式而已。而我本人由于不關心政治,總是站在中間偏左(即《大公報》路線)的地位上面。這種政治態度,受胡政之、張季鸞的影響最深。我是研究文學的,對政治不夠關心,但也正是我不屑在國民黨腐敗統治下營謀職位的原因。”
這,是他作為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最真誠、最具自知之明的總結。如果聯系思考當時所謂左與右的選擇、斗爭,許君遠的坦白是非常耐人尋味的。可以說,他真誠地說出了許多知識分子沒有說出的真話。他沒有刻意標榜自己,多么激進,多么“左”;也沒有刻意“矮化”自己,多么“反動”,多么“保守”。當然,許君遠在1949年之后,便立即寫文章歌頌共產黨,歌頌新社會,抨擊資本主義制度和文明,這是他自覺、自然地“適應”新時代。不管怎么說,1949年前與后,許君遠的言行體現的是“正常時代正常人,非正常時代非正常人”。
許君遠在1949年之后便開始自覺、自然地適應新時代,但是如同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總還是有一些不適應感,終于在1957年“大鳴大放”中被“引蛇出洞”,表示向往“自由”,向往1949年以前的《大公報》,對目前的新聞管制環境有不滿。很快,許君遠被《人民日報》稱為“右派急先鋒”。此后他日漸消沉、落默,但他的內心對時代的認識是清楚的,這從他臨死前寫的回憶故鄉人和事的《故鄉》中可以看出來。當然,這也不過是他在遭受扭曲時代的打擊之后,所表現出來的一部分尚未泯滅的真誠、自然的人性,并不是說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有多么偉大、崇高,能夠逃脫時代的牢籠。
在當下的民國文人研究中,經常出現刻意拔高、刻意遮蔽一些知識分子的現象。許多研究者還因為刻意拔高,而對他的研究對象為什么在1948年之后迅速倒向新政權表示不解,進而懷疑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品格。刻意遮蔽、丑化,也是經常的事,仿佛在知識分子群體中有絕對的界線,因此一些文人作家被主觀認定為“反動”、“保守”,尤其是跟隨國民黨或待在淪陷區,以及所謂“附逆”或在日本控制的報刊發表文章的知識分子。如果我們了解了許君遠的人和文,尤其是結合他的許多自白文字,我相信人們會對知識分子這個群體,以及這個群體與時代的關系有新的啟發,尤其對當時左與右的選擇、斗爭有更客觀的認識吧!
許君遠終其一生,是一個善良、正直、勤奮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雖然他沒有磅礴的思想、一流的文學作品和能夠藏之名山的學術著作,但是他作為跨幾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關于知識分子與時代的關系說出許多真誠的見解,也能激發我們以新的視角思索有關知識分子與時代的話題。而且,許君遠還是有一定的挖掘價值的,至少可以為現代文學研究、現代報刊史研究、現代知識分子研究補充一些新史料。這也是我編《許君遠文存》的勇氣。
《許君遠文存》的編纂,以收錄許君遠具有文論價值和史料價值的文章為主,而他的游記小品、抒情散文、中短篇小說等其他文學作品,以及新聞作品等,均不在此書的搜羅之列。之所以做出這種打算,一是因為許君遠的此類文章生前從未結集出版,而是散落在各種報刊中,不少是難以查找的偏僻報刊;二是許君遠家人所編《許君遠文集》,已收錄不少許君遠的散文、小說,但漏收了一些具有文論價值和史料價值的文章;三是具有文論價值和史料價值的文章,較為一般關注民國文壇、報界的讀者所歡迎,同時也可為文學史、報刊史、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研究提供一些參考資料。目前,我們編纂許君遠的這類文字公開出版,或許是符合實際的較為明智的做法。至于《許君遠小說散文全集》、《許君遠新聞作品集》等恐怕要在以后等待時機。
本書正文共分為四卷。卷一以收錄讀書筆記、文藝雜談、前言后記一類文章為主,我們借此可以了解許君遠的才情、學識,其中不少也涉及民國文壇,如評價左翼作家王余杞的長篇小說;卷二收錄外國文藝評介文字,對于了解外國文藝作品譯介入中國的歷史過程或許能提供一些信息、史料;卷三收錄有關電影、戲劇、音樂、繪畫等方面的文字,其中多為評論或回憶民國藝壇,涉及趙望云、熊佛西、衛仲樂、張書旗、沈尹默、汪亞塵等許許多多藝術家,因此顯得材料珍貴;卷四收錄懷人、自傳篇什,透露出大量以前未曾披露的文壇、報界信息,如關于徐志摩、梁遇春、蔡元培、張季鸞、胡政之等人的回憶,同時許君遠所寫的一系列關于北大和民國報界的回憶文字,都是彌足珍貴的第一手史料,這些是此書史料價值最豐富的一部分。需要說明的是,為了反映許君遠整個一生的變化,尤其是許君遠在1949年和1957年前后發生不少微妙或離奇的“蛻變”,經再三考慮,編者仍將作者寫于1949年以后的特殊時期的文章酌量收入,如使許君遠戴上“右派”帽子的《發言二則》、《報紙應當這樣干下去嗎》等,同時也收入許君遠晚年在意志消沉之后的《自傳》等文字。讓讀者自己去體味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如何在時代轉變中自然適應和痛苦掙扎的相互共存。
附錄的十篇回憶許君遠的文章,寫成于不同年代,大致可以窺探各個時期對許君遠的追憶、評價。這些文章的作者既有許君遠的家人,又有許君遠的學生,還有許君遠的同事、朋友等,從各個角度反映了許君遠的文藝成就和精神品格。附錄十一系由筆者所撰《許君遠年表》,總共萬余言,主要內容為許君遠生平事跡和著述版行情況,并盡量收入譜主與文壇、報界有關的文字,以凸顯史料價值。
感謝許君遠之女許乃玲女士提供大量珍貴資料;感謝華東師范大學陳子善教授、廈門大學謝泳教授為此書作序;感謝武漢大學陳建軍教授提供不少文章,感謝王浩天、梁國寅等先生寄來相關資料。當然,還得感謝蔡登山先生提供這個出版的機會。
(眉睫編:《許君遠文存》,臺灣秀威信息科技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