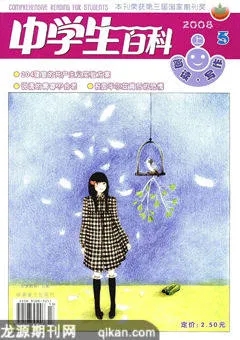欠了春天一束花兒
我和敏是多年的老鄰居,一起玩大的,彼此知根知底,沒啥拘謹。十來年的交往,雖說免不了紅個臉撅個嘴什么的,但一覺醒來照舊嬉戲打鬧成一團。可是,誰也沒料到,高二不久,我們竟翻了臉,而且這一回,我們倆好像都動真格了,拗著性子誰也不再理誰,似有“你走你的陽光道,我過我的獨木橋”的意思了。
小的時候,我不懂何為嫉妒,只是覺得敏很受寵,公主一樣特惹人憐愛。后來慢慢長大,終于領悟“禪機”:敏實在太優秀了,不僅長得漂亮,而且才情也遠勝于我,涓涓文筆宛若其人,常有文章見諸報刊或者拿到各類獎項,至于作文課上,老師更是習慣了挑她的文章當范文在班里朗讀賞析。如此出類拔萃的敏,如此享盡風光的敏,讓我不知不覺在佩服之余有了更多的嫉妒心態。友情天平逐漸失去平衡,為了抬起自己,我也渴望能像敏那樣,讓文章變成鉛字。于是,私下里我更加勤奮了,一篇接一篇不知疲倦地寫,然后偷偷投給校報,甚至不知天高地厚地寄往外面的雜志社。
然而,我所收獲的卻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投出去的稿子無一例外地石沉大海。希望的花兒任我怎么努力,總不見一朵為我綻放,我近乎氣餒了。與此相反,敏卻越來越“囂張”。我固執地認為,驕傲的敏有點兒藐視我。
終于有一天,我的名字印上了校報,這讓我激動不已。不過,我沒好意思將這份喜悅“蛋糕”與其他同學共享,因為敏的存在讓我覺得自己這點成績實在太“小兒科”,拿出來怕人笑話。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折疊好報紙,像慈母呵護自己的嬰兒一樣,又將它平平整整地放在抽屜里,時不時瞟上一眼,幸福無比。
哪知還未等我好好陶醉一番,課間休息時,我出去一趟再回來,卻忽然發現報紙不見了。我大吃一驚,慌忙四下尋找,焦急難耐中總算在廢紙簍里發現了它。那時,它已經被蹂躪得不成樣了,正躺在角落里無助地看著我。我沖過去捧起它,內心一陣刺痛,淚水呼啦一下就掛上眼眶了。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兇手”竟然是敏,是她拿去擦桌凳的,擦完了揉成一團就隨手扔進了廢紙簍……看看“高傲跋扈”的敏,又看看已然面目全非的凝聚著自己心血的文章,我的淚水終于噴泉一樣涌了出來。整個教室的人都呆住了,他們根本無法想象一張報紙與一場痛哭之間有何關系。
整個上午,我都在想:敏憑什么可以這樣粗暴地對待我?就憑她能耐、得寵嗎?還好朋友呢,算我瞎了眼,認識這種表里不一的虛偽的人!我越想越氣憤,簡直忍無可忍。放學后,我攔住敏,拉開陣勢痛痛快快地與她吵了一架,將心里壓抑許久的怨恨都迸發出來了。
我想,如果敏能及時向我道歉,我或許會好受一些,但她沒有,依然以公主式的口吻輕描淡寫地說:“不就是一張報紙嗎?”
就這樣,隨著一張報紙的破損,我和敏漫長的友誼也宣告破碎了。我們倆從此誰也不再搭理誰,一副“老死不相往來”的樣子。可以想象那段時間我的心情有多糟糕,不光為那張報紙,更因敏對我的“無情”。我無法原諒敏,無法原諒她帶給我這么大的傷害。
友情缺失的日子,我孤單了許多,空曠的校園里我常常獨來獨往,從前放學路上爽朗的笑聲難覓蹤跡了,轉而成了我和敏互相躲避的眼神兒。
事過境遷后,我也意識到了自己的過分,畢竟當時敏并不知道那是一張登有我作品的報紙。她是無辜的,霸道的是我。好幾次我都想與敏和好,卻因擱不下面子而遲遲未能主動伸出友誼之手。我們始終就那么遙遙相望著,像兩只受傷后不敢彼此再靠近的刺猬。
時間一晃,臨近畢業了。正值美麗的人間四月天,我們班集體去郊外春游。曠野里云白風清,水綠草碧,蝶舞蜂嚶,陣陣油菜花香沁人肺腑,讓人不覺間忘了一切不快和煩憂。當我們全班三十五雙手緊緊拉成一串,迎著鏡頭展現最燦爛的笑容時,年輕的臉頰上都無比歡欣。無意中,我和敏的目光相遇了,短暫的尷尬后,我們相視一笑。
“這兒真美啊!”敏說。
“是,風景真好!”我說。
“我們……”幾乎是異口同聲,我和敏都說出了“我們”兩個字。我知道敏想說什么,敏也知道我想說什么,無須再多言,一陣沉默后,我們又一齊笑了起來。那時,天空陽光正艷。
田野里溫柔的風暖暖拂過我倆的心田,忽然間,我意識到,其實春天真的不曾走遠,其實友情也始終未曾破碎,只是年少幼稚的我曾欠了春天一束花兒,欠了友情一顆寬容的心。
編輯/李章
- 中學生百科·小文藝的其它文章
- 成長的煩惱
- 我相信你的愛
- 如何與孔雀型朋友相處
- 校園華爾茲背后的恐慌
- 金牛座的星語
- 心動DE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