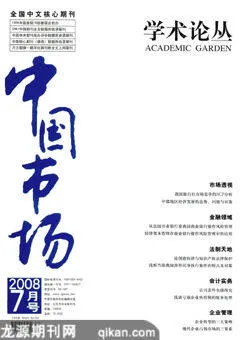論罪刑法定原則的開放性
摘要:罪刑法寂靜原則自其產生以來,在刑事司法保證領域反對罪刑擅斷,保護人權等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隨著時代的進步有人對它提出了質疑。筆者在本文中對其未來如何發展以適應時代的需要做出了分析,我的論述重心將放在這一原則的開放性上。
關鍵詞:罪刑法定原則;開放性;相對性
自刑事古典學派提出罪刑法定原則以來,已經過去了二百多年。在這二百多年里,這一原則經歷了誕生、發展和輝煌的一系列過程,時至今日,我們所處的社會與二百年前相比,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一曾被奉為刑法鐵則的原則是否還具有生命力?或者需要對其進行“軟化”,以適應今天社會的現狀?
一、罪刑法定的含義及我國刑法之規定
罪刑法定原則是現代刑法的特點之一。它反映了刑法的制定和適用都必須嚴格遵循法律規定的要求。[1]19世紀初,P?A費爾巴哈首先用Nullum Crimen,Nulla Poena Sine Le-ge這種格言形式的拉丁語來表示這個原則。在現階段,我們通常把這個原則譯為“把這段拉丁文譯為‘法外無罪,法外無刑’似乎更為準確,因為原文中并沒有與‘明文’并對應的詞。”盡管它的某些淵源可以追溯到更為久遠的時代(特別是1215年英王約翰的≤大憲章≥第39條),但總的來說,這個原則是啟蒙思想的產物。法國大革命時期頒布的一系列法律文獻,最先在立支中為這個原則的現代含義披上神圣光環(最初的如≤人權宣言≥第8條規定:“汗毛只能規定的確且顯然必要的刑罰,不依合法程序適用行為前頒布的法律的規定,任何人不受處罰”)。
從定罪上看,指刑法中未規定為犯罪的行為法官絕不能任意“入人于罪”,這就在罪與非罪行為之間設置了一道門,請注意,在這里我將之喻為一道“門”,而非“屏障”。既然是“門”,證明其有開放的可能性。法官不能“入人于罪”但他是否可以“出人于罪”?即是將已被刑法規定的為犯罪的行為放出門外,使之不為罪?我們知道,一部刑法一旦頒布實施,可能會發生兩種情形:一是某個行為被規定為犯罪,但社會的發展使該行為發生了質的變化,再把它作為犯罪處理,顯然違背公眾的法律倫理觀念,[2]例如我們79年刑法所規定的投機倒把罪;另一種情況是某個行為未被規定為犯罪(可能是由于立法者的局限性或社會的發展變化),但后來發現其對社會具有危害性,與社會整體法秩序不相容。這種情況是無法避免的,因為成文法所具有的滯后性和封閉性與社會的發展變化是一對矛盾。然而,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開啟的門,來對成文法的封閉性加以緩解呢?
我國1997年刑法典第3條明文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罰;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的,不得定罪處罰。”這條規定實質上為罪刑法定原則的傳統含義增加了一項新的內容,即“法有明文規定必為罪,法有明文規定必處罰。”
二、從絕對走向相對
罪刑法定原則已被確立為刑法的“鐵則”,然而,在罪刑法定原則的旗幟下,西方刑法學界對什么是這個原則的基本精神以及如何對待這個原則與類推的關系等基本問題的理解并不統一,而是多元化的。從啟蒙時期的自然法理論到現代的現實主義法學思潮,從古典的法律實證主義到時髦的純粹法學,西方法學史上各種法學流派都力圖用自己的理論對罪刑法定原則的內涵做出自己的詮釋。
根據保障國民的預測可能性與國民主權的原理,要求行為構成犯罪以及受刑罰處罰必須以法律的存在為前提,這便是罪刑法定所要求的法律主義。但是只有處罰行為的法律存在,還不能滿足罪刑法定主義的要求,如根據行為后開始實施的法律(事后法)處罰以前的行為,便是國民不能預測的,因而是不允許的,又如對于刑罰法規沒有直接規定的行為,類推適用某刑罰法規給予處罰的情況,雖然可以說形式上具有刑罰法規的依據,但實質上違反了罪刑法定主義的要求。上述法律主義、禁止事后法、禁止類推解釋,是傳統的罪刑法定主義的內容,被稱為“形式的側面”。
但是現在,罪刑法定主義的內容更加擴大了,即要求刑法的內容適當、正當,不符合這一要求的刑法是違反憲法的,因而是無效的。這就是所謂的“適正處罰的原則”,或稱“實體的正當程序”。被認為是罪刑法定主義的“實質的側面”。[3]這一原則要求,禁止不明確的刑罰法規(明確性的原則)、禁止殘虐劃、禁止處罰不當罰的行為(刑罰法規適正的原則)。其中禁止不明確的刑罰法規,是保障國民的預測可能性,立法原則的要求;禁止殘虐刑與禁止處罰不當罰的行為,是關于犯罪與刑罰的法律內容本身的正當性問題。
就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屬性而言,它傾向于保障人權,實現一般正義和增強社會安全感,可以說,罪刑法定原則是一種價值偏一的選擇,而非兼顧各種價值目標和利益。但是我認為,任何一種原則,或者說任何一項法律制度,都有其利益保護的側重點。都有其主要體現的價值,而不可能面面俱到。在刑法中有多個原則,今后隨需要還會產生其他的原則,現存的原則也可能隨社會的發展而被淘汰。[4] 在些原則是相輔相成的,共同決定了刑法的價值取向,任何一項原則我們都不能因為它沒有概括包容了其他方面就認為它是片面的,是沒有生命力的。而且,從絕對的罪刑法定向相對的罪刑法定過渡的這一過程的本身就體現了該原則內部自我調整和完善的過程,他的“軟化”實際上并沒有背離它保障人權的初衷,而是更有效地實現了這個目的。
綜上所述,我們完全可以說,新的相對的罪刑法定原則更好的適應了社會發展的目標,滿足了刑法的價值要求,他的“軟化”過程也正是他的完善過程,至少到今天為止,它依舊是刑法價值的一根支柱,至少它是否改變了形狀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畢竟,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對適應的原則,而是原則只有適合于自然界和歷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
三、司法裁量——罪刑法定原則開放之途徑
如何認識罪刑法定與司法裁量之間的關系,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貝卡利亞等人的絕對罪刑法事實上主義,是完全排斥法官的自由裁量的,他們將司法裁量與罪刑法定完全對立起來,在這種司法結構中,法官成為一個機械的法律適用工具,沒有任何司法裁量權。我認為, 這兩者之間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它們可以在罪刑法事實上的開放性上找到一個結合點。
我國學者對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權的價值作了以下論證:
1.實現個別正義的手段。制定法是立法者針對普遍的對象就一些共同問題所定的規范,只對社會關系作類似的調整,而不作個別調整,刑法不可能是對具體個人的單獨立法,因而也必須包含著對特殊社會關系的舍棄。這就是說制定法律體現一般正義,對大多數人來說可以獲得各得其所的分配結果。但是具體情況并非總是典型的,相對于典型情況存在許多差異,如果把個別情況與典型情況適用同一法律,必然犧牲個別情況而導致不公正。這就是說制定法在實現一般分配公正的同時,并不能保證每一次的分配是公正的。[5]對個別正義的追求如前所述單靠法律是不能實現的,必須引入人的因素——盡管這種因素是危險的,需要嚴加防范的——因為只有人才能做法律不能做的,能夠度量事物之間的差別并作出適當的裁判。
2.法律靈活性的保證。刑法是制定于過去,適用于現在,規制著未來的行為規范,這一特點決定其具有穩定性,它體現了刑法的安全價值。刑法的安全價值要求把各種行為的法律后果明確于社會,使人們的行為之前即可預料刑法對自己行為的態度,不必擔心突如其來的打擊,從而起到防范權力階層濫用權力的作用。然而刑法適用于現在又規制著未來,它又必須具有適應社會發展的職責。社會生活是發展變化的,要求刑法也應該是發展的,具有靈活性的。排斥靈活性的刑法是僵硬的、凝固的刑法,它同時就失去了生命力,為社會所拋棄。如上所述,刑法的靈活性蘊含于具有穩定性的法律中,而保證刑法靈活性的實現還得引入人的因素,由法官在動作中發揮主觀能動性,因為法律不可能自我調節以實現與發展的社會生活相一致。
3.突變性立法的避免。法律作為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必須為之服務。一般情況下一定社會經濟基礎的發展是漸進的,劇烈的社會震動性的變革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不能成為一種主要形式。社會的漸進發展決定法律發展的漸進性。法律如果不能適應這種需要,勢必阻礙經濟的發展,問題的積累使得法律不進行大量修改甚至廢除重立便無存在的余地。這種突變立法的形式盡管最終滿足了社會的需要,但是,這樣的立法社會震動大,而震動與損失成正比,社會所遭受的損失也大。刑法與其他制定法一樣,它的特點決定其不可能自行漸進的變化以適應經濟基礎的發展,漸進變化的任務主要靠法官來完成。
我同意以上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價值的論述,法官斷案依靠法律,而一部法律要想順利的得到實施也不能離開法官——人的作用。罪刑法定并不排斥法官的自由裁量,而能夠也應當包容司法裁量。法官的自由裁量是實現罪刑法定開放性的重要途徑,承認并重視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也就使法官擁有了開啟罪刑法定這扇大門的鑰匙,在不違背法律的情況下,他可以做出“合情合理”的價值選擇。[6]盡管罪刑法定與司法裁量并不矛盾,能夠并存,但罪刑法定制度下的司法廳裁量是應當受到限制的。因為我們知道法官也是一個普通人,他擁有普通人的理性,也同樣有著普通人的弱點,我們不能要求他具有超凡的能力來辨別真偽、抵制誘惑。
作者單位:河南質量工程職業學院
參考文獻:
[1]陳忠林.刑法散得集[M].北京: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