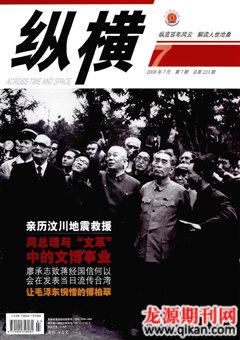正氣堂:吳佩孚為十九路軍題匾
沈 堅

到廣州,必會到沙河頂看十九路軍陣亡將士陵園。這是當年鏖戰淞滬、血灑疆場的數千粵鄉英烈的魂歸地。在陵園內外和紀念館參觀,看到不少歷史人物的題詞,李濟深、陳銘樞、張治中、蔡廷鍇、蔣光鼐、戴戟、胡漢民、林森、宋子文……多是與那場戰爭直接相關的人,或是當時國民政府的執政者。偶見展廳上部還高懸著一塊由民國聞人吳佩孚題寫的橫匾,匾的正中自右往左寫有“正氣堂”三個剛勁有力的正楷字,表達了吳對十九路軍的肯定和贊譽。匾的上款則為“甲戌春月”,下款有“吳佩孚書”字樣和兩方印鑒。
據了解,這塊匾應是當年吳佩孚題贈廣州十九路軍陵園的,后來由于政治風云的變幻,吳匾卻不知怎么流失了。20世紀80年代以后在一戶人家中發現了它,已被主人攔腰鋸作兩半,翻轉來做了他們的飯桌,待重新拼接修復后,才掛在了紀念館的墻上。
吳佩孚系北洋軍閥直系首領,照片為其刊登在美國《時代》周刊封面上的第一個中國人。軍閥混戰,禍亂天下,鎮壓過1923年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殺害了共產黨員林祥謙、施洋,親手制造“二七慘案”。
那么,題匾何以會在廣州的十九路軍陵園現身?吳佩孚這位曾經權傾一時、素來活躍在北方的軍政人物,又怎么會同多由南國粵人組成的十九路軍牽連上的?
1926年北伐戰爭爆發,北伐軍揮師北上,直搗武漢,交兵的對手就是吳佩孚。十九路軍的前身即系當年北伐勁旅——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的一部分(第十師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團),他們同葉挺指揮的獨立團和其他部隊一道,參加了對固守湘鄂的吳佩孚的攻擊。8月27日到29日的汀泗橋—賀勝橋惡戰,吳佩孚親自坐鎮督戰,負隅頑抗,戰況極為慘烈,直至吳軍主力十余萬人被擊潰。10月10日,北伐軍攻克武昌,善打硬仗的第四軍遂得“鐵軍”美譽,吳佩孚兵敗,兩萬人覆滅,就此從權力的巔峰迅速跌落下來,走入他人生的拐點。1927年5月,兵敗失勢的他眾叛親離,一蹶不振,不得不通電下野,西遁四川,托庇于楊森等人。可以說,十九路軍這支部隊堪稱吳佩孚的死對頭,由于在軍事上徹底打敗了他,從而也充當了他的政治掘墓人。
1931年“九一八”事變,東北三省相繼失陷。面對如此危殆之勢,中國各種政治力量無不需要重新調整態勢,因應變局。吳佩孚也就在此多事之秋,離川北返,途經蘭州、包頭等地,于1932年1月末抵達北平。而此時的日軍,又將魔爪伸向上海,觸發了十九路軍奮起抗戰的“一·二八”事變。
早在1919年北京爆發“五四運動”時,吳佩孚尚擁兵遠在南方,隨即以軍旅之身,聯絡61名南北將領向大總統徐世昌發布通電,公開要求北京政府拒簽有損中國主權的“巴黎和約”,并對學生愛國行動表示明確支持,盛贊“其心可憫,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他的這番及時表態,對當時中國政府的外交決策大概是不無正面影響的。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吳佩孚正偏居四川,立即以向日本駐成都領事館發出通電的方式,公然表明自己的立場。他滿懷民族義憤,指斥日本人“前既據我東魯,今又竊我沈陽,人謀雖巧,公理難容”,要其“早日撤軍,免殆戰禍”。電文一出,引得不少西北、西南軍政大員紛起呼應。
吳佩孚北返,甫抵北平,便對時任北平代理軍分會委員長、“世侄”輩的張學良不客氣地予以當面訓斥,責問他在沈陽為何不抵抗,還表示愿出馬領兵,直趨前敵。偽滿開鑼出臺時,他又以個人名義通電聲討,嚴斥溥儀。盡管坊間不乏對他當時或存以“抗日”之名重組軍隊、東山再起之心的揣度,但其時全國的民心向背和大勢所趨,似乎更是決定吳佩孚態度的一個重要動因。
“一·二八”事變,十九路軍剛毅堅定、拼死抗爭。那時不光普通民眾、各界賢達,就連許多中央高層政要、地方封疆大吏,也都紛紛舉行集會,發表宣言、通電,同仇敵愾,表達了高漲的抗日愛國激情。像馮玉祥、陳友仁、唐紹儀、胡漢民、李宗仁、白崇禧、鄒魯、伍朝樞、陳濟棠、程潛、張發奎、孫科、孔祥熙、方振武、張鈁、甘乃光、鄧澤如、熊克武、韓復榘、蔣鼎文、余漢謀、魯滌平、孫連仲、孫殿英、何鍵、朱紹良等,在聲援十九路軍,主張抗日御侮這一點上,無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此刻吳佩孚的想法和態度,同他們是一致的,通過他給十九路軍陵園題匾這一舉動,也足以說明問題。
廣州十九路軍陣亡將士陵園,始建于“一·二八”事變結束后當年的晚些時候。如今我們看到的吳佩孚題匾,標明甲戌春月,當為公歷1934年春。正值十九路軍發起反蔣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敗之后,也是吳佩孚賦閑幽居北平東城什錦花園胡同之時。他晚年似乎沒有再到南方去過,此時題匾相贈,不知是以何種方式送達的。吳佩孚慨然書以“正氣堂”,體現了他對十九路軍的景仰之意,能撇開昔時汀泗橋的夙怨,唯秉民族大義,亦堪為難能可貴。
責任編輯:賈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