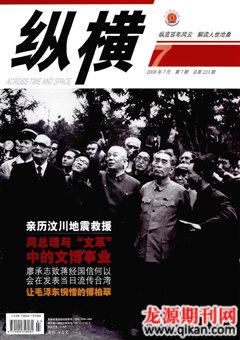走過票證年代
魏章官

如今無論什么商品,只要有鈔票,肯花錢,都能買到。在許多超市和商場,還不用帶錢包付現金,只要遞上銀行卡一刷,即可成交,人們稱之為“一票通”、“一卡通”。
而在計劃經濟年代,特別是在“文革”動亂、越窮越革命的歲月里,直至改革開放初期——尚未根本改變短缺經濟現象的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鈔票并不能包打天下。別說是高檔工業品,就連一些生活必需品,也得票證加鈔票,才能買到。
忘不了1970年我跟隨一位地廳級領導到福州郊外一個山村檢查工作,在深山小道上碰到一位老人,問他對政府工作有什么意見,他說:“沒什么別的意見,就是春節已經過去了一個月,干部還沒把布票發下來。”那時候,城鄉中某些人高馬大者量體裁衣用布多,希望政府不要搞“一刀切”,要給他們多發點布票。為了省錢省布票,我母親穿的兩件上衣的袖子做成“拆裝式”,夏天把長袖拆下成短袖,冬天再把袖子裝上變長袖。我的兩個妹妹在20世紀70年代先后出嫁前,母親為了給她們多做一兩件嫁衣裳,還向左鄰右舍借布票,并約定男方送的聘禮中要有二丈布票。可見,布票對于當時的人民群眾是多么珍貴!
粉碎“四人幫”之后,記得是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有了大量進口日本尿素,其包裝袋尼龍布輕柔耐用,不少人用它做短褲或蚊帳頂,省了布票。我妻子買來尿素袋做了床單和蚊帳頂,那上面寫的“凈重40公斤”、“含氮量保證46%”的幾行黑字,在燈光映照下,仰視看去特顯眼。有人用它做短褲,穿著去山西參觀大寨到澡堂洗澡時,上面“凈重”、“含氮量”等字被外賓看到,成了笑料。后來有了的確涼、滌綸等人造纖維布,尿素袋才失寵,布票的地位與作用也一落千丈,最終布票被取消了,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那年代,廣大農村群眾能享有的票證最多的就是布票。在福建南部沿海甘蔗產區的農民有時還能領到白糖票。肥皂票時有時無,但有些農家無所謂,因為他們用不起肥皂,可用油茶餅洗衣。有些農民對城里人,尤其是機關干部擁有較多票證很羨慕。你看,有糧票、油票、肉票、蛋票、魚票、糖票、酒票、煤票、果糖票、香煙票、香皂票以及搪瓷臉盆票等。在企業單位,工人能獲得不用票證購買、又印上“獎”字的臉盆或牙杯獎品,也感到高興。我家至今還用著朋友送來的1979年他榮獲的牙杯獎品。我1968年大學畢業后先到一個地廳級機關工作10多年,正是票證盛行期。有時還發手表、自行車、縫紉機供應票證,因數量很少,發到處級單位七八十人,這“三大件”才各發一票。單位領導往往把這“三大件”的票證發給工作先進個人,以資鼓勵。
逢年過節前,各級機關單位都給屬下干部職工發放多種副食品票證,平添了節日氣氛。人們領到的有黃花菜票、山東粉票、面粉票、柑橘票、香煙票等。那時香菇、木耳不能人工栽培,是野生的,供應量少,所發的香菇、木耳票,每人選其一,上寫“2兩”。發的酒票有茅臺、五糧液、汾酒、竹葉青、四特、洋河大曲等,用抽簽辦法,每人只有一瓶。不喝酒、不抽煙的人分到煙酒票,也高興地拿了用來送人情。春節票證發得多的單位,簡直被認為“搞特殊化”。平時,肉票最受歡迎。記得1986年的一天我帶肉票一早上街排隊,買的是從四川運來的凍肉。輪到我時,不容挑肥揀瘦,師傅看是3公斤肉票,一刀下去切一塊,過秤時只多幾兩也要切掉。當時機關干部“肚里沒有油,下去游一游;口中沒有味,出去開個會(有吃喝)”,平時在家缺油水,看到買的豬肉,肥多于瘦,真高興!
那時發的煙票,抽煙人不夠用,往往感到苦惱。沒煙抽時,撿自己扔掉的煙蒂剝出煙絲,用稿紙一卷再抽是常有的事。1980年秋,我到《人民日報》送稿件返回時,在首都機場憑飛機票購買兩包鳳凰牌香煙,好高興!買后,只見營業員還在機票上蓋個印,以防旅客用機票重復購買。那時普通干部群眾即使有錢也買不到好煙。有人因此感嘆:“中華大地無‘中華,‘牡丹不向群眾開。‘前門專從后門走,‘鳳凰何時飛下來。”

至于糧票,不知啥時起還成了有價之票。在1980年初,每公斤糧票還可賣到8角左右。1986年,在福建省商店里購買糕餅或進館店吃面條已不用糧票。可這一年6月,我作為一名省報記者出差上海,晚上7點多到賓館住下后,過了賓館食堂吃晚飯時間,只好上街跑老遠找到一家食雜店,想買幾塊面包當晚飯,不料營業員說要用糧票,我要求加點錢頂糧票,營業員很講原則,嚴肅地說:“你想搞不正之風?”我說:“我們福建都不用糧票了,上海大地方怎么還用糧票?”營業員說:“福建、廣東改革開放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上海還沒搞‘特殊與靈活,當然要用糧票啰!我只好跑到外灘黑市買了2.5市斤糧票,再到附近一家食雜店買了面包和餅當晚飯。
從我的人生經歷看,從寄宿學校讀初中,到成家立業后,買的每一件在那時看來比較重要的日用品幾乎都憑票:1960年,我買的第一個搪瓷臉盆代替木盆,是福建古田第四中學發的臉盆票;1970年初,我參加工作后戴的第一塊手表,是用單位領導照顧給我的票、花26元買的南京產“鐘山牌”手表;1979年,我用的第一輛自行車,是憑關系弄到票去指定的縣長樂百貨批發站購買的;1985年,我用的第一臺14英寸福日牌彩電,是一個縣委書記給批條買的;用的第一臺也是最后一臺縫紉機,也是想方設法弄到票才買上,不想后來根本不穿“縫縫補補又三年”的衣服,搬進新居后嫌縫紉機礙手礙腳,送給鄉下親戚了。
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至今,從手表、自行車、縫紉機“老三件”,換成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新三件”,再換成電腦、車子、房子“大三件”,由憑票證和批條購買,到后來取消票證,太方便了!現在,超市店鋪里的商品琳瑯滿目,應有盡有,商家還發愁你不買呢!
票證,是過去搞極“左”、“窮過渡”造成物資匱乏的標志性產物,是溫飽不足的年代體現低層次公平的見證。我想,上了年紀的人都經歷過票證年代,都有我這樣刻骨銘心的感受,都忘不了國家的困難時期和自己生活的艱辛。但現在許多年輕人并沒有這種親身體會,有些年輕人有了新票證——“獨生子女證、小車駕駛證、房產證和績優股票”后,還不喜歡進行今昔對比,覺得昔日的七票八證不可理喻。我們說,有比較,才有分析,才能鑒別,才好看出時代的進步。回顧票證年代,比比如今“一票通”、“一卡通”,可以看到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的巨大變化和成就。小平同志說得好: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責任編輯:王文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