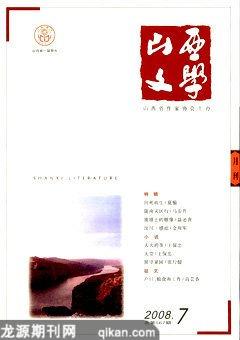這一場跨世紀的馬拉松(同期評論)
段崇軒
早就想給保忠寫一點評論文字了。但一來他創作甚勤,作品很多,要全面評述真要花費些時間和力氣呢。二來我這幾年陷在弄專著的泥潭里,實在無暇他顧。近期《山西文學》要推出他的“作品專輯”,編輯部約我寫一則“同期評論”,任務輕松,正好了卻我的心愿。
近年來,山西青年作家的創作勢頭正健,保忠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整整10年前的1998年,我在《山西文學》做編輯,就“隆重”地給他開辟過“作家小輯”,他在創作談中表達了“一如既往,無怨無悔”地走近鄉村、走近文學的愿望。其實他的出道比這還要早,1994年就在省級刊物上露臉了。如此算來,今年42歲的王保忠,寫齡已近15年之久,這還不算他此前的創作準備和練筆的時間。真是一場路途遙遙的馬拉松長跑啊!15年來,保忠不斷有作品問世,產量不算高,但絕不低。主要是短篇小說,也偶有中篇、長篇,記得他說過:要主攻短篇小說。我和圈內的文友們都很贊賞他的這一志向。因為現在短篇小說不大景氣,很多中青年作家都有,最疏遠這一文體了。現在有作家不計“功利”,孑身“投奔”,這種精神首先就感動了你。但在1994年之后的十幾年間,保忠寫呀、寫呀,卻總是默默無聞,發了就發了,并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有道是“天道酬勤”,2004年的《張樹的最后生活》,先在《小說選刊》轉載,引來了人們的注目,隨后又在“2004——2006年度趙樹理文學獎”評獎中獲得短篇小說獎。王保忠悄然崛起了。2007年在省級刊物發表的《前夫》、《美元》、《長城別》等,接連在《小說月報》、《小說選刊》、《新華文摘》等權威選刊轉載,標志著王保忠的創作已然突破,進入了一個超越期。我為他的執著敬佩,也為他的進步高興!
我常常覺得,文學這一行其實就是一場無形的馬拉松競賽。在漫長而寬闊的跑道上,總是擁擠著眾多的、一代一代的作家。每代作家起步時,總是成群結伙,但跑著跑著,就不斷有掉隊的、受傷的、改行的,最后所剩的就寥寥無幾了。而堅持到最后的那幾位,倒不一定是靠了才華、修養之類,而往往是憑了一種信念和精神。我和保忠相識已久,十多年前他就是《山西文學》看重的“新生代作家”了;但交往不深,我至今不大知道他的個人情況。但在與他的短暫接觸和他的作品中,我感受到了他的身上和心里那些感人至深的東西。他不是那種才華橫溢或者學養豐厚的作家,而是屬于那種踏實苦干的功夫型作家。他質樸、厚道、溫和,說話做事有點蔫蔫乎乎的笨勁,但你卻能從中感受到他的真誠、正直和內在的聰慧。就像一塊“牛皮糖”。他出身農民家庭,未經過很正規的大學教育,又蝸居在雁北一個小縣城,能夠15年如一日地堅持到今天,走向全國文壇,依憑的正是一種對文學的堅定信念和不屈不撓的探索精神。有人說文學是愚人的事業,笨人王保忠終于在馬拉松競賽中奪得了第一輪好成績。
1990年代中期,山西更年輕的可以稱之為第五代作家破土而出,這批出生在以1960年代為主體的作家群,陣容不小,素質也較好。但十幾年時間過去了,厚積薄發的葛水平遙遙領先,發憤努力的李駿虎碩果累累,重拳出擊的晉原平獨占一域,而王保忠和高菊蕊(其實她起步更早,縱跨了第四、第五代)則憑借“鐵棒磨針”的精神,跨上了一個新臺階。當然,這一代作家還在探索、成長過程中,但他們個體的實績和潛力已經初步顯現。再過10年,這茬作家的狀況肯定是另一番情景,有一點則是肯定的,即陣容會變得更小,但我相信執著的王保忠必定還在其中,或許有了更可觀的成就。一個人發幾篇作品并不難,難得是數十年“不拋棄、不放棄”地矢志不移,并能不斷地超越自己,走向全國乃至世界。
對一個青年作家來說,豐富駁雜的生活就在那兒擺著,各種各樣的藝術方法和手法就在那兒堆著。你要“寫什么”、“怎樣寫”?全靠你的探索、悟性和選擇。保忠在10年前的《走近鄉村》一文中所:“鄉村生活是庸常的,如同我們每天必須忍受的平淡無奇的城市生活”。“但我在小說里拒絕這種庸常的狀態”。“我喜歡涉及庸常的鄉村生活里那不庸常的一面,在我為數不多的習作里,人物往往處于一種非常狀態,悲歡離合就交織其中。我以為在這樣的狀態下,更能見出人物性格、品德、情感的復雜性,而命運又充滿了偶然、殘酷和不可知”。寫出鄉村“庸常生活”中的“非常狀態”,這話自然不錯,這是保忠10年前的“文學觀”。正是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保忠在他的小說里寫了農業文明同現代工業文明沖突下,農村和農民的變化與陣痛,寫了在自然災害(如洪災、旱災)面前,各種農民的行為、性格和心理。這條路子是對的,但它不是保忠自己發現和探索出來的,是很多前代作家蹬出來的。再加上保忠有意強化、故事化這種“非常狀態”,就難免落入“模式化”、“雷同化”的巢臼。看來,即使是具有“普世價值”的真理,也只有經過自己的消化,才會變成有用的東西。“牛皮糖”王保忠沒有停止他對生活、對文學的探究。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多麗絲·萊辛說:“我要找的,是那種溫暖、同情、人道和對人民的熱愛”。這段話給了保忠極大的啟迪,或者說照亮了他的慧心。他在創作談《小說的品質》中說道:“這后一句話非常重要。如果萊辛這獎拿得還有些道理,如果人民可以拆解為一個個小人物,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小說這東西,就要給人以信心,溫暖,同情,關懷和熱愛”。保忠并沒有放棄表現“庸常生活”中的“非常狀態”的宗旨,但這里的“非常狀態”已由外在的社會人生變遷,變為人或者說底層農民精神世界中閃光的真善美的東西了。這種真善美的人情和人性,淹沒在無邊的“庸常生活”里,但它卻是世俗社會的“非常狀態”、希望與光明。作為農民的兒子的王保忠,他對這種深藏的“珍寶”很是諳熟、感受深切,而這又是那些遠離鄉村和農民的作家不熟悉的一個領域。
以一個小知識分子的赤誠之心,零距離地潛入各種農民混沌的精神和人性世界里,從中發現那種原生態的質樸、善良、寬厚、仁愛等美好的東西。用它來點燃世俗生活的希望和生機,抵御現代文明洶洶涌涌的污泥濁水。運用傳統現實主義的典范方法和手法,截取生活的橫斷面,突出大寫的人物形象,并用真誠、細膩、憂郁、幽默的敘事語言,創作出一幅幅精湛、溫情的鄉村圖畫來。這大約就是王保忠的小說特征吧。在《美元》中,那個不諳世事的山村閨女艾葉,賣繡花鞋墊掙來20美元,竟把她拋進了一個令人恐慌的外面世界,城里人的冷漠、懷疑、勾引種種丑行,卻絲毫沒有動搖她純真、善良、堅執的品質和性格。這一形象令人動容。在《前夫》里,作者一筆寫了兩個人物,巧枝和她的前夫。巧枝歷經婚姻的坎坷,但依然自強、自尊、理智、寬厚;前夫由窮光蛋變成煤老板,但真情依舊,為富有仁。作品充滿了濃濃的溫情。在《天大的事》中,新媳婦玉英為家庭和母親計,進城打工做了“雞”,丈夫根子口頭嚷嚷“非要打死她不可”,但心里漸漸理解、寬恕了她,
并精心挑選了大紅的連衣裙,等待著她的歸來。而心知肚明的老媽媽,包好餃子期待著女兒。天倫親情化解著他們的心頭之痛。
保忠的發現是真實的,描述是感人的。但我依然有一種不滿足,就是他對人物的情感態度,是建立在同情和歌頌的基點上的,他對人物的理性觀照,是立足于肯定和美化的前提下的。中國農民當前的精神心理狀態,是需要全面地、深入地去審視的,特別是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無論是理解、贊頌,還是審視、批判,都需要謹慎對待的。這是當下鄉村小說的一個關鍵課題。
短篇小說是一種令人神往的文體,是由于它的精美和高潔;短篇小說又是一種讓人生畏的文體,是因了它的苛刻與法度。現在短篇小說所以不景氣,就是因為它的高難度要求和低效益回報之間的強烈反差,使眾多的作家失去了興趣和勇氣。保忠能夠知難而上,這種精神尤為可貴。更難得的是,他能繼承現實主義短篇小說的優秀傳統方法,寫出一篇篇扎實而精到的短篇佳作來。其實,在短篇小說創作上,山西有著豐厚的資源,老一代作家有趙樹理、馬烽,中年作家有成一、李銳以及王祥夫、曹乃謙等,他們眾多的精品力作和寶貴經驗,很值得我們借鑒。在保忠的創作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多方面的深刻影響來。在小說的藝術表現模式上,保忠采用的是以人物性格為核心的情節結構模式,就是說要找到一個“橫斷面”式的巧妙情節,再以此為內核,一步步地展現出人物的精神和性格來。如《長城別》中寫攝影師趙思藐與模特桑小青來古長城拍照片,構成了小說的基本情節,在情節的推進中,又凸現了巧珍和丈夫這兩位底層青年貧困而充實的奮斗人生,同城里人那種矯情多欲的虛無人生形成了鮮明比照。再如《美元》里艾葉兌換和消費外幣的情節,使我們不禁想到馬克·吐溫《百萬英鎊》描寫的有趣故事,但保忠“反其道而行之”,展現的是一位山村閨女純樸而高貴的人格品質。當然,對今天的短篇小說而言,藝術表現模式已非常豐富了,除情節模式外,還有抒情模式、諷喻模式、象征模式等等。保忠完全可以解放觀念,大膽借鑒,創作出更多樣的小說形式來。在小說的人物塑造上,保忠基本上運用的是現實主義典型化手法,這在今天普遍忽視人物塑造的文壇上,顯出了其獨特的價值。如《張樹的最后生活》,寫一位叫張樹的光棍放羊漢,在他住鎮養老院的最后歲月里,寂寞的內心世界和可憐的人性欲望以及整個生命的被毀滅,讀來令人感嘆和深思。是一個山村老農的象征性形象。此外,其他幾篇作品的主人公形象也很結實、豐富。在小說的敘事角度和方法上,保忠潛心探索,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種路子,就是作者自己化入情節和人物之中,以人物的心理軌速(意識流)為主干,熔故事發展、人物行動、環境描寫等等為一爐,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社會人生,形成一種樸素、流暢、深切、流動的敘事風格。《前夫》、《天堂》突出地顯示了這種藝術追求。但我以為,這種敘事方式也不可濫用,因為它本身就存在著冗雜、瑣碎的局限。不知保忠以為對否?
文學的馬拉松是永無止境的。我希望保忠能靜心讀一些書,開闊自己的思想視野,努力站到更前沿去思考、去寫作。我希望保忠在審美追求上要不拘一格,探索小說的各種模式和寫法,創造出多姿多彩的小說世界來。
責任編輯:陳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