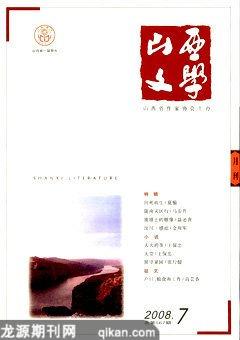小說的品質(創作談)
王保忠
寫了十多年小說,一直在想,什么是小說,小說究竟要表達什么?小說究竟應該有怎樣一種品質?
曾經有朋友說,你的小說都是寫底層的,你小說里的人都是小人物,就不會弄個大題材,寫個大人物?我不知道什么是大題材,什么又是大人物,只知道小說這東西,無論它的源頭,還是開闊處,都離不開小人物。蕓蕓眾生,多還是小人物,我想,人民這個莊嚴的詞匯,說到底就是一個一個小人物的集合吧。小人物寫,寫小人物,寫小人物的小事,平常事,吃喝拉撒的事,高興的事,不高興的事,最后又落實給小人物看,這就是我理解的小說。小說其實很小,不要把小說想得太大,太大就不是小說了。即便你肚子洶涌著喧嘩著很大的聲音,也得往細處說,往小里說。小說說到底就是說話,至于你說的是真話還是假話,甚至大話空話鬼話,那就是各人的追求了。是真佛只說平常事,我喜歡平平常常說話的小說,這就跟我喜歡平平常常的人一個道理。
想想到現在,出現在我小說里的人物,最高級別的充其量也就是個鄉鎮書記。再大的人物,在我的小說里只是一晃而過,只是一個背影或一個手勢,或一個講話,我不熟悉他們,看不清他們,所以還是讓別人去寫吧。說得再直白一些,活躍在我文字里的人不要說級別低,差不多還都是灰頭土臉的,種地的,趕車的,在工地搬磚的,說話又特別土,有時我想,他們會不會普通話?他們這輩子去過星級酒店嗎?他們搓不搓麻將?他們在博客里發文字上網聊天嗎?除了自己的老婆或丈夫,有沒有過婚外情?這還真是個問題。
接著再說小人物需要什么。這個問題其實很可笑,差不多是個偽問題,吃飯,睡覺,生孩子,人該有的欲望他們都有。而且,小人物往往又是最簡單的人,欲望在他們身上也最簡單地呈現出來。那么小說能給他們帶來什么呢?小說這東西不能當飯吃,不能當衣穿,那為什么我們還要生產小說,還有人喜歡讀小說?為什么我們還是要寫小人物,而小人物也還是看小說?或者就因為他們是小人物,而小說在這個喧囂的時代,也灰頭灰臉的像個小媳婦?想想好像不是,至少,他們在小說里能夠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他們的喜怒哀樂,看到他們怎么在這個世上活著。當然,如果你的小說恰好讓他們看了,看了又讓他們覺得這個世界其實還是很有意思的。那你的小說就也有點意思了。
我們總以為小人物很累,很苦難,日子也總是過得緊巴巴灰撲撲的。其實這是一種誤讀,不是這樣,這只是我們的想象。比如我認識的一個鍋爐工,他每天要在鍋爐房工作十幾個小時,還供著兩個孩子上學,這確實不容易,加上老婆偶爾還要嬌氣一下,生點小病。這樣的生活我們一定覺得很苦了吧。可是他卻跳出了我們的“覺得”以外,活得很樂觀。燒完鍋爐,他還要在自家的院子里種點菜,還要寫點東西。他說他寫的東西不一定好,但是他想寫。就這么個人,有時我覺得他比我們過得好,他活得很充實。
忽然想到了一個人,一個叫多麗絲·萊辛的英國女作家,這是一個去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小人物,她比較看重托爾斯泰、司湯達、陀思妥耶夫斯基、巴爾扎克、屠格涅夫、契訶夫這些作家,認為文學的最高峰是十九世紀的小說。而且她這樣說:“我不是在(他們的作品里)尋求對傳統道德價值觀念的再度肯定,因為其中有很多我也不能接受;我不是在尋找重溫舊書的快樂。我要找的,是那種溫暖、同情、人道和對人民的熱愛。正是這些品質,照亮了十九世紀文學,使那些小說表現了對人類自身的信心。我覺得,這些品質也正是當代文學所缺少的。”
這后一句話非常重要。如果萊辛這獎拿得還有些道理,如果人民可以拆解為一個個小人物,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小說這東西,就要給人以信心,溫暖,同情,關懷和熱愛。如果小說只是一堆沒有溫度和光熱的文字,如果寫小說成了個技術活,如果一個文本完成后,在它輝煌的表皮下,裸露出的僅僅是絕望的情感的迷亂,那我們只能說,這樣的小說不要也罷。
如此,小說究竟要表達什么,就好理解了。好的小說究竟需要一種什么樣的品質也就好理解了。順便說一句,即便你寫的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你的小說可能已經具備了一種高貴的品質。
責任編輯:陳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