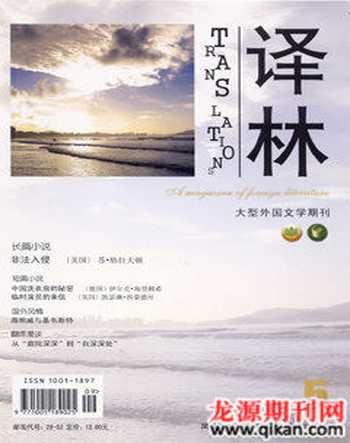“生活是戰爭”:異域文化中的中國經典翻譯
摘要:本文試圖通過趙健秀作品中多次出現的“生活是戰爭”的引言,揭示中國經典在華裔反對種族歧視、重塑華裔英雄形象的斗爭中所起的積極作用,探討華裔在異域認知中國傳統文化的途徑及特點,重在說明翻譯在文化傳播中的作用,以及中國傳統文化在異域的傳播途徑和發展變化。
關鍵詞:趙健秀 美國華裔文學 《孫子兵法》 文化翻譯
趙健秀的作品中經常出現“生活是戰爭”這句引言。該引言出在其散文集《刀槍不入佛教徒》中。在該書的第三頁上,趙健秀指出:“Sun Tzu says:Life is war.War is the state of being the big fuck瞮p.Life or death.The road to glory or extinction.Therefore,before you go to war,study it.Study hard.” (注:Frank Chin.Bulletproof Buddhists & Other Essays.Hawai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8,p.3.) 翻譯成白話文,意思是:“孫子曰:生活是戰爭。戰爭關系到國家命運、生死存亡、榮辱之大事。因此,參戰之前,要先做研究,要用心研究。”但是,在和《孫子兵法》對照之后,發現《孫子兵法》中并沒有“生活是戰爭”這樣一句話。與該段意思最相近的是《孫子兵法》的開篇章《始計第一》中的第一句話,這句話是這樣的:“兵者,國之大器,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注:本文中的孫子兵法全部引自劉伶主編《白話孫子兵法讀本》,白山出版社,沈陽,1995年7月重印版,第3頁。) 而“兵者,國之大器”并不包含“生活是戰爭”之意。趙健秀在《刀槍不入佛教徒》中大段大段地引用《孫子兵法》,多數是直接引語。那么他引用的孫子語錄來自哪里呢? 趙健秀談到中國經典的英文翻譯時說:“最好的和最有權威注釋的翻譯都是美國人做的。羅慕士翻譯的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沙博理翻譯的《水滸傳》(又名《水邊的不法分子》),余英時翻譯的《西游記》,還有新加坡人翻譯的。”(注:The best and most scholarly annotated translations have been American.Moss Roberts,Luo Guanzhongs (Romance of the) THREE KIINGDOMS; Sidney Shapiro (THE WATER MARGIN) OUTLAWS OF THE MARSH,Anthony Yu (U.of Chicago) (MONKEY) JOURNEY TO THE WEST.and Singaporean.——趙健秀郵件,2004年10月3日(保留了趙健秀原文中的大寫)。) 趙健秀在另一封電子郵件中表示不懂中文。2004年,當我告訴他我把通過電子郵件對他的訪談翻譯成中文并在《中華讀書報》上發表后,他回信請我寄一份報紙給他,并說 “抱歉我讀不懂中文,請寄給我一份報紙,我會找人翻譯給我聽。”(注:Im sorry I dont read Chinese.But send me the article anyway.Ill have a friend translate.——趙健秀郵件,2004年2月2日。) 可見趙健秀閱讀中國經典主要是通過英譯本,而美國人翻譯的中國經典在他看來信譽度很高。假如“生活是戰爭”引自美國人翻譯的《孫子兵法》,趙健秀一定認為他引用的就是孫子語錄,而不是翻譯者根據自己的理解增加的話語。趙健秀所說的“孫子曰:生活是戰爭。”應該是從《孫子兵法》的英文譯本中得到的,而英文翻譯者又是從何處讀出“生活是戰爭”這句話的,無從考察。
一、《孫子兵法》之對趙健秀
由于趙健秀認為“生活是戰爭”出自孫子,而孫子又是他十分欣賞的軍事家、戰略家,因此,這句話被趙健秀廣泛引用。在趙健秀看來,這句話不但道出了生活的真諦,而且蘊含著豐富的戰略戰術。“中國人的道德是儒道,它不是建立在基督教這樣的信仰的基礎之上的,而是建立在知識和歷史的基礎之上。生活就是戰爭。在戰爭中要想贏得勝利不是靠你相信什么,而是靠你知道什么。”(注:本文所引《甘加丁之路》均引自趙文書翻譯、譯林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甘加丁之路》。)趙健秀認為,要想在生活中成為勝利者,就需要真才實學。除了戰斗精神,還要有戰略戰術。“生活是戰爭,所有的行為都是策略和戰略……寫作是戰斗。” 趙健秀的寫作致力于顛覆美國文化中消極、怪異的華人刻板形象。趙健秀要重塑華人形象。寫作就是開展一場特殊的戰役。(注:張子清《與亞裔美國文學共生共榮的華裔美國文學(總序)》,《甘加丁之路》,趙健秀著,譯林出版社,2004年,第2頁。)
戰略家孫子對趙健秀的影響非常之大。在《刀槍不入佛教徒》中,趙健秀摘錄了大量的孫子語錄,全書中共有四十段之多,最長的一段孫子原文是一百六十八個漢字,把趙健秀引用的英文譯文翻譯成漢字,漢語譯文長達三百多漢字。趙健秀引用的孫子語錄主要有兩類,一類用來表達他對戰爭的認識,另一類用來表達對要取得勝利就必須具備戰略戰術之重要性的認識。“指揮軍隊作戰的最高境界是使人看不出任何痕跡,因此無論深藏的間諜或是高明的智者都不能謀劃出辦法對付你。”(故形兵之極,至于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孫子語)(注:Frank Chin.Bulletproof Buddhists & Other Essays.Hawai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8,p.11.) “因此,我每次取得的勝利,采用的作戰方法都不是簡單的重復,而是根據情形有無窮的變化。”(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于無窮。——孫子語)(注:同上,p.19.) “戰爭中最難的莫過于制勝的策略。難在要把迂回的路變成直便的路,把不利的條件變成有利的條件。”(莫難于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孫子語)(注:同上,p.15.)
“生活是戰爭”及其他由此而來的趙健秀口號,都深受《孫子兵法》的影響。《孫子兵法》作為中國經典文獻之一,不但影響到趙健秀的人生態度,而且影響到他的創作思想。在美國華裔作家中,趙健秀以言辭激烈著稱。他的作品火藥味十足。他所“引用”的這句孫子的語錄,成為其招牌式口號。與莎士比亞著名的“人生是舞臺,每個人都是演員”相比較,趙健秀聲稱的“生活是戰爭,每個人天生都是戰士”可謂截然不同。趙健秀的口號源于他認為的孫子兵法,源于中國文化。
二、具有美國價值觀的中國英雄
然而,趙健秀畢竟是生長在美國的華裔。美國文化對他的影響要大于中國文化對他的影響。他所塑造的華人英雄形象不可能完全是中國經典文學角色的復制。事實上趙健秀塑造的美國華裔英雄受到兩種文化的影響,是兩種文化結合的產物。趙健秀顯然學到了孫子的機智,因為他用美國文化中的英雄形象來顛覆美國文化中華人的負面臉譜化形象。他的表述充滿美國文化元素,甚至西方文化元素和西方價值觀。他的小說《甘加丁之路》的標題就取自英國作家吉卜林的一首詩“甘加丁”。詩歌描寫一個為侵略印度的英國殖民者服務的印度人。在趙的眼里甘加丁是個民族叛徒。小說的第一部分“創世”講述了演員關曼龍一生最大的愿望是飾演陳查理。陳查理是一個虛構的華人偵探,在1925—1949年間曾先后在五十部電影中出現過,在美國聞名遐邇。陳查理代表了主流愿意接受的華人形象:肥胖,缺乏性感,唯唯諾諾,講蹩腳的英語,滑稽可笑。(注:張子清《與亞裔美國文學共生共榮的華裔美國文學(總序)》,《甘加丁之路》,趙健秀著,譯林出版社,2004年,第2—3頁。) 趙健秀要糾正這種華人形象。趙健秀樹立的正面華人形象和陳查理完全相反。他們英勇威武,極具男性魅力。他們既有中國民間英雄關公的威武外表,也有西方文化中的個人主義精神,從里到外是徹頭徹尾的英雄。在趙健秀作品中,中國民間英雄和美國硬漢形象合而為一,比如,他經常用西方文化中的英雄形象指涉華人:“假如普羅米修斯是華人,他會從諸神那里盜取火種,警告人們撤離城市后焚燒首都,砍下觸怒他的諸神的首級,懸掛于宮殿之大柱上,再一把火將宮殿付之一炬夷為平地。”(注:Frank Chin,“This Is Not An Autobiography,” in GENRE ⅩⅧ ,Summer,1985,pp.110—111.) “我們家的姓是戰神關公的姓……他們說關公是關姓家族中最偉大的人。媽媽說關公就像中國的約翰·韋恩。媽媽的大姐芙蓉阿姨說他看上去更像中國的克拉克·蓋博。”(注:Frank Chin.Bulletproof Buddhists & Other Essays.Hawai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8,p.66.)韋恩是美國電影明星,扮演過許多西部牛仔,塑造了眾多硬漢子英雄形象。蓋博是美國電影演員,在20世紀30年代以扮演粗獷、富有男子氣概的角色聞名。事實上該小說中表現的華人正是富有個性的美國人,而不是陳查理型的華人。有人認為趙健秀對英雄傳統的主張不僅扭轉了黃種人作家的局面——在白人的時鐘上辨認出黃種人的文學時間的尷尬,而且以美國華裔的標準對西方傳統提出了批評。(注:David Leiwei Li,“The Formation of Frank Chin and Formations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Comparative and Global Perspective,Eds..Shirley Hune,etc..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Pullman,Washington.1991,p.220.)但是趙健秀的做法也引起了爭議,被認為是“企圖用一種完全美國的方式,把華人傳統解讀成一種積極的個人主義傳統”。(注:張子清《與亞裔美國文學共生共榮的華裔美國文學(總序)》,《甘加丁之路》,趙健秀著,譯林出版社,2004年,第4頁。)
在趙健秀看來,中國的神話、兒歌、古典小說等民間文學等都是中國文化的記載。了解和記住這些,就意味著了解和記住了中國文化,否則就是不懂中國文化:“我記不清中國是啥樣。沒有一點記憶。記不得一張臉,記不得一個神話故事,連一支搖籃曲也記不得。”(注:Frank Chin.Bulletproof Buddhists & Other Essays.Hawai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8,p.81.) 因此,是否在華裔文學中如實反映中國經典,反映中國神話,是關乎是否繼承中國文化的大事。了解中國經典神話和民間故事,對于趙健秀來說就是繼承中國文化傳統。“任何依附于歷史的,或對歷史有興趣的,或書寫歷史的,或書寫華人移民的任何美國華裔與英雄傳統都有關系。正因為我們首先是帶著英雄傳統到美國來的。每個堂會都是按照《三國演義》的桃園結義的形式組織起來的。最大的聯盟就是梁山泊的一百零八條好漢。”(注:Frank Chin.Bulletproof Buddhists & Other Essays.Hawai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8,p.457.) 趙健秀指出:“一個美國亞裔不知道四大名著,不知道中國的文化,他不會感到惱火,但是一個真正的華裔就會。我是一個華裔,雖然我講英語,但是我從來沒有適應他們的文化,我也從來沒有去迎合或被同化。盡管我比《融入美國》節目中的那些美國華裔更了解基督教徒和白人文化。” 趙健秀問:“華裔作家把所有的作品都看作歷史,以至于每部作品都要作上注釋,標上日期甚至連故事集也不例外。我們知道在朝代和孔子出現之前的中國神話和傳說,我們知道岳飛的生卒年代和歷史事實,我們也知道明代寫成的關于岳飛的英雄傳奇。今天(在中國)人們仍然能讀到這些歷史嗎?有關英雄傳統的作品仍然有賣嗎?——《三國演義》、《水滸》、《封神榜》、《岳飛傳》、《楊家將》、《梁紅玉傳》、《西游記》和《紅樓夢》,在這里(美國)的每一家書店都有賣。”(注:The Chinese writers treated all writing as history and as such dated and annotated everything,including the collection of stories.We know the “Myths and Legends” came before dynastic China and Confucius.And we know the dates and factual history of Yue Fei and the “romantic fictions” of the Yue Fei of the heroic tradition written during the Ming.Are the histories still available to the people? Is the heroic tradition still available—3 Kingdoms,Water Margin,Creation of the Gods,Yue Fei,the Yang Family Generals,Liang Hongyu,Monkey,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eyre available here,in every bookstore.——趙健秀郵件,2003年4月30日。)這里所說的華裔作家顯然是指趙健秀自己。
趙健秀并不是唯一認為神話和傳說等是反映歷史事實的。其他學者也有同樣的認識,比如美國學者Helena Grice:“神話與關于過去的合法版本的歷史、自傳或傳記應該具有同等效力,一般認為話語是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之上的。”(注:Helena Grice.Negotiating Identities睞n Introduction to Asia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 New York:Manchester UP,2002,p.184.) 神話、傳說、民間故事等等是否等同于一個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在離散文化研究中一直是一個重要議題。因為這關系到離散族群對祖籍國文化的認識渠道和離散族群本身的文化建構問題。神話和傳說等等是離散族群認識祖籍國文化的主要渠道之一。“從小耳濡目染,走進屋,你就會看見關公,走進餐館,你還是看見關公,見到桃園結義的三兄弟(筆者在美國觀察到,許多唐人街華裔的店鋪正廳都供奉著關公,關公是他們的守護神)。走進屋,餅干盒上的福祿壽三尊神像,也許是花木蘭像,誘使你打開餅干盒。”(注:Frank Chin.Bulletproof Buddhists & Other Essays.Hawai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8,p.457.) 盡管他們所謂耳濡目染的類似關公的塑像等等,已經是離散族裔化了的塑像。因為這些塑像充盈著離散族群對中國文化的理解、翻譯和改寫,其中加入了許多受到異國文化影響之后形成的想象。這些想象體現了離散族群的希冀、愿望和需求。
最近美國的研究證明,神話在美國已經成為族裔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而受到重視。以下的研究成果較為詳細地說明了美國學者對神話的作用的最新認識:
近年來對美國移民的文化研究提高了對移民作家講述故事方式的重視程度,指出它們已經不再是對移民融入美國社會過程的簡單陳述。沃納·索勒斯、喬·格杰德、馬修·雅格布森、莉莎·露易等學者發現,這些講述改寫了關于“美國”的概念,它們力圖證明移民作為國家成員的合法性。奧姆·歐沃蘭德也加入了討論,以他的《移民者的思維》和《美國身份》兩項研究成果深入探索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歐洲移民如何利用想象建構自己在美國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的地位,并在此基礎上展開他們自己的歷史版本,以申明美國是他們的家園。奧姆·歐沃蘭德注意到一種“從歷史到神話的調適”,指出移民群體的領袖創造出了他稱之為“尋找家園的神話”或故事,證明移民族裔在基因上或意識形態上與對美國象征體系非常重要的人物和事件之間存在的聯系。歐沃蘭德明確列出的一系列的文化文本例證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它們包括虛構的和自傳體的文本,族裔報紙的社論,以及族裔領袖們在宴會和集會上的演講,還有紀念族裔傳統的節日,為族裔英雄紀念碑而舉行的籌資活動等文化活動。他認為這種尋找家園的神話是一個美國現象,因為它們共同的主題和情節超越了族裔分界:對于所有的族裔來說,這些神話都是為了確保他們能被盎格魯主導的社會所接受,同時(也許有些自相矛盾地)確定族裔身份在美國的重要性。盡管專業的歷史學家認為這些故事是幼稚的,甚至是有害于歷史編纂的而對其不理不睬,但歐沃蘭德認為必須嚴肅對待這些神話,并不是因為這些神話的內容,而是因為它們產生的原因。(注:Peter Kvidera.Immigrants Minds,American Identities,American Literature,Vol.74,No.2,p.416.)
由此可以看出,不僅是美國華裔對神話非常看重,其他族裔也同樣如此,其中包括歐洲裔美國人。在大家都是移民的這樣一個國度,每個族裔都要創造出自己的神話,用以申明自己在這個國家的合法地位和權利。這似乎成為美國見諸于各個族裔群體的一種文化現象。美國華裔只不過是用同樣的方式做了其他族裔都在做的事情。
三、中國文化在異域的傳播
趙健秀“生活是戰爭”的來由,以及他對此信條的發揮,從一個方面表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在異域傳播與發展的狀況。離散族群在他們能夠接觸和理解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之上,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取舍。取舍的過程是一個文化翻譯的過程。他們所理解的中國傳統文化中被加入了中國傳統文化不曾蘊含的內容,加入了異域文化的文化價值觀,以及他們認為他們需要在異域文化的語境中必備的文化要素。此時的中國文化主要起到象征的作用,象征著他們的這些思想來自中國,來自中國傳統文化。他們不必了解這些文化文本,甚至可以完全不了解,仍然可以拿它說事。假如“生活是戰爭”不是出自英文翻譯,另一種可能就是趙健秀根據自己的理解或記憶加入到《孫子兵法》中去的。趙健秀有可能和別的一些華裔作家一樣,把記憶、想象和史實全都混在一起,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創作。不少華裔作家對中國文化的表述都充滿了記憶和想象。以趙健秀對中國文革的描述為例,趙健秀的文本顯示了他曾受到中國20世紀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雖然他并沒有親身經歷或間接閱讀相關文本。這在《甘加丁之路》中有不少描述。“盡管他們(華裔)沒有讀過毛主席的《紅寶書》,卻對《紅寶書》深信不疑。” “紅衛兵是我的兄弟姐妹,伙計!” 我對他們說,“我喜歡革命現代京劇。哇! 它們正中我的心坎。”(注:Frank Chin.Bulletproof Buddhists & Other Essays.Hawai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8,p.242.) “……我現在是第三世界革命唐人街先鋒隊——唐人街黑虎隊——的‘權力歸于人民之教育部長。”(注:同上,p.249。)
在海外的趙健秀未必了解當時的文化大革命的背景和內幕,但是趙健秀掌握了當時文化大革命最流行的口號:造反。這正是當時趙健秀所需要的,也是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國華裔所需要的。因此他們會說:“紅衛兵是我的兄弟姐妹,伙計!”,他們會說:“我喜歡革命現代京劇。哇! 它們正中我的心坎。” 盡管他們并沒有真正看過樣板戲;他們沒有讀過毛主席的《紅寶書》,卻仍然 “對《紅寶書》深信不疑”。趙健秀的傳記作者約翰·查爾考·吉休特(John Charcles Gishert) 曾經評價《甘加丁之路》道:“趙健秀至今最長的而且最為復雜的小說《甘加丁之路》,是對現當代美國亞裔的經歷進行全面評價和批評的一部小說。”(注:John Charcles Gishert.Frank Chin, Boise:Boise State University,2002,p.20.)20世紀60年代、70年代是美國華裔文化的建立被提到議事日程的時代,(注:徐穎果,《美國華裔文化——美國語境里的中國文化》,《南開學報》,2005年第4期,第37頁。) 是美國華裔歷史上的重要時刻。《甘加丁之路》作為趙健秀反映現當代華裔經歷的重要小說之一,勢必要反映當時華裔受到的各種影響。趙健秀的造反精神可以說是受到過當時中國紅衛兵“造反”口號影響的。
綜上所述,華裔所理解和表述的中國文化具有三個特點。首先,作為美國華裔了解中國文化重要渠道的中國經典在被異域文化中的人翻譯的過程中經歷了文化翻譯,被加入了異域文化。福勒認為,文化身份不應是唯我論的由文化根源決定的,而是彼此間有密切關聯的,翻譯則是從語言層面說明這種情況。(注:Colleen Glenney Boggs.Margaret Fullers American Translation.American Literature,Vol.76,No.1,March 2004.pp.32—33.) 出生在美國的華裔,主要是第二代、第三代等等,學習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主要渠道之一是閱讀中國經典的英文翻譯本。而他們閱讀的翻譯文本多為美國人所翻譯。由于翻譯者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和對漢語的掌握直接影響到譯本的內容,所以從異國文化的視角闡釋中國文化時給譯本中加入異國文化的因素是難以避免的。英文翻譯的中國經典經歷了一個被再創作的過程,其中包括對中國文化價值觀的再創造。當趙健秀說“……媽媽說關公就像中國的約翰·韋恩。媽媽的大姐芙蓉阿姨說他看上去更像中國的克拉克·蓋博。”時,他們絕不是在說從外表上關公長得像約翰·韋恩,因為這是不可能的。他所說的意思是,關公之對于中國文化,恰如韋恩之對于美國文化。約翰·韋恩代表的是典型的美國文化中具有強烈個人主義內涵的英雄主義形象。因此,在趙健秀作品中,關公變成具有中國男性外形的美國西部硬漢約翰·韋恩。趙健秀在這里崇尚的是美國的文化英雄。語言的翻譯帶來的文化翻譯致使華裔認知的中國文化不同于我們生長在中國的人認識的中國文化。文化之可再創造性并不是個秘密,已有學者指出:“文化不再是人為操控的產物,而是具有創造性、批判性和抵制性的。”(注:Peter Krapp.Déjà Vu:Aberration of Cultural Memory.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4,p.219.)
其二,華裔文化是受到兩種文化影響的文化,它根據華裔的需要從兩種文化中吸取文化成分或文化符號。由于華裔生活在異域,對發生在中國的事件沒有直接的第一手經驗,所以往往根據自己的生存需要,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以及現實中對他們有用的東西各取所需,用他山之石攻玉。因此,木蘭就變成現當代西方的女權主義者,引領西方婦女的解放運動;關公就變成了華人英雄,率華人移民在美國西部開山修路。他們可以喜歡自己并沒有讀過的書、看過的戲,而認為說到他們的心坎上;也可以認同任何他們喜歡的人為“兄弟姐妹”,而喜歡他們所做的一切。華裔用中國文化中的事件來言說美國語境中的事情,這是非常普遍的。這被許多中國讀者和學生認為是華裔在與中國文化認同。這里被忽視的是,他們用中國文化中的事言說的是華裔作為美國人的麻煩和問題。近年來歷史學家發現并且基本達成了共識,認為舊的移民推拉(pull and push)模式不足以完全了解遷移定居者的經歷,理解他們的心態——用后現代術語來說即他們的主體意識,這些移民者在不脫離與故鄉和家庭關系的基礎上,出于自身需要和愿望形成了新的關系。美洲大陸諸國對早期華人男性移民貼上的隱性標簽——“過客”,正是一種雙民族或跨民族思維和運行的模式,兩者都承認但同時又超越了移民的“舊家”和“新家”。 (注:Evelyn Hu瞕ehart.Concluding Commentary on Migration,Diasporas and Transnationalism in Asian American History.p.310.) 正如“跨”在跨民族中所表明的那樣,“跨”說明了兩個國家之間存在著距離。從離散到跨民族是一個自然的進程,正如從移民到離散一樣,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解釋了移民、離散和跨民族概念有時為何可以互換。它們互不相同,但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這個進程還包含了更大的解釋空間。(注:Evelyn Hu瞕ehart.Concluding Commentary on Migration,Diasporas and Transnationalism in Asian American History.p.311.)
第三,由于第一手經驗的缺失,華裔在表述中國文化時加入了大量的想象和記憶。他們間接獲得的中國文化的記憶在被表述時經歷了再創作,這成為中國文化在域外本土化時的一個特點。華裔對中國文化的本土化經歷了被托尼·莫里森稱之為“再記憶” 的過程。在湯亭亭的《女勇士》到底是虛構還是非虛構小說的討論中,托尼·莫里森發表了看法,她認為《女勇士》不是自傳,而是有意識的“再記憶”,“是在通過口頭傳說和文本形式去傾聽并訴說我們所知道的各種過去”。(注:Helena Grice.Negotiating Identities—An Introduction to Asia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New York:Manchester UP,2002,p.94.) 美國華裔作家表述的中國文化,都表現出明顯的再記憶的特點,而成為華裔對中國文化經過想象、記憶、再記憶而生成的文學產品。趙健秀的“生活是戰爭”,典型地說明華裔在海外所認知的中國文化既有語言翻譯和文化翻譯所帶來的異域文化的影響,也有華裔現實生活對中國文化的需求,更有華裔間接接觸中國文化而形成的廣泛地利用記憶、想象和再記憶的事實。三者結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海外的中國文化傳播和被本土化的主要方式。
趙健秀的“生活是戰爭”之信條的來歷和作用,說明了中國文化在海外傳播的途徑及其發展變化。趙健秀在一次訪談中所說:美國華裔和美國日裔說:“我們不是中國人,也不是日本人,而是我們自己,是新的——似乎是說,我們來到此地,有新的歷史,新的經歷,新的感受。”(注:Frank Chin.Bulletproof Buddhists & Other Essays.Hawai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8,p.456.) 美國華裔文化的構建,離不開中國文化的內容。但是,中國文化在海外經歷了本土化的過程,這是不應該忽視的。中國傳統文化在海外的傳播,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研究課題。特別是在21世紀的今天,當文化交流和多元文化成為世界性的文化生態時,研究中國文化在海外的傳播與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論文為天津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資助項目之重點項目。)
(徐穎果:天津理工大學美國華裔文學研究所 郵編:300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