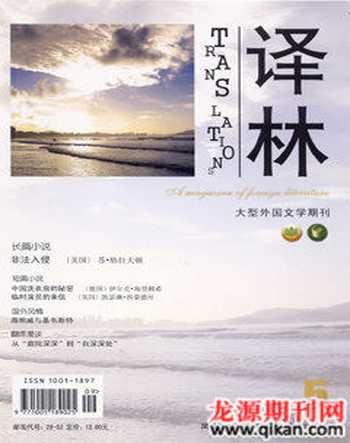《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的四種解讀
陳 紅
摘要:對《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故事和人物的批評主要有“心靈激情說”、“人道主義悲劇說”、“異變心理說”和“作家自我表現說”等。“心靈激情說”和“異變心理說”借鑒心理學理論,運用心理分析的手法來深入挖掘人物的心靈世界。“人道主義悲劇說”突出分析“陌生女人”愛情中的人道精神和悲劇特征。“作家自我表現說”把小說當作作者的自我代言人,表現身處特殊時代的作者的精神世界。
關鍵詞:心理激情 人道主人悲劇 異變心理 自我表現
猶太籍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是一位頗受讀者歡迎的作家,他的作品是被翻譯成其他語種最多、發行量最大的德語作家。他的中篇小說《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由于其凄美驚人的愛情故事、哀婉動人的語言敘述、細膩復雜的情感描寫等藝術特色受到各國讀者的青睞。1948年,馬克斯·奧菲爾斯把這個故事搬上了銀幕,讓更多英語國家的人們了解了茨威格;而由徐靜蕾在2005年改編的中國版電影《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讓更多年輕的中國人也熟悉起茨威格的名字。
《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是一部跨越時代和國界的杰作。在這個開放多元的、反傳統的現代社會里,評論家們從不同的讀者視角去剖析解讀該小說中的故事和人物。總結各種評論,頗為集中和典型的有以下四“說”:
一、 心靈激情說
“心靈激情說”認為這是一個激情故事,它歌頌了唯美而極致的愛情。花季少女偷偷愛上了新鄰居:一個“富有、奇特、神秘”的、擁有許多漂亮圖書的青年作家R。這個“陌生的女人”將愛情視為生命,充溢在她的心中的熱烈純真的激情是她生活的動力。在那個物欲橫流的時代,玩弄愛情、濫施感情已經司空見慣,人們“玩弄愛情,就像擺弄一個玩具,他們夸耀自己戀愛的經歷,就像男孩抽了第一支香煙而洋洋得意”。但是,在她的心里,“愛情卻是我至高無上的激情——所以我把原來分散零亂的全部感情,把我整個緊縮起來而又一再急切向外迸涌的心靈都奉獻給你。”(注:茨威格:《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夜色朦朧》(德漢對照),張玉書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以下對小說的引用均出自張玉書譯本。)
從頭至尾,她愛得如此純粹而不加雜質:少女的癡情有別于成年婦女的“欲火熾烈”、“貪求無饜”的愛情,而成人后的她對作家的激情不僅一如既往,而且變得“更加熾烈、更加含有肉體的成分,更加具有女性的氣息”。她愛得如此熱情而奔放:當作家的一道偶然的目光投向年少的她的時候,她的心里就燃燒起火焰,“從我接觸到你那充滿柔情蜜意的眼光之時起,我就完全屬于你了”;當她成為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的時候,“當年潛伏在那個不懂事的女孩子的下意識里、驅使她去拉你的門鈴的那個朦朦朧朧的愿望,現在卻成了我唯一的思想:把我奉獻給你,完全委身于你”。她愛得如此倔強自尊:“我要你一輩子想到我的時候,心里沒有憂愁。我寧可獨自承擔一切后果,也不愿變成你的一個累贅”,因此當她有了他的孩子的時候也對他守口如瓶;為了他們的孩子過上“上流社會的光明、快樂的生活”她寧愿賣身做有錢人的情人而不去懇求他的幫助。
她的純粹、奔放、自尊的愛情全是出于心靈的激情和意志,“自從我從童年覺醒過來以后,我這整個的一生無非就是等待,等待著你的意志!”
柏拉圖認為心靈有“三曲”即由三個部分——理性、欲望與激情構成。這三者功能有異,各司其職。理性用于思考推理,擅長理智活動;欲望用于感受愛情與饑渴等,是種種滿足和快樂的伙伴;激情介于理性與欲望之間,通常是理智的盟友,但有時也會站在欲望一邊反對理智。在理想情況下,即在道德修養高的人身上,激情會同理智結盟,從而人就會采取合理而公正的行動。(注:引自王柯平:《柏拉圖的心靈詩學喻說》,載《外國文學評論》,2003年第3期,第133頁。) “陌生女人”更符合弗洛伊德的欲望哲學,在她的心靈構圖上,理智的成分被淡化了,她的心靈受到利比多(libido)的魔力的攫持,到死方休。換言之,激情和欲望聯袂表演,唱響一曲為情而生死的心靈絕唱。
二、 人道主義悲劇說
“人道主義悲劇說”突出分析“陌生女人”愛情中的人道精神和悲劇特征。“陌生女人”為愛而活,為愛而死,她的愛死心塌地、舍身忘己。少女的她心里魂牽夢繞只有他,她“一頭栽進我的命運,就像跌進一個深淵”。在被迫隨母搬家到因斯布魯克的兩年中,為了在心靈深處同心中的他單獨相處廝守,她拒人于千里之外,沉湎于她“那陰郁的小天地里,自己折磨自己,孤獨寂寥地生活”。經過了五年的癡癡等待,她終于成為他“幾百個女人當中的一個”,同他做成“連綿不斷的一系列艷遇中的一樁”,但她毫不言悔,并且對他帶來的“無比的歡娛、極度的幸福”喜不自勝、感恩不盡:“我愛你這個人就愛你這個樣子,感情熱烈而生性健忘,一往情深而愛不專一。我就愛你是這么個人,只愛你是這么個人。”在她的愛情里,不求回報的索取,只有自我的奉獻。自從有了她的“命根子”,她對他的激情化作了一年一度在他生日時贈送一束白玫瑰的象征性行為;而為了他的“另一個自我”,她不惜出賣肉體并且毫不為此感到羞愧,“這對我來說也不算什么犧牲,因為人家一般稱之為名譽、恥辱的東西,對我來說純粹是空洞的概念:我的身體只屬于你一個人,既然你不愛我,那么我的身體怎么著了我也覺得無所謂。”她拒絕伯爵的求婚,為的是不讓婚姻捆住手腳,因為她心里始終珍藏著一個“永恒的夢”,就是對那個放縱情欲、揮霍感情的作家的堅貞不移的愛。
這是怎樣一種現實與理想之間的悲劇性矛盾啊!她的內心其實一直煎熬在矛盾之中。她恨他和另外的女人“這樣明顯地表示出肉體上的親昵,可同時自己也渴望著能得到這種親昵”;她對他隱瞞著關于自己以及孩子的一切,而她多么渴望被他認出來。隨著她的“命根子”的逝去,她的靈魂、她的生命也隨之而去。“我將第一次對你不忠,我已經死了,再也不會聽見你的呼喚:我沒有給你留下一張照片,沒有給你留下一個印記,就像你也什么都沒給我留下一樣;今后你將永遠也認不出我,永遠也認不出我。我活著命運如此,我死后命運也將依然如此。”這字字血聲聲淚的宿命傾訴,為她心中的他,為我們讀者唱響一曲崇高的“情圣”悲歌。
朱光潛在《悲劇心理學》中有一段轉述尼采的悲劇學說的文字:“尼采用審美的解釋來代替對人世的道德的解釋。現實是痛苦的,但它的外表又是迷人的。不要到現實世界去尋找正義和幸福,因為你永遠也找不到;但是,如果你像藝術家看待風景那樣看待它,你就會發現它是美麗而崇高的。尼采的格言:‘從形象中得到解救,就是這個意思。”(注:朱光潛:《朱光潛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58頁。)我們不妨也將《陌生的女人》解讀為“酒神原始的苦難融入到日神燦爛的光輝之中”(注:同上,第2卷,第363頁。)的文本。
三、 異變心理說
“異變心理說”認為這是一個單戀故事,它集中分析單戀女主人公的偏執與瘋狂。那個小說家R在許多讀者看來只不過是個紈绔不羈、缺乏責任心的花花公子,甚至她自己是完全了解這個風流公子的品性的,但是她還是義無反顧、心甘情愿地用她的一生守候著這份癡情:“你對我一無所知,你正在尋歡作樂,什么也不知道,或者正在跟人家嬉笑調情。我只有你,你從來也沒有認識過我,而我卻始終愛著你。……我的一生一直是屬于你的,而你對我的一生卻始終一無所知。”
這是怎樣的一份違背常態的愛情啊!心理變異的女子沉湎于愛情的烏托邦里,絲毫不顧她已經秋毫洞察的他的雙重性:“你過著一種雙重生活,既有對外界開放的光亮的一面,另外還有十分陰暗的一面,這一面只有你一個人知道——這種最深藏的兩面性是你一生的秘密,我這個十三歲的姑娘,第一眼就感覺到了你身上的這種兩重性,當時像著了魔似的被你吸引住了。”少年時的她每天回家都會躲在門后,透過門上的小孔窺探作家的一舉一動;她上百次地跑下樓,仰望作家屋子里的燈光,想象著自己怎樣親近心儀之人;她親吻作家摸過的門把手,撿回他扔下的煙蒂;她想方設法進入作家的房間,里面的一點氣息和氛圍就足以為她提供“神思夢想”的養料;遠離維也納的日子里她把作家的書讀得滾瓜爛熟,“要是有人半夜里把我從睡夢中喚醒,從你的書里孤零零地給我念上一行,我今天,時隔十三年,我今天還能接著往下背”;回到維也納的她每天下班后來到他的窗下站著,直到燈光熄滅,為的是等候一個永遠不能實現的夢想,一種“不為你所認出的命運”;當她有了“三夜銷魂蕩魄繾綣柔情的結晶”的時候,她欣喜若狂,“這下子我終于把你抓住了,我可以在我的血管里感覺到你在生長,你的生命在生長,我可以哺育你,喂養你,愛撫你,親吻你”。
通過第一人稱娓娓而道出的暗戀心曲,一顆孤獨單戀的靈魂的最隱秘處被剝離得淋漓盡致。這是一個“置身于人群之中卻又孤獨生活”的靈魂,追求激情和壓抑情感這對矛盾一直沉積在她的潛意識中,從而導致異變的心理和鐘情妄想。茨威格曾借《象棋的故事》中人物之口說:“我素來感興趣的就是各種有偏執狂的人,即囿于某種單一的思想不能自拔的人,因為一個人用來局限自己的范圍愈狹小,他在一定意義上就愈接近于無限。”(注:茨威格:《茨威格精選集》,韓耀成編選,山東文藝出版社,2000年,第752頁。)“陌生的女人”正是一個生活中的獨行者,只有惺惺相惜的人才能看到這種偏執狂的接近生活本真的“無限”。
四、 作家自我表現說
“作家自我表現說”認為,“陌生女人”是作者的自我代言人。茨威格曾經生活在19世紀的維也納,那個“太平的黃金時代”。但是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硝煙摧毀了“昨日的世界”的合理性、人道性和他所崇尚的歐洲文明。“戰爭把我這個人以及我的精神世界變成一個可怕的荒原。我像一個逃難者,光著身體,身無分文,從我生命深處燃燒著的屋里逃出來,向何處去——我不知道。”(注:茨威格:《茨威格散文精選》,人民日報出版社,1997年,第297頁。)
這種無所適從、茫然無助的精神情結猶如被壓抑的無意識,在作家寫作的時候得到激活并通過作品這個渠道得到曲折的宣泄。這一論點由于茨威格和弗洛伊德的密切關系(注:關于茨威格與弗洛伊德的關系,參見張玉書:《兩位文化偉人之間感人至深的情誼——弗洛伊德與茨威格通信集》,外國文學,2006年第2期。)而得到認同,而小說所具有的詩化特征使得“作家自我表現說”更具說服力。詩化的小說往往如詩歌那樣運用“情緒的流動,內心的獨白,放射性的結構”等手法賦予小說以“透視法、抒情性、象征性、比喻性、聯想性、音樂性等審美特征”(注:張薇:《論伍爾夫小說的詩化》,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2期。)。《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以如泣如訴的抒情筆觸,通過借喻和象征的手法,表達作者的現實處境和旨蘊意念。“陌生女人”可以被解讀為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即那個“昨日的世界”的象征;而小說家R則象征著作者生活的現實世界:這個使他失去祖國失去家園的磨難的世界;陌生女人的死似乎預示著作者飄零異鄉自殺身亡的命運。
五、 結語
茨威格小說的翻譯家張玉書認為,茨威格小說不以“眾多的人物,廣闊的歷史背景,絢麗多彩的風俗畫面,錯綜復雜的故事情節”取勝,而是“以狂暴激烈的內心斗爭,變幻莫測的感情起伏,也就是以內心世界波瀾壯闊的變化和深刻尖銳的矛盾”見長。這種扣人心弦、讓人噓唏的作品跨越了時代和國界,獲得一代又一代讀者的青睞。(注:偉大心靈的歲月回響——張玉書談茨威格作品及其翻譯 http://www.ewen.cc/books/bkview.asp?bkid=139317&cid=420124。)上述特征加之作者非同一般的身世,給茨威格小說的多元解讀提供了基礎。在對《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的上述四種解讀中,“心靈激情說”和“異變心理說”借鑒心理學理論,運用心理分析的手法來深入挖掘人物的心靈世界。“人道主義悲劇說”突出分析“陌生女人”愛情中的人道精神和悲劇特征。“作家自我表現說”把小說當作作者的自我代言人,表現身處特殊時代的作者的精神世界。
(陳紅:中國計量學院外國語學院副教授,郵編:31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