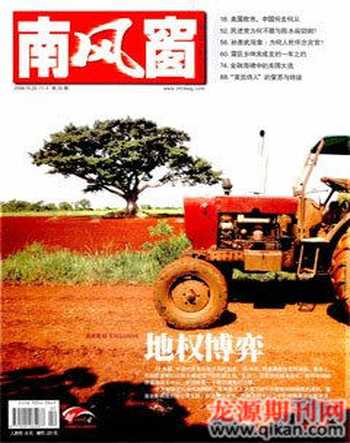震區鄉紳席成友的一年之約
甄靜慧
5·12地震之后,千萬富豪席成友被火線提拔為重災區勝利村的村支書。這個12年里不斷拒絕當村官的精明生意人,一朝上任,立刻扮演起“新鄉紳”在農村基層組織中的作用。而他的想法與做法在勝利村引起的波瀾,正是大災之后,鄉村社會基本矛盾的生動體現。
閃亮的奧迪車輪輾在地震災區路旁廢墟的泥濘中,顯得格格不入。而當席成友將車停在一個簡陋殘敗的帳篷前,則又帶來另一種強烈的對比。
妻子和兒媳正在大帳篷邊上熱火朝天地炒著菜,席成友笑了笑:“我就住在這里,衛生條件差,將就一下吧。家里什么都沒了,只有車子在綿陽,幸免于難。”
“我們在綿陽有房子!”夫人遠遠喊話。席成友皺皺眉,放低聲音:“看,她就這么成天找我吵架。我說吵你的去吧,不高興你們就回綿陽啊。但他們去了沒半天又要回來。”
北川縣擂鼓鎮大多數人都知道勝利村有位富豪村支書,這在當地絕無僅有。
地震前,鎮上資產上千萬的人共有16個,席成友是其中之一。如果不是這次地震,2009年他的個人資產將會上億。
“酒店倒了,養殖場沒了,正準備興建的電廠計劃擱置了——直接經濟損失大概一兩千萬吧。”不過,水廠和在其他鄉購置的幾萬畝林地還在,他依然還有數千萬身家。
這個故事早就在當地被反復傳頌。
5月12日,席成友正和妻子、兒子在綿陽買推土機。地震突然發生,妻子兒子趕忙回綿陽市里的房子探望,席成友卻立刻開著剛買的推土機,邊開路,邊往老家勝利村趕,平時40分鐘就到的路,那天用了4個小時。
雖然尚在村里的親人無恙,但勝利村1700口人,家家房子倒塌,10多人在瓦礫中喪生,塵埃蔽日、哭聲連天的慘況觸目驚心。席成友當機立斷,清空了自家倉庫,把7000斤大米,500斤鹽分給大家,支起鍋灶建了4個大灶,賑災自救。
6月29日,村里召開黨支部會議,大家一致投票選席成友當村里的黨支部書記,7月,上級黨委的任命下達——這是迅速而典型的“火線提拔”。
就這樣,在這個特殊的時刻,席成友巨額的個人財富、帶有個人色彩的經濟發展眼光,以“村支書”身份為紐帶,迅速與和國家治理鏈條最末端的村官權力結合在了一起。
“拒官”12年
這并不是他第一次與“村支書”身份扯上關系。
1996年,席成友正式開始經營自己的公司,并積累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鎮黨委和村里的老支書開始游說他回勝利村當村支書。
相中他的原因不難理解。自己有相當財富積累的企業家當上村干部,一來不會存在貪污村里有限經費的擔憂,而且在政府對基本建設投入不足時,富豪村官極有可能以個人財力承擔一部分責任。
更重要的是,讓有經濟發展眼光的企業家為官,村里等于有了致富的領路人——這種被稱為“新鄉紳治理”的模式在農村改革進程較快的地區已經出現多年。
“當時也曾想過回來。我是在勝利村長大的,也不想見到鄉親窮困,村里連條像樣的道路都沒有。”然而席成友最終還是沒有回來,他并不諱言,12年來不接任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放不下自己在外面的生意。
“一個地方一直落后肯定有它的道理。當地老百姓思想閉塞,原來的政府部門又缺乏發展和改革的魄力。”就在席成友說這句話的時候,外面有村民發生了激烈爭吵,其中一個瘦削的中年男子特別激動,幾次跳起來要動手,最終要以數人之力將其拉開。

這段時間村里每天都上演著這種鬧劇。
為了重建,政府征地建設永久性住房。這天,生產三隊發現二隊一間房子倒塌的墻體恰恰跨在兩隊包產地的邊界上,如果要根據墻體邊沿劃界征地,二隊就多占了幾十平方米的土地。雖然以一畝地10萬元左右的賠償額度,幾十平方米土地的賠償費用平攤到一個生產隊眾多人頭上,根本體現不出幾元錢的差異,但沖突還是無法避免。
面對這些雞毛蒜皮卻似無休止的爭執,席成友露出厭煩和恨鐵不成鋼的神色:“無論怎么說,他們仿佛永遠都不會明白,死守這一畝三分包產地,最終只是害了他們。”
席成友認為,這些年橫亙在他回村治理道路上的最大阻力,就是當地雷打不動的土地聯產承包制政策。
征地的矛盾
如果以土地利用的類型來劃分,擂鼓鎮勝利村是個典型的農耕型村莊,村里9個生產隊,土地以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方式分下去,每人擁有的土地面積從幾分到數畝不等。
土地作為農村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其效益的發揮程度與村民的富裕程度直接掛鉤。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質是不允許農民失去土地,作用僅限于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
但在勝利村,甚至連溫飽問題也不能依賴包產地解決,農耕并不是當地村民的主要生活來源。這里土地貧瘠,無法栽種糧食和經濟價值更高的作物,只能在上面種點耐旱度高的玉米,村民口糧都要從外面買。而在一畝土地上辛勤勞作一年,往往只有五六百元進賬,年經濟收入最多也不超過1000元/畝。
地震前,勝利村的人均年收入能達到3580元,主要靠年輕人外出打工,只有老人才在家種地,土地效益非常低。“既然是這樣,何不轉變思維,改變這些貧瘠耕地的用途,讓其發揮更大效益?”
12年前,席成友給勝利村畫過一幅藍圖:把土地收歸集體進行集中經營,引進企業。成功招商引資后,由企業給失地村民提供一次性賠償款,以后村里給村民每人每月發30斤大米,120元生活費;富余勞動力可自由選擇外出務工還是替當地企業打工——“這肯定比種包產地的收益高。”
然而,“失地”對數千年來依賴土地生存的農民來說是一個多么沉重的詞。包產地年收入再低,那是穩定的,除了直接經濟收益外,給予他們的還有實實在在的安全感;而席成友的承諾,卻更像個虛幻的空中樓閣。
“老百姓目光短淺,沒見到實際利益前,他們不會信任你。”席成友與村民間的不信任感由來已久。在他當上村支書后,這種矛盾愈顯尖銳。據他統計,村里專愛跟他唱對臺的“搗蛋”分子約有30%,比較信任他的也占30%,還有40%屬于“騎墻派”,哪邊抬頭就往哪倒。
其實,村民對席成友的感情很復雜,種種抗拒背后,除了不信任外,還隱含“不服氣”的賭氣情緒在內——都是生于斯長于斯,他憑什么能擁有千萬資產;把大家的土地交由他去支配,經濟發展起來真正受益的到底是誰?
原始積累
“企業做大了,回來撈政治資本吧!”這些話,村民不但對記者說,有時還當著席成友的面指責——富豪當村官,確實不屑于貪污村里那點資金,但他們對資源的支配和利用,究竟是以利己還是利他為原則,農民并非不會質疑。
上世紀90年代,集體水廠進行股份制改制,席成友等幾個管理人員出資買下股權,集體企業私有化實現了他的原始積累同時,也難免加大他與普通老百姓之間的隔閡。
兩三年前,席成友想在勝利村搞林業基地,引進經濟價值較高的果樹,就遭到了強
烈的抵觸。按他的計劃,建一個集中的種植基地,栽種經濟價值高的藥材和核桃,8年以后就能體現出巨大的經濟價值,村里人均經濟收入應該可以達到5~8萬。年輕人還可以在基地打工,學習農業和養殖技術。
然而村民對此很反感。建基地,還是涉及征地,而且還征到席成友個人名下去。“你也是長一個腦殼,我們也長一個腦殼,就你能種核桃,我們不會種嗎?”火氣大的村民這么說。
努力不果,席成友把基地建在了離擂鼓鎮一段距離的墩上鄉新民村、禹里鄉禹穴村和都壩鄉水井村三個村子里,共計有3萬畝林地,都栽上了藥材和核桃樹。而把這一切看在眼內的勝利村村民,很多也隨之種起了核桃——顯然,他們雖不愿服從他的治理,卻還是相信他的經濟眼光。
對此,席成友很不屑:“這么一畝三分地,有什么用?就今年初有企業過來,要收200噸核桃,以包產地零零碎碎的種植量,能交出來嗎?最終還是產生不了規模效應,致不了富!”
“要發展,就必須集約化、規模化,船大才好抵御風浪。小打小鬧永遠成不了氣候!”他用力揮手拍在桌子上,聲音很響。“軟的不行就來硬的。一開始村民可能會因為失去土地而哭泣,但年底得到利潤分紅,他們就會理解了。”
基于此,富豪席成友曾向鄉鎮政府提出了三個要求,要求“權力擔保”:“要我回村當支書,第一要擬定政策,把70%的包產地收歸集體,只留下30%作為村民自留地。第二是所有建房要通過每個合作社集中建起來,騰出大部分的宅基地,還是用以招商引資。三是搞公司集約化后,以村為單位成立治安聯防隊,在進行治安管理過程中政府不得追究我的法律責任。”
無法雙贏
在勝利村,村民的自建房占地面積都很大,有的人家里常住人口只有兩三人,卻建了多間房子,而且各人的房屋錯落分散,把土地切割得零零碎碎。在席成友眼里,土地是能下金蛋的寶貴資源,他看著心疼。
但村民總覺得:建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的房子,才有歸屬感。

地震后,政府規劃在平地的中心地帶建永久性住房。但村民意見很大,把村長未繼明愁壞了:“老百姓開始不希望集中建房,還是希望建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后來實在沒有就地重建的條件,他們又在爭集中住房到底建在哪里,都要求建在自己的生產隊地盤上,現在的規劃是建在五六隊的地上,其他生產隊天天都在鬧。”
傳統觀念深入骨髓,連天災也無法將其打破,更何況當年風調雨順時?當年如果有人要拆房子,大伙不沖上來拼命才怪。這種事席成友自己做不來,也不愿擔惡名,他希望政府來協調。
“這在你們發達地區的農村早就在做了吧?”席成友表情嚴肅地皺著眉頭,“但當年政府放不開思想,說這跟改革開放政策相違背——土地承包30年,還沒到期限呢,怎么能收回來呢。”
土地收歸集體流轉,這些年來在東部地區確實不是稀罕事,部分村莊依靠這種方式拉動了經濟發展,但其間出現的問題與爭議也從未停歇。當年鎮政府不答應,一方面是觀念相對保守,而另一方面,也許是出于對可能出現的問題及民憤的擔憂。
但對于席成友來說,他生于斯長于斯,企業的發展離不開當地的關系,當企業處于擴張階段時,掌握村官權力及各種資源的支配權,不但可以帶領村子發展經濟,對個人企業的長足發展必然也更為有利——這是一個“雙贏”的考慮。
然而如果土地問題解決不了,對資源的支配權受限,不僅村里經濟始終發展不起來,他個人也只能長期耽于芝麻綠豆的村中小事,反而會拖慢個人企業發展的步伐。
權衡之下,他不愿干了。
村干部直選每換屆一次,鎮領導就找席成友一次,每次席成友都提一模一樣的三個條件,政府始終還是一條沒答應。如是這般12年,老支書已年過70,席成友還是勸他:“你再頂一屆,下屆我再考慮。”
拒當村支書后,席成友個人、事業發展一日千里:林地、養殖場、酒店等資產與日俱增。
貧和富的差距,即使在災后重建的艱難日子里也有明顯體現。當村長夫婦正用政府免費發放的大米煮著咸菜稀飯的時候,席成友的妻子端上了排骨、魚、肉、雞、南瓜等一大桌豐盛菜肴,肉香從四面通風的帳篷里一直飄出去。破而后立
不過,這些年席成友并不是以“富豪”的身份與勝利村隔離的,雖然在綿陽有房子,但他口里所說的“家”在勝利村。
從1996年首次拒當村支書開始,每年春節他都給村里70歲以上的老人慰問金,并多次出資給村里修路。包括這次地震開倉發糧,他一直在村里扮演著傳統社會鄉紳的角色,也希望能通過這些舉措漸漸修復與村民之間的隔閡。
“這次臨危受命,本來不想干,但大災當前,推不掉。”席成友平時表情嚴肅,極少笑。但只要是跟村民交流,他都會露出友善的笑容,但這并不能減少當上村官后的他與村民的直接沖突。
在明暴雨造成的山體滑坡現場,他激動地跟旁邊幾個村民交談著,幾番爭執后,他快步往泥石流形成的廢墟走下去,指著露出地面的輸水管道告訴記者:“這里本來是村民的包產地,泥石流后變成了砂石廢墟,有些村民就挖砂拿去賣。河床越挖越深,不能容許他們再這么干了。”
對這些瑣事,席成友不勝其煩,卻又不能不管。“老百姓就是這個樣子。干再多的事情都得不到理解,你的態度稍為不好,他們還要罵你。”
好在政策峰回路轉,席成友仍舊干勁十足。
擂鼓鎮早在1996年就被劃入北川縣城一體化發展范圍,但12年過去了,地征不下來,村里沒有一條真正像樣的大道,公共設施無法興建。然而地震后只用了20天,道路全部推通了,兩個月后路燈也安裝好了。
由于接收安置附近山區的災民,四個村的常住人口一下子從4000人猛增至1.5萬人以上。四個村的總體幅員面積2.6平方公里,除去河道和道路只有1.9平方公里,再減去城鎮規劃的公共服務設施,可供開發的只有1.1平方公里。
基于此,政府定了規劃,要把這里建成禹羌民族文化村,使其作為未來旅游產業的樞紐——從成都到地震遺址博物館,從擂鼓中轉,最后再到九寨溝,形成一條旅游環線。而最令席成友高興的是,為了集中建房以及建設旅游設施,政府下了政策征地,村民終于不得已接受了這個事實。
包產地和宅基地收回,集中永久性住房建起……這一切實現后,席成友12年前提出的條件基本都已具備,最重要的是政府承諾埋單——對于失地的農民,將通過農轉非,納入社保、醫保、低保體系。
“還有比這更理想的狀態了嗎?雖然地震奪走了我們很多人的生命,破壞了我們的家園,但卻又給我們帶來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破而后立的格局,是他當初料想不到的。
精英的作用
盡管村民對席成友的不信任與怨言一如既往,但現實似乎表明,由這樣的農村精英領導的村子,發展步伐的確快得多。
在擂鼓鎮政府臨時辦公室,負責災后重建規劃的山東援建人員對席成友也很熟悉:
“當其他村子還在為征地問題糾纏不休時,席書記已經把勝利村的未來經濟發展規劃都做好了。”
更重要的是資金。
作為一個生意人,席成友非常清楚該如何與社會資源產生良性互動。
7月初首次見面,席成友便送了份材料給記者,《勝利村的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天情況介紹》,凡有外界的來訪者,他都會遞上這份僅標題就讓人印象深刻的說明。
據席成友介紹,因為他的積極宣傳引薦,現在已經有兩個機構直接捐款資助勝利村災后經濟發展,金額約為1000萬。“如果不是前段時間老百姓太搗蛋,我起碼還能再要到1000萬。”同是一片平地上的幾個村落,只有勝利村在短期內獲得了這么多的捐助。談到這個問題,席成友難得地露出笑容。
前段時間,他個人出資3萬元注冊了“禹羌文化拓展有限公司”,公司以集體名義成立,60%股權分屬于村民,20%屬于生產加工管理團隊,20%屬于銷售團隊。一方面利用羌族的文化禮儀接待游客從而產生價值;另一方面生產加工包括羌繡、羌族服裝,山核桃工藝品等產品,在產生利潤同時解決部分就業問題。
思路定下后,問題出來了。羌族文化特色是載歌載舞,但擂鼓鎮上的羌族大多已被漢化,能堅持這種傳統的有多少?
為了盡快形成特色,席成友要求村民把羌族傳統重新撿起來。“白天吵翻天我不管,晚上給我好好學習歌舞。”他知道對村民來硬的不行,勸說也不行,只有利益驅動最有效,“要在‘禹羌文化拓展有限公司分得股權,就一定要把羌族‘歌莊學會。”
這當然只是“嚇一嚇”他們的話,但成效甚卓。晚上來到勝利村,月朗星稀,兩三百村民穿著帶有民族特色的服裝,在空地上熱鬧地練習傳統舞蹈,他們心里也許不太情愿,但這場景勢必令旁觀者非常感動。
最近又有一個機構承諾撥款支援永久性住房建設,條件是房子建好后留一部分給他們以后接待游客。“很多機構是這種類型的——援助的同時也在尋找商機。我們必須努力與別人的商機相配合,才能盡快籌集到更多資金和資源。”
“新鄉紳”之治
資金到位,席成友心情很好。但村民們更多地著眼于眼前利益,拉回來的資助款項怎么用,公司怎么運作,他們缺乏思考。
村里未來怎么發展,其實還是在席成友的一念之間。
村民天天為一點土地賠償款爭執不休的短視行為在他眼里更加不值一哂。村里各生產隊的劃地會議上根本不會看到他的出現:“要把有限的精力放到更重要的事情上去。老百姓留給基層干部去開導。”一把手席成友書記這樣說。
8月下旬,席成友到山東濟南修改建設方案,濟南政府向他引薦了當地西區開發經驗——政府向農民征用3 40多平方公里土地,建成了集商住、娛樂、大學和科技園一體的規劃區,兩年半就把一切都完成了,據說對當地經濟促進很大。
“當時我就有個想法,何不讓我們村的村民去學一學,開開腦筋。”9月19日,他個人出資買了10多張機票,帶著村里9個生產隊的隊長直飛濟南,在濟南市政府接待考察后,第二天晚上又乘飛機回到勝利村。
短短兩天,9個生產隊長不約而同改變了當初的態度,開始配合推動征地計劃和安撫反對的村民。
“這么做當然也有副作用。村里有人說我把政府的補償款私吞了,拿來給隊長游山玩水,買通他們。不過沒關系,我自己做的事不需要其他人理解。如果連基層干部都不能把工作做通,那么就少數服從多數,強制執行!”席成友目光堅定而銳利。
“老百姓現在再怎么罵,看到實在的利益后他們就會理解的。而且我也不會在這個位置上做太久,上了軌道后就讓高素質的年輕人去管理吧。”口里雖說不介意別人的看法,但席成友還是不斷強調著他對村支書職位并不留戀,希望以此撇清自己牽涉其間的利益關系。
而他,也的確放心不下自己的個人財富,對他來說,那才是一切的基礎:“經歷了地震,我的公司也處于非常時期。村里的事情解決后,始終要把精力轉回去。”
“我只干一年,帶領大家渡過難關就不干了。”7月記者初見席成友,他曾堅定地表態。
3個月過去,他雖然仍舊說著“干一段時間就不干了”,卻再未提及“一年之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