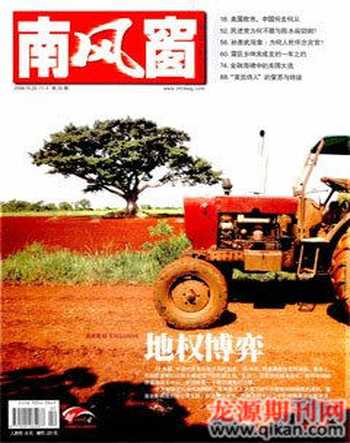想念華爾街
崔少明
一個月前,本欄說香港繼2003年沙士后,在“政經兩方面同時遭到沖擊”。不料面對80年一見的金融海嘯,“沖擊”遠遠不足以形容形勢的嚴峻。
同屬金融中心的開放型小經濟體系新加坡已步入衰退,香港相信也難逃一劫。因為股樓插水,倒閉、破產、失業上升而加劇的勞資和貧富分化,必定反映在政治上。商界為求自保,將更趨保守;基層為了生存,也將激烈抗爭。庫房因為衰退而入不敷出,無力應付民生訴求。官商與市民的摩擦將會加劇,源于生活的家庭悲劇將會充斥傳媒。要到淘汰了“足夠”的弱勢行業和勞動力后,經濟才可望進入新的上升周期。但此時已尸橫遍野。
我無意危言聳聽。但這次的金融危機,我做了30多年的新聞,還是第一次領教。市場缺口恍如太空的“黑洞”,美歐各國天天加大力度救市,但所放出的千億計美元恍如落入無底洞。危機看不到盡頭。香港回歸頭幾年,亞洲金融風暴所激發的社會矛盾有可能重演。
我不敢說,明年香港又會有幾十萬人上街,戾氣沖天,但必須作最壞的打算。何況香港上次有難時,內地經濟仍然勢不可擋,可以伸出CEPA(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的橄欖枝。但這次的華爾街災難非亞洲危機可比。國家對歐關的出口將大為縮減,股樓也少了外資的支持。目前只因為人民幣并非自由兌換,危機來得較慢。但東莞和浙江已開始為制造業救亡。面對全球性的風暴,中國不可能靠內需獨善其身。若此,中央恐怕很難提供太多的協助。港澳還得自己挺住。
限于財力,我沒有能力參與華爾街。但自1980代初起,就開始“近距離”地觀察,歷經1987年10月的股災。當時我在紐約編中文報紙,起初負責財經版。我做的是親大陸的小報(僑社的中文報紙有三大派:反共親臺灣,擁共親大陸,只求賺錢的商業報。以親臺的勢力最大),財經組只有我一個人,選材撰稿起題校對一腳踢。
當時海外的中文報主要是翻炒兩岸三地前幾天的報紙。報道僑居地時,只講華人圈子,不鼓勵僑胞走出華埠、融入大社會。但我因為搞學運才改行做新聞,覺得華人無論住在哪里都不應該固步自封,因此積極介紹華爾街剛開始流行的理財工具,希望改變老一輩把現款塞在床底下謾藏誨盜,或者存活期任由通脹侵蝕的習慣。我開展了這方面的報道后,銀行開始注意,其他中文報紙加入競爭,開闊了華人的眼界。
個人理財工具當時作為新生事物,主要是股票互惠基金和類似現款的貨幣基金,風險低,投資額小,機制明確。投資者有可能會賠,但不會破產。但后來華爾街見獵心喜,創造出大量的投資“衍生工具”(derivative),背后的機制日趨復雜。資產一押再押后,用隱晦的手法和關麗的詞藻彼此推銷,只講回報,避談風險。在股市狂熱中,連最有名的金融機構也互相承受,毫不懷疑。但所有的資產彼此扣連,只要有一個環節大貶值,整個資產鏈就像骨牌那樣沒救。
最近導致全球爆破的一些產品更帶有欺騙性。月初我在港的專欄見報后,一位獲政府高層咨詢的名教授來電,明言他和大學的一些同事也搞不懂最近出事的CDS(Credit Default Swap亦即“信貸違約掉期合約”)具體是怎么運作的。連大教授都不明白,也就是說,無法估計這種工具的風險、爆破后要賠多少錢。我的這位研究院室友一向敢言,經常見報,但現在顯然覺得很無奈。
我與華爾街的接觸不限于新聞報道一有一年多的時間,華爾街距離我上下班的必經之路步行不過5分鐘。我當時住在與曼哈頓一河之隔的新澤西,一周6天,凌晨4點半坐名為PATH的地鐵進紐約,在7年前恐襲中倒塌的世界貿易中心下車,然后走將近半小時回華埠。下午大約兩三點再經世貿坐地鐵回家,世貿倒塌、華爾街海嘯,對我來說就像是老朋友遇難。我近年每次回紐約,都去世貿的遺址憑吊。下次也許還要繞過去華爾街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