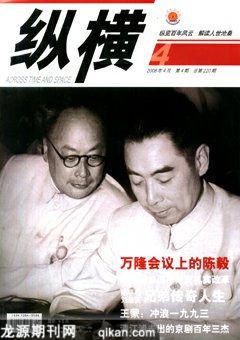沖浪一九九三
王 蒙
1992年上半年,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中國的形勢又有大的發展變化,用一位黨外老人的話來說,叫做“春潮澎湃”。
1993年這一年,我接到幾個邀請:一個是香港嶺南學院現代文學研究所梁錫華(又名梁佳蘿)教授邀我去作一個月的研究交流;一個是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院院長韓南教授請我做特邀學者,到他那里做三個月的研究工作;一個是在意大利舉行的關于公民社會與公共空間的研討會,是由美國賴斯大學本杰明·李教授組織的;一個是新加坡文化部藝術委員會邀我做他們舉辦的“金點文學獎”華文小說組的主審評委;一個是馬來西亞《星洲日報》的邀請;還有一個是臺灣《聯合報》邀我參加他們主辦的兩岸三地中國文學四十年研討會。
于是,1993年便成為了我的游學之年、旅行之年、環球之年、周游世界之年,而且所有這些活動都與我的妻子崔瑞芳一起。
這一年是芳與我第一次同時出境觀景,時芳已經60歲整。我們一起去了新疆,一起去了伊犁,一起去了巴彥岱人民公社,現在我們終于可以一起走出國門,看看世界是怎么樣的奇妙了。
飛往新加坡
出發前有一個插曲,在與新加坡方面聯系我的出訪安排時,我得到了香港方面偕夫人共同訪問的邀請,而訪港與訪新都是往南走,從旅行路線上說宜于合并出訪。最初我與新方友人探討我與妻子同行的可能性的時候,新方遲遲沒有答復。于是我決定單獨一人赴新,然后在香港與芳會合,因為香港邀請的是我們夫婦二人,且已獲準,辦好了有關手續。新方行事很謹慎很嚴密,當他們得知我們夫婦將在香港會面時,立即發出了對芳的邀請。
直到登上飛機,升空飛行數分鐘以后,我和芳才互相祝賀,我們終于實現了雙雙攜手走世界的夢想。

一路上,印象最深的是天上的云:傍晚時分,日落前后,各種白云,形狀極其奇特,有的如蘑菇云,有的如大口袋,有的如一個巨鐘,有的如葫蘆,有的如團扇。平常在地面上,我們仰頭看云,覺得云大體上是平鋪在天上的。而此次坐在機艙看云,卻覺得云是懸掛、站立、垂直在你的身邊。而天色又一點一點地改變著自己的調子,由明亮而昏暗,由潤澤而沉重,由白而黃而醬色而黝黑。
等到了新加坡的賓館,已經是將近午夜,我們又一次相互祝賀起來。
訪問與評獎活動還是很正規的,在宣告評獎結果的會議上,要求每位評委用英語講五分鐘話,我也比較自然地完成了這個任務。
在文學講座中,我聽到一位菲律賓作家的講演,他講到,過去菲律賓作家們的寫作是為了爭取自由和民主,現在,馬科斯的獨裁政權已經被推翻了,作家們的寫作反而失去了方向了。
此話對我并不陌生,因為此前我已經聽到一位俄羅斯漢學家講過,說是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原來要民主要自由,得到了民主與自由以后,不知道自己還要做些什么。
與我講這類話的人中也包括費德林博士,斯大林時期他曾任蘇聯駐聯合國代表,赫魯曉夫時期曾任蘇駐日大使。赫魯曉夫1959年訪問北京,特別調他擔任翻譯。我1984年訪問莫斯科時他任蘇聯作協外委會主任與《外國文學》主編。他90年代初兩次來我家,情緒低沉,反復地說“我們失敗了”。
我也想起了我的一首詩:冬天/盼望著春天/夏天/盼望著秋天/只有春天和秋天最難過/不知道應該盼望什么。(大意)
這次訪新使我們有機會結識了從事慈善救助事業的張千玉女士,她對于一個溫柔美麗的世界與人生的設想,令人感動。她的文字亦極佳。嚴峻苦斗的中國人已經好久沒有接觸過這樣溫和而且良善的文字了。
通過張千玉,我還拜訪了國學大師潘受(又名國渠、虛之、虛舟等),他的書畫詩俱極佳,被新加坡政府授予“國寶”的稱號。我們在潘老師家中用了午餐。我們感受到了一個真正有學問的老人的格外謙和與雅致,潘老的微笑多于評論,聆聽多于講述。他的七律《黃鶴樓》上接崔灝、李白,下臨今日實況,感慨萬端,憂國憂民:
謫仙未敢題詩處,海客狂懷嘯忽開。
芳草空余鸚鵡賦,殘基曾踏鳳凰臺。
剩攜禿筆三生淚,難寫神州百劫哀。
今日倚樓試招手,白云重望鶴飛來。
“剩攜禿筆三生淚,難寫神州百劫哀。”十四個字寫得如此沉痛深沉,寥闊空茫,我算是五體投地。先生生前,無緣朝夕聆教,先生去后,總算不斷地背誦下來了這十四個字。無緣問學,有心攀附,就用這十四個字來咀嚼自己的經驗和所余的日子吧。
張女士有一種真誠的,我要說是東方的基督徒的熱忱。她謙遜也含蓄,但拯救迷途的羔羊的熱忱是永遠熾烈的。她到哪里去常常帶一個大孩子,那個男生曾經流落在街頭,流落在下九流的場所,在張女士的幫助下走上了正路。甚至于到潘受老人那里,她也帶著他,我倒是覺得潘老恐怕不大好理解這種人和故事的。
訪問馬來西亞

接下來訪問馬來西亞,與先父的友人、德國漢學家傅吾康教授有很大關系。他在漢堡大學退休后,常常住在吉隆坡的一所大學里,老年的他受不了漢堡的冬季。傅的女兒在北京時聽說了我要訪問新加坡,便告訴了她的父親,傅教授推動了《星洲日報》對我訪問馬來西亞的邀請。
我們是晚間到達吉隆坡的,報社同仁打著橫幅在機場歡迎我們,總編輯劉鑒銓先生與副刊《花蹤》的主編蕭依釗女士安排著與照顧著我們的訪問。蕭女士的工作作風與待人接物,給我的感覺是異域碰到了雷鋒。劉總與我的交談也是一見如故,他們對于中國的關切與期待,擔憂與親愛,都非常令人感動,也都非常健康和富有建設性。他們的董事長張曉卿先生,祖籍福建,更是一片熱誠,關心中華。我在那里做了一個講座,我國駐馬來西亞大使與夫人,以及使館其他官員都參加了。
還有一點,根據馬國的國情,據說我每天講了什么,他們的安全工作人員都是要寫匯報的,這次,匯報怎么寫一直來問我的東道主,倒也公開化、透明化了。
此前制定的對于中國來客的特殊防范制度與當年的馬共游擊隊活動有關。當年確有許多熱血青年,團結在馬共陳平書記的旗幟之下,意圖以武裝斗爭的方式贏得革命的勝利。后來,游擊隊被剿滅,陳平陣亡。為此吉隆坡街頭修建了一個類似和平紀念碑的雕塑,是紀念馬國對于共產黨游擊隊的戰勝。我們看了,也有所感慨。天地滄桑,人間起伏,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天地不仁,萬物芻狗。豈止陳平,列寧斯大林和突然在中國紅了一兩下的切·格瓦拉,在各自國家,最后又會是什么樣的結束呢?歷史是豐富多彩的,道路是各式各樣的,而個人反而更加顯出渺小來了。世上畢竟有比自己的政見與對于政見的記憶更重要的東西,它們是人類的命運,民眾的福祉,歷史的合力,現實的要求與國家民族的最大利益。
寫本書時,我正在翻譯印度駐華大使拉奧夫人的詩,她有詩云:“我們都是一些面包碎片,被歷史的烘面包片機的不同部位所烘烤。”然也。
我們一起去了檳榔嶼、馬六甲與新山。在檳榔嶼,我們足喝了肉骨茶。在馬六甲,我們領略了那里的“娘惹”文化,一種早期華人與當地原住民的文化混合。在新山,我們參加了華文學校的一個活動,馬國華裔人士對于中華文化的熱情與苦撐,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山毗鄰新加坡,新加坡作家陳美華特意從新趕到,參加我在新山學校的活動。
小憩珠海與煙臺
從馬來西亞回國后,我應邀先到珠海斗門縣白藤湖度假村小事逗留,同行的還有從維熙夫婦、錢鋼夫婦,還有一位老編輯夫婦。我們在那里見到一位斗門縣的老領導,因故被開除了黨籍,改行下海經商。他自己開著一輛“大奔(馳)”,名片上是他任董事長的公司在珠海和澳門的地址。讓人深感時代之不同,覺得他就是黑紅黃三道說的例證。其時已有此說,黑道指搞學術,因為博士帽兒是黑顏色的吧。紅道是指所謂“仕途”。黃道是指經商,金子是黃色的嘛。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的前途也逐漸多樣化了。
十余年后,我突然收到這位朋友寄來的他的講述中國古典詩詞的新作,我心中一動:莫非他不再經商?莫非他經商受挫?不久,見到來自南國的友人,證實了我的想法,他的生意垮了。“文章憎命達”(杜甫),“從來才命兩相妨”(李商隱),這也是一個雙向的過程:第一,文窮而后工;第二,途窮而后文。當然不是絕對。
白藤湖之行的另一個額外收獲是聽錢鋼的夫人于勁講她的關于黎錦光的報告文學。傳主與黎錦熙、黎錦暉是三兄弟,前者是語言學家,是國語注音符號的發明者。我住的北小街46號的原住戶,夏衍之前便是黎錦熙。黎錦暉是作曲家,《可憐的秋香》、《葡萄仙子》等家喻戶曉的老曲子便是他作的。黎錦光也作曲,《采檳榔》、《夜來香》等是他的代表作品。
于勁說她到了黎錦光家中,貧窮自不待言,黎的家人的舉止穿戴也徹底地底層化勞動化非白領化了。這倒是符合把顛倒了的一切再顛倒過來的理念。那么多美好的振聾發聵的理念,實行起來卻發生了與理念背道而馳的效果。而一些說起來美好,實際上卻難見美好的理念卻老是那樣無可奈何地左右著現實。這是多么煞風景卻又多么必須面對的現實啊!
于勁說黎錦光的命險命苦,改革開放后,上海的一個區落實對他的政策,安排他擔任了區政協委員,數月后,他亡故了。大時代的人的命運,形形色色,孰能無過?孰能免禍?
從珠海直飛煙臺,我與芳到中國文聯文藝之家休息并寫作《戀愛的季節》去了。每天上午寫作,下午到二浴場游泳至少一千米,正逢海蜇活躍的季節,有時臉上手上身上到處撞上海蜇。與這邊的作家,原煙臺師范學院院長、作家蕭平,長篇小說的寫作能手張煒,部隊作家李存葆、李心田等都有友好交流。原文化局長劉德璞、副局長郝鑒,也都多有照料。煙臺市政協主席巴忠鼎,多次設宴招待。中國是一個很講究人情的國家,只要國家不出大變故,活在中國,其實是一件舒服的事。
參加在意大利舉行的研討會
8月22日,我應美國一所大學與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邀請到意大利參加一個研討會,接著應哈佛大學燕京學院的邀請到他們那里作三個月的研究訪問。可能是由于雙程機票才便宜,再加分別結算機票的方便,他們安排的是我與芳先飛抵美國哈佛大學所在地波士頓,第二天立即跨越大西洋飛往意大利,再從意大利飛美國波士頓。可這么一飛就累死人了。22日,上午飛機晚點,到上海停留兩個半小時(延長了時間)再飛到東京,再停留近二個小時,中間是否還在阿拉斯加停留,記不清了。反正再飛到紐約,早過了預定飛波士頓航班的起飛時間。面臨最后一班飛機,航站管理人員說是座位全滿了。我們當時真有點筋疲力盡,彈盡糧絕之感。
說明情況后,他們還真是破例為我們騰出了兩個備用座位。過了午夜才到達了波士頓,害得接我們的友人劉年玲也是不知等了多長時間。
睡醒一覺,再上機場,乘英航先抵倫敦的希思羅機場。英航的空中先生極英俊親切,服務周到。希思羅機場的四號站(國際站)也極寬敞。只是轉機等了不少時間,數小時后,終于到了意大利的米蘭。
貝拉吉奧是一個風景區,四面環山,中間是一條更像河流的狹長的科摩湖。山區一處建筑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科研與研討會中心。這里保留著古老歐洲的傳統,每晚要正裝集體用餐。這里喝番茄汁的時候要加沙司、鹽與胡椒。
我最最中意的是湖。除與大家共乘游艇游湖外,我每天清晨起來先下湖游泳。以至一位美國學者向他人講他的經歷,說是他已經起得夠早的了,下湖游泳,忽然遠處出現了一個人頭,把他嚇了一跳,卻原來是王蒙,起得更早,游得更遠。
研討的主題是公民社會與公共空間。會議中人們對于中俄兩國發展變化情狀的比較很有興趣。在人們說到亞洲、東方等概念時,與會的兩位俄國學者則強調他們既是歐洲國家也是亞洲國家,他們的領土有多少多少萬平方公里是在亞洲。他們的論據不由得使我想起赫魯曉夫時期的中蘇論戰,關于蘇聯是否應該參加亞非會議的問題。中國說蘇聯是歐洲國家,不宜參加亞非會議。蘇聯說它有多少多少平方公里在亞洲,所以它必須參與亞洲事務。時過境遷,爭論性質完全不同,論據不變。俄國學者爭的是他們的改革模式,是為了論證他們的改革模式具有跨大洲的普遍意義,論證他們的模式雖然一時效果不佳,但最后,只能是他們笑到最后。這也使我想起中蘇論戰時期關于“蘇聯經驗”的普遍性問題的爭論。何必那么關心自己的道路的普遍適用性問題呢?中國干脆稱自己的辦法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需要也沒有沖動去推廣自己的經驗。
我沒有興趣去比較中國模式與俄國模式的優劣,各國情況不同嘛。只是《大塊文章》中提到過的西班牙老大使,他在1989年離華改任駐俄大使,到90年代后期又回北京任駐華大使,他說,他比較了兩國的道路,相信中國的路子更成功。
我還有一個體會,公民社會啊,公共空間啊,這些提法都非常有意義,對于中國的社會進步與民主政治的發展有很大參考價值,但是這些名詞畢竟來自歐美社會形態與社會政治觀念,有些與中國的情況不完全對榫。而在中國,人們用的掛靠呀,對策呀,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呀,保持一致呀,統一思想呀,放寬政策呀,闖紅燈(現在不提了)呀,松綁呀,加大改革開放力度呀,站得住呀,通得過呀……之類的字眼,也不是歐美人弄得清楚的。又是我們不一樣,We are different了。
貝拉吉奧的面條實在做得太好了。有些國人總以為天下餐飲篤定中國第一,包括有些領導同志也是這樣認為并論述的。這恐怕不能說得太絕對:第一,西餐重選材與原色原味,明快清晰,并不意味著加工不足。第二,西餐的乳制品、甜品、冷食以及番茄汁、鮮檸檬與檸檬汁的使用,葡萄酒的品類與質量,種種酒的香氣,種種飲料的制作與供應,馬鈴薯的制作與種種鮮菜生菜的大量食用,直到某些特定的菜肴,如法國鵝肝、俄國黑魚子、許多種類的牛排(包括肉牛的品種與飼養)大致優于中餐。第三,中餐的爆炒(出了太多的油煙)及大量醬油與食油直到味精的使用,都有可以改進之處。第四,我們的口味當然喜歡中餐,不等于西餐不如中餐。
烹調是我們的強項,但絕不可小覷西餐。例如意大利面條,含面筋比我們多,結實有力,做法也具特色。我吃的一次菜汁蕎面條,拌一點洋蔥花與橄欖油,足以令人銷魂。那天芳想少吃一點,沒有去餐廳,結果旅美學者李歐梵一個人吃了兩份。當然,他到北京來時,我找他去新疆餐廳用飯,拉面條,他也吃了兩碗,他再洋,學問再大,畢竟根在河南,他是河南人也。
研討會的組織者是本杰明·李,他的夫人是小說家、北大1977屆畢業生查建英,查的父親是原北京市委學校支部工作科長、后來的社科院馬列所領導人查汝強,查汝強的前妻鐘鴻曾與我同在一擔石溝勞動,是一個美女右派,文藝工作者。我們與他們的第一、二代人都是,也應該易于成為好朋友。
在美講學
連來帶走五天,我們回到了哈佛所在地波士頓邊的康橋大學城,開始在美國講學的三個月。
這三個月是我們自己租的房子,位于中央廣場附近的法耶特街14號。法耶特,即拉法耶,人們熟知的二戰時期法國將軍。我們租的是一間二層小樓的二層,三室一廳。所謂廳,把客廳、起居室、廚房、飯廳結合、連通在了一起,約有20平方米。三室中大的有12平方米,一個窄窄的雙人床,真不知道人高馬大的美國雙人怎么樣在上面睡;其次的大約8平方米,內放一單人床;更小的不過五六平方米,是電腦工作室。原主人是一名女教授,年近50歲,新婚,與先生去歐洲度蜜月,乃出租此房。她是左翼,是當地反對核武器的代表人物,曾去過蘇聯,并受到戈爾巴喬夫的接見。
這一處房屋雖然不太大,但很實用。我們除了付房租,還幫她照料室內綠色植物。有趣點之一是,大門,二門(即通二樓的門),每一間房門,都有鎖,房東并建議我們出門時所有的鎖都要鎖上,但全部只有一個鑰匙,一樓是另一家,鑰匙也一模一樣。這就避免了例如聽說一位領導分了房,同時掌握了二百多把鑰匙——多么麻煩。也避免了瞎黢黢地換一把再換一把,老是找不對鑰匙。希望美國人的這個經驗能被我們的房地產開發商適當參考。
只是按中國國情與心理定式,一把鑰匙,誰能信得過呢?
陽臺是六角形的,也可愛。走廊里是她與親屬的各式照片,如同家庭圖片展覽。她喜歡收集陶罐陶壺。她的電視機極其一般,尺寸也小。
哈佛燕京的院長時為韓南教授。我們在北京三聯書店組織的活動中首次相識。他翻譯過中國古典作品《肉蒲團》。
這三個月,我主要是寫季節系列第二部《失態的季節》。我在哈佛遠東與太平洋研究中心——又稱費正清中心作過兩次講演,介紹當代中國文學。我記得我特別以80年代韓藹麗與90年代洪峰的同名小說《湮沒》作了比較,悲情的政治傾訴與一種冷漠的自嘲與荒誕的對比,我也講到了新寫實主義的零點寫作與王朔的出現。講到了《爸爸爸》等作品,還有一些爭論,關于文學史分期,關于偽現代派什么的。
我參加過一次中文課,因為該堂課是講我的《夜的眼》。
我到衣阿華大學、耶魯大學、加里弗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馬里蘭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亞洲協會(在華盛頓特區)、華美協進社(在紐約)等地發表了講演。衣阿華大學亞太研究中心聘我擔任他們的顧問,當時中心主任是韓裔的金再溫教授,我們交談得很開心。但是顧問云云,也只是掛名而已。
華盛頓的亞洲協會,聽眾多是外交官或退下來的外交官。聽眾中有前駐華大使恒安石等。
在馬里蘭大學我見到了美國友人李克與夫人李又安,斯時李又安癌癥已近晚期,為了對于中國的關切,她是坐著輪椅來的。他們為中國的狀況與面臨的問題十分擔憂,聽了我的介紹,他們說是好過了一些。
我必須講明,斯時的數量可觀的美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是把中國視若地獄的。有的人甚至想當然地認為我既然已經“出來”了,就不會再回到地獄里去。美國人的自信帶著天真。我看過他們的音樂劇《屋頂上的提琴手》,是寫原東歐的猶太人過著怎樣痛苦的生活,劇本的光明的尾巴,是劇中的人物終于獲準移民美國了,他們次日就要動身赴美,人們充滿了憧憬與希望。布什總統在伊拉克陷入泥潭不是偶然的,按照美國人的邏輯,去掉了大魔鬼薩達姆,送來了美國式的民主,伊拉克人還能不感恩戴德,載歌載舞?從此一步進入了天堂。這也是從天堂的理念出發,構建出了貨真價實的地獄來的一例。
我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少談理念與意識形態,講中國的實際,講市場經濟與有關爭議、日常生活的改變、消費的發展與終被認可、精神面貌的發展、發了財的作家與正在罵娘的作家、自由表達的甜頭與限度、言論的寬泛與貶值、首都出租車司機的論政、電視節目的黨性與電視廣告的覆蓋性、暢銷書與文學、新的民謠、話劇近況,等等。例如,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郭啟宏的本子《天之驕子》,講曹植的事:有一個佞臣向曹丕打曹植的小匯報,曹丕不感興趣,對佞臣說你老匯報他寫詩的事,你也寫一首詩嘛,佞臣第二天給曹丕朗誦自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寫出的歌功頌德之作,曹丕聽完評說:“三分詩,七分吼……”戲劇演到這里,掌聲與笑聲混合成一片。但同時上海的一位共同觀劇的朋友不理解這樣的情節如何能引起掌聲,他們說上海人對這種帶政治性的對白,早已喪失了興趣。
我大講加強相互理解的重要性。我講到深化改革開放的同時保持連續性的必要,防止大動亂的必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精髓的必要。我明確告訴聽眾,要求中國放棄馬克思主義只會引起更大的動亂。問題在于怎么樣理解與解釋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強調的是造反有理,而鄧小平強調的是實事求是。我不懂得為什么美國人不希望中國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精髓。美國人認為當然的事情,到了中國不見得當然,而可能是當然不行。所以要理解而不是煽情。
會場上不斷傳來掌聲和笑聲。他們說,一段時期以來,來講話的中國人不是痛哭流涕的就是跳腳大罵的,他們已經不能想象介紹中國的時候能贏得掌聲和笑聲了。當有聽者問我對于滯留不歸的華人知識分子的建議的時候,我從原則上回答說:回去。中國的事只能在中國辦。我認為如果以不歸為代價定居海外,或者以不出門為代價定居大陸,都是太糟糕了。
有人問我對于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建議的看法,我談到了據云的匈牙利的經驗,他們將過往時代的遺物,集中放到布達佩斯一個“斯大林公園”里,成為一個見證,一批文物,一道風景,一個旅游點。就是說既不必諱莫如深,也不必再煽悲情,引吐苦水。
一位來自祖國大陸的女留學生非要請我們在“水門”公寓附近吃晚飯。她說,我的面孔上有“苦難的痕跡”,而那一位對“公園說”大怒的兄長長著的是一副撲克牌臉。此說有些新意。我回到賓館特意照了一回鏡子,覺得我的臉上的“苦難”可能主要是來自南皮縣潞灌鄉龍堂村的鹽堿地和代糧食品紅薯、近海食品鹵蝦醬。您就看看鄙同鄉張之洞那張倒霉的面孔吧。
從9月到11月底,我們盡情享受了新英格蘭地區的紅葉與橡樹。其間我到明尼阿波利斯與圣保羅雙子城去看望了在那邊讀書的二兒子王石。我學會了許多在美國的生活知識,登記了社會安全號碼(SSN),從而可以更方便地完成完稅、免稅、開戶等財務手續。置辦了信用卡。選擇了往中國打電話最便宜的電話局。學會了電話確認機票與購買必需品的辦法。我們在劇院聽了小澤征爾指揮的馬勒的交響樂。我們熟悉了當地的許多中西餐館。不僅僅是講學,而且也包括了日常生活,我們對美國社會與各種運作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紐約的皇后區,來自臺灣的友人陳憲中先生為我們請來了著名音樂人羅大佑先生與他的姐姐,羅先生一面喝紅葡萄酒一面唱歌,我可真有面子!
同時,也在陳先生家里碰到來自大陸的一位女作家,就是她在1986年讓陸文夫兄大大地晦氣了一回。她請文夫吃完飯讓文夫簽字好拿到什么機構報銷,文夫憤而買單請了她。此次她則聲言正在研究破解六合彩的密碼,就差一兩個數字她就篤定可以得到頭等獎了。她獲頭等獎后,將購買比陳先生家更好的房屋,房子不但要傍山,還一定要靠水。
我順便發表我的感想,還是回到祖國更舒服,更好。你想有助于國家民族人民的進步發展福祉,當然最好與國家民族人民,與這960萬平方公里土地在一起。如果你因故定居海外,常回來看看。如果你一直在國內,有條件的話出去走走。不要治氣,不要較勁,不要想當然地與國家,與故鄉,與時代的變遷,與不同的文化傳統,與世界或者與太多的地域、民族、宗教、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過不去——其實最后是自己與自己過不去。
如今,人的心里應該有個廣闊的世界。頭腦里,文字里,經驗里,閱讀里,思考里都應該有這個世界。有了對于世界的認識與理解才能正確地與有效地堅持自身的獨立自主,才能正確地與有效地應對來自世界的東南西北風雨。鼠目寸光,夜郎自大,抱殘守缺,以封閉愚昧為榮,與唯洋是瞻一樣,日子是不好過下去的。
周揚說過,第一,社會發展是不能夠跨越階段而進行的,第二,一個國家的發展是離不開世界的。
語重心長。
(選自即將出版的王蒙自傳第三部《九命七羊》)
責任編輯:王文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