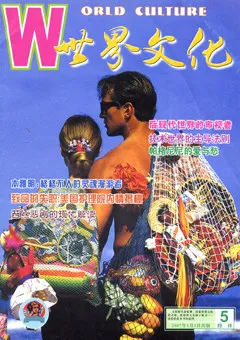技術世界的主導法則
正當人類興高采烈地進入“信息化”、“數字化”時代時,這場偉大的進步也帶來了一系列悲觀性后果。其實,如果我們看看自己的身邊,就會發現,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人們的生活和世界觀都在發生著改變,而有些改變帶來的后果顯然不能算是積極有益的。
如果將20世紀,特別是20世紀末的傳輸革命(即以數字信號、衛星等現代通訊手段為媒介的傳播)與19世紀的運輸革命(即通過汽車、飛機為代表的交通方式)進行比較,那么19世紀的運輸革命顯然使得人們可以比過去更加容易地從一地移動到另一地。這種物理的位移,也就是旅程,從出發到到達,存在著時間的延遲和空間的延伸,這一切使人獲得一種“解放”的真實感。從那時起,人類一直在加快位移的速度,企圖獲得一種對于地球引力的“解放”。20世紀末的傳輸革命使人們能夠不必進行人身的物理位移,就同時在不同的地點“在場”(遠程在場),使整個世界成為一個城邦。信息高速公路甚至還創造出虛擬的現實,這種虛擬的現實使人將真實與虛擬相混淆。
20世紀人類“解放”的極端例子,就是登月,人類登上了這顆過去只能仰望和想象的夜晚之星。此時,由于沒有了地球的重力,沒有了人類過去所熟悉的各種參照,沒有了大氣層所造成的光照的過渡,當執行完登月任務的宇航員門返回地球時,他們甚至對月球上的那段生活產生了虛幻,因而沒有獲得絲毫的真實感。
這似乎可以得出一點結論,即無論是以一種“解放的速度”達到對于“地球-母親的世界”的解放,還是通過信息高速公路實現的遠程在場,都導致人的真實感的喪失。
世界正變得越來越小。多年前,超音速飛機使得世界各地的距離大大縮短,這是19世紀開始的運輸革命的頂峰。而現在,由電視網、電信和互聯網組成的通訊革命也正讓時間延遲消失。
“從真實空間的基礎設施(港口、車站、航空港)的位置到真實時間中由互動的遠程技術學(如電信設施等)導致的對環境的控制,技術學的這一突然轉移,在今天更新著‘臨界的維’”(見《解放的速度》,維利里奧著,陸元昶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以下引言均出自該書)。時間維,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當前的維,已經到了臨界狀態。真實時間的遠程技術所要實現的東西,正如保羅·克利所言:“孤立地給‘當前’下定義就是殺死‘當前’”。它們為了一個可換但不是“具體在場”的別處,即“謹慎的遠距離在場”,把“當前”與其“此時此地”相孤立,從而殺死了它。
無線電技術(數字信號、視覺信號和無線電信號)通過一些笨重的物質裝備(如道路、鐵路等)對領土產生的控制,在今天讓位于非物質的或幾乎是非物質(如衛星、光纖電纜)的控制。這使人類環境的本質、人類環境的領土主體的性質,尤其是個體的本質與其動物性身軀的本質發生了劇烈的碰撞。借助于假器(鍵盤,顯示器,數據手套或服裝),它們使被“超級裝備”起來的健全人變得與被裝備起來的殘疾人幾乎完全一樣。
如果說時間的間隔(積極符號)和空間的間隔(消極符號)布置好了世界的歷史和地理,那么第三類間隔即光類的間隔(無符號,如互聯網)的出現,意味著一個質的飛躍,以及人與其生活范圍間關系的深刻變化。光的極限速度及其穩定性制約著世界的時間延續與空間擴展的現象感覺。至此,光速被用作直接行動和即時遠程行動的絕對標準。“從一個點向另一個點的物理位移,在昨天意味著一個出發、一次旅行和一次到達,運輸的革命已經在上個世紀使這種位移變成對旅行的時限,甚至是旅行的本質的一種逐漸清除,盡管目的地的到達仍然還是一個被位移的時間延續本身所‘限制的到達’”。“在20世紀末,與出發的取消相重合,旅程于是就喪失了構成它的那些相互接續的組成部分,而只顧及到達”。對此,俄國思想家尼古拉·果戈里早有預言:“還沒有出發,人就已經不在原處”。
“這樣一個普遍到達在今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