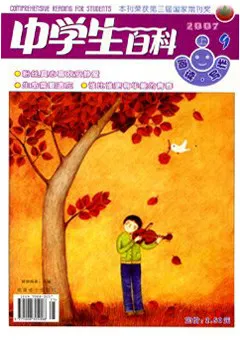夏花燦爛
那一年我只是一個即將中考的學生,什么關于人生的種種喜怒哀樂悲歡離合,只能換算成分數來感受其中的喜悅與失落,零分到滿分,一百零一個整數單位,主宰我所有的人生觀。
唯一的例外是高我三個年級的阿米,面臨考試壓力的我們每晚在校門口公車站相遇,從打招呼到聊幾句,從散步到送阿米回家。五月底學校停課前,阿米在巷子口告訴我,我們得分別專心準備考試。“到這里就好。”阿米說,要我在巷口停下腳步。
GO6RQK7aeuKH+34FeKmiFF+oD2hO7+AlNyUrgL6ZmJ8= 阿米向著巷底的街燈走去,炙亮的街燈將白衣藍裙剪成黑色背影,我看著阿米的背影,說:“那我考完再來找你。”
燈光下,阿米的背影只是一團黑,我覺得阿米轉身沒入轉角似乎曾經點頭,但只是似乎,我無法確定。五月的夜里,空氣中彌漫悶熱的水汽,在我臉上身上覆蓋一層細薄而沉悶的汗水。許久許久,我的視線才逐漸轉移到黑暗中唯一的光源,然后我看見街燈下無數的飛蛾,他們一圈圈繞著街燈,像白炙的燈火吹吐出的一圈圈黑塵。
那是我第一次隱約發覺有些感受不是分數所能表達,有些飄浮不穩定的意義在過熱的氣溫中發酵,氣味蒸騰,不是我未諳人事的鼻腔所能分辨。
三個月后,學姊的哥哥走向守在巷口的我,抓起我的衣領,扯落我的扣子,把我那顆悶出一頭濕粘汗漬的頭往路燈拉近,我才覺得自己與頭頂那一圈圈繞飛尋死的飛蛾同伙。
阿米的哥哥一拳又一拳搗向我的胃,我感到五臟翻轉,口中漫生酸水,無從開口解釋。也就在沉默的同時,我知道自己的行為在三個月之間無端被認定成跟蹤與騷擾。
更離奇的是,我先后進入阿米的高中與大學就讀,大一新人的我與即將畢業的阿米在學校聚會中相遇,阿米好像不認得我了,問我就讀哪所高中,驚訝又親切地握手稱呼我學弟。
而我卻不禁下意識縮起肩膀,防御性地將手收回,口中似乎嘗到一股酸嗆的胃液,熱辣辣地在我喉頭蔓延,最后彌漫成那個夏夜的悶與熱。
過了很久很久,當我終于卸下警戒與防備,才了解阿米只是單純地忘了我。因為不在意而忘記約定,因為無所謂而遺忘曾傷害過一個對她而言并不重要的小男生,只是因為太不重要,我無力附著在她過往的印象中。
因此她面對我一臉笑容,燦爛自在,如一朵盛開的夏花。就像燈火,不會記得,它吞噬過多少起于迷戀終于毀滅的生命。
編輯/孫櫟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