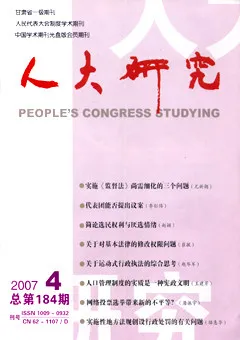實施性地方法規創設行政處罰的有關問題
根據立法法第六十四條有關立法權限的劃分,地方性法規包括三類:即針對地方性事務制定的地方性法規;針對中央專屬立法權之外、中央尚未立法的事項制定的地方性法規;為執行已有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而根據本地方實際情況作出具體規定的地方性法規。由于前兩種沒有直接上位法,理論上把它們統稱為創制性地方法規,而把后一種叫做實施性或執行性地方法規。
從實踐上看,創制性地方法規在整個地方性法規體系中所占比例較小,在行政處罰設定方面也沒有太大爭議。本文僅就實施性地方法規中創設行政處罰的有關問題做一探討。
一、實施性地方法規可否創設行政處罰
所謂實施性地方法規創設行政處罰,就是指實施性地方法規在直接上位法規定的行政處罰之外,增設新的行政處罰。關于實施性地方法規可否創設行政處罰,存在著針鋒相對的兩種觀點,分歧的原因在于對行政處罰法第十一條第二款的不同理解。行政處罰法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法律、行政法規對違法行為已經作出行政處罰規定,地方性法規需要作出具體規定的,必須在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種類和幅度的范圍內規定。”否定論者認為,該規定從行為、種類和幅度三個方面,對地方性法規設定行政處罰的問題進行限制,其中,有關“行為”的限制就是明確否定地方性法規創設行政處罰。因此,實施性地方法規只能對其上位法設定的行政處罰在種類、幅度等方面進行細化,作出更加具體可操作的規定,而不能擴大上位法規定的行政處罰范圍,另行增設新的違法行為并給予行政處罰。肯定論者則認為,實施性地方法規對于其上位法已設定的行政處罰可以細化,自不待言。但對于上位法沒有規定的違法行為,也可以作出補充規定并增設相應處罰。
筆者同意肯定論者的觀點。理由如下:
首先,行政處罰法第十一條第二款并未明文禁止實施性地方法規在上位法既有規定之外另行設定行政處罰。“必須在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種類和幅度的范圍內規定”的前提條件是,“需要作出具體規定”。因此,按照語言邏輯,如果地方性法規不是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行政處罰作出具體規定,而是在法律、行政法規的既有規定之外另行“設定”行政處罰,就不應該受“必須在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種類和幅度的范圍內規定”的約束。否定論者忽視了語言內部的邏輯關系,曲解了條文的含義,是不正確的。實際上,也可以說,條文本身并沒有界定所爭議的問題。
其次,實施性地方法規創設行政處罰是我國立法實際狀況的需要。第一,在我國現行有效的法律體系中,有不少法律、行政法規制定于改革開放之前或改革開放的初期,甚至有些建國初期的法律至今仍然有效。如《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條例》《城市集市貿易管理辦法》等,均制定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農業稅條例》《戶口登記條例》《城市街道辦事處組織條例》 等,則制定于20世紀50年代。這些法律、行政法規立法時的社會背景與當今的社會現實已大不相同,難以適應改革開放后社會經濟狀況的不斷變化。就行政處罰方面而言,當時的規定已經不能滿足或適應現在行政管理的需要。第二,歷史上,我國的立法活動一直貫徹著“宜粗不宜細”的指導思想,許多法律、行政法規只是框架式的或粗線條的,有關行政處罰條款的設計自然也是粗略的,并不能完全滿足各地區行政管理的實際需要。第三,立法者的認知水平總是有限的,并非全知全能。任何立法都必然打上立法者認知水平的烙印。因此,在立法中,對某些領域、某些環節考慮不周,遺漏某些事項、細節,是難免的。還有,我國地域遼闊,各地社會、經濟、文化等情況差異較大,在一地存在或突出的問題,在另一地方則不一定存在或突出。法律、行政法規的制定者必須站在全國的角度,通盤立法,這就難免忽視甚至舍棄局部,使得各地的實際問題并不都能反映到全國的立法上。總之,上述種種因素綜合導致了法律、行政法規在設定行政處罰條款時不可能面面俱到,包攬無遺,為了適應現代行政管理的需要,地方性法規必須對法律、行政法規進行補充。否則,地方性法規本身存在的意義也會成為問題。
再次,從關聯條文的理解和實際運用看,實施性地方法規也可以創設行政處罰。行政處罰法第十條第二款規定:“法律對違法行為已經作出行政處罰規定,行政法規需要作出具體規定的,必須在法律規定的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種類和幅度的范圍內規定。”此條是對實施性行政法規(即為實施法律而制定的行政法規)設定行政處罰的限制。不難發現,它與行政處罰法第十一條第二款的表述方式完全相同。相同的表述應作相同的解釋。那么,是不是實施性行政法規也不能超出法律的規定而另行創設行政處罰呢?我們還是先看兩個例子。《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1999年1月1日實施)第四十四條規定:“違反本條例第二十八條的規定,逾期不恢復種植條件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改正,可以處耕地復墾費二倍以下的罰款。”該條對“不恢復種植條件”的違法行為設定處罰,就是一種創設規定,其上位法《土地管理法》并沒有對這種違法行為進行規定,更沒有設置處罰。再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實施條例》(2000年1月29日發布并實施)第四十六條規定:“違反本條例規定,未經批準,擅自將防護林和特種用途林改變為其他林種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林業主管部門收回經營者所獲取的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并處所獲取森林生態效益補償三倍以下的罰款。”該條“將防護林和特種用途林改變為其他林種”的違法行為,在其上位法《森林法》中也未作規定,同樣屬于創設的行政處罰。這樣的例子在國務院的行政法規中還可以找到很多。既然實施性行政法規可以“突破”法律的規定,創設行政處罰,那么,地方性法規為何不能“效仿”呢?
總之,實施性地方法規創設行政處罰,不僅實際需要,而且理論上和法律上可行。當然,這并不是說實施性地方法規可以隨心所欲地創設行政處罰。在具體立法過程中,我們必須注意我國行政處罰一度過多過濫的事實,準確把握憲法規定的法治精神以及行政處罰法限制處罰、避免濫罰的立法意旨,謹慎為之。
二、實施性地方法規創設行政處罰的種類和名稱
實施性地方法規創設的行政處罰種類有哪些呢?筆者認為,根據行政處罰法的規定,實施性地方法規只能創設警告、罰款、沒收違法所得 (非法財物)、責令停產停業、暫扣許可證(執照)等五類行政處罰(以下簡稱“五類處罰”)。實施性地方法規也沒有理由突破此限,設定其他行政處罰種類。
當然,這里還涉及一個處罰種類與名稱的對應關系問題。一方面,由于立法技術、立法傳統以及行政管理本身的復雜性等,行政處罰法規定的處罰種類與具體法律、法規中出現的處罰名稱有時并不完全一致。如行政處罰法中規定的責令停產停業,在具體法規中可能表現為責令停產(停業)整頓、責令停產(停業)改進、責令改正等;行政處罰法中規定的暫扣許可證(執照),在具體法規中可能表現為暫扣證書、吊扣駕駛證等;行政處罰法中規定的沒收違法所得(非法財物),在具體法規中可能表現為沒收毒品、沒收非法工具(設備)等。這種“一類多名”、“同罰異表”的現象是司空見慣的,應當引起我們的注意,不要把不同的處罰名稱誤作不同的處罰種類而加以排斥。簡言之,實施性地方法規在創設行政處罰時,既不能突破上述“五類處罰”的范圍,又要兼顧處罰種類與處罰名稱不對應的實際情況。在具體立法活動中,做到依法表述、準確表述、靈活表述,同時要盡量與上位法使用的處罰名稱相一致,避免產生歧義。另一方面,我們要注意區分不同類別的行政處罰,避免混為一談。這是因為,盡管行政處罰法僅規定了六種處罰種類,但由于法律、法規可以創設處罰種類,使得實際出現的處罰種類遠遠超過六種。其中,有些處罰種類易于混淆,可能誤以為是“同罰異表”。如通報批評不屬于警告,責令限期治理不屬于責令停產停業等。這就是說,實施性地方法規在創設行政處罰時,不能望文生義,把不屬于“五類處罰”的處罰種類誤以為“五類處罰”而加以設定。
(作者單位:遼寧省沈陽市人大常委會法工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