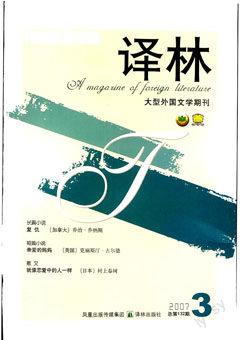向匠人致敬
黃集偉
西德尼·謝爾頓的小說是我多年前念書時讀到的,前后讀過的還有歐文·肖和阿瑟·黑利。謝爾頓的《假若明天來臨》,黑利的《最后診斷》及歐文·肖的《富人·窮人》構成了我對域外流行小說的最初印象。當時,我正在念大三大四,這類書雖然是明白無誤的公開出版物,可一天到晚抱著這些書看,多少還是讓班主任或外國文學授課老師側目——在他們看來,讀雨果、托爾斯泰或巴爾扎克更靠譜,因為在專業考試時,怎么會考《大飯店》或《汽車城》?當然,面對“側目”,我總是假裝渾然不知,繼續和同學們你來我往,沉溺在新鮮刺激而且非常陌生的閱讀經驗中。我記得我買下的那本《富人·窮人》一年后傳回我手里時,已“形容枯槁”。
謝爾頓的小說,包括歐文·肖、阿瑟·黑利的小說,可以被貼上很多標簽——它們是流行小說,也是類型小說;是暢銷小說,同時也屬于流行文化、商業文化的一分子。它們多半伴隨著逐步豐富完善的一整套商業化運作手段促銷推廣,廣而告之……而如上種種,也不過都是些我道聽途說而來的口耳之學,膚淺皮毛,受不起追問,更經不起推敲。作為一個異國他鄉的讀者,我與那些圍觀街頭把戲的看客并無二致,也就一看熱鬧的。
當然,熱鬧看得多了,漸漸有了一些觀感,簡單說,就是那句老話:三十六行,行行出狀元。通俗小說也好,類型小說也好,比起純文學乃至嚴肅文學,不僅境界全無高下之分,而且,就技巧和專業精神而言,更如一口鍋里的菜。老話說,有破東西,沒破活兒。對于一個作家而言,重要的不是你的偉大志向,你諾貝爾文學獎志在必得的偉大宣言,你耿耿于懷的史詩之夢、玄幻之夢、武俠之夢或言情之夢,而是你交出來的作品在技術與專業上究竟是勉強及格還是嚴重超標,說得更直接,那就是,對于一個作家而言,活兒的好壞才最根本。從這個意義上說,通俗或商業甚至要求更刁鉆、更嚴酷。
謝爾頓的小說其實可以被看成如今大行其道的美劇的濫觴,他的小說情節周密嚴謹,人物性格鮮明;而阿瑟·黑利的小說則一直以行業為背景,故事之外,當成某個行業入門小百科去讀絕對受益匪淺;克里斯蒂的小說有一種縝密的邏輯之美,當孩子王時我給娃娃們講“邏輯常識”,它是我頻繁“點擊”的語料庫——林內特小姐的女仆當著波洛探長和西蒙·道爾的面說:“假如那時我沒睡覺,假如那時我還在甲板上,也許我就能看見兇手進入我太太的房間”……這個細節讓娃娃們尤其意外和興奮——原來邏輯推理才是波洛探長的殺手锏。
可以說,在技術和專業態度上,謝爾頓、歐文·肖、阿瑟·黑利乃至于斯蒂芬·金、阿加莎·克里斯蒂之類,是一撥的。包括后來的羅琳,后來的丹·布朗,均為流行小說中的品牌與精英。面對流行小說或類型小說,很多人僅僅仿效其商業炒作的皮毛,卻一直忽略其寫作的技術性與專業精神。仔細想來,這也不奇怪,它與我們社會化過程中由來已久的宏大敘事教育相當吻合,而其實,一個異想天開的偉大夢想必須落實為每一顆擰緊的螺絲釘,就像莊稼漢的田園之夢一定來自于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在第五代電影人里,我喜歡導演張建亞。與他諸多帶有實驗性的電影作品比,我更欣賞的,是他的技術觀念與專業精神。他宣稱,自己是個電影匠人,記者問其緣由,他說:“做這行之前我做過七年的木匠,我不覺得‘匠人是一個不好的稱呼,我覺得我能夠做成一個匠人挺牛的。”
他還說:“現在大家做特技都花錢到國外請外國人做,但是我喜歡自己做,這并不是我想突出自己,我只是抱著一個作為工匠的心態去嘗試。……我還是希望首先成為一個匠人,可能成不了大匠,但是至少不能丟人。”
張建亞的如上闡述證明,這位中國導演跟謝爾頓他們也是一撥的。“如果我寫到一個地方,我肯定去過那里;如果我寫了某道印度尼西亞菜,那我肯定在哪家餐廳吃到過這道菜。我不想欺騙讀者。”上面這話是謝爾頓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的。我曾在一篇報道中得知,在寫《大飯店》的準備期,黑利為了寫好一個細節,專門跑到某飯店工程處,請工人師傅現場演示盥洗間面盆下那根彎管的拆卸與安裝……在我看來,這些對于細部的錙銖必較,這些面對小說細節層面、專業技術層面的精準要求,當然就是一個“匠人”必備的專業態度,可它更是任何一個偉大夢想的落腳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