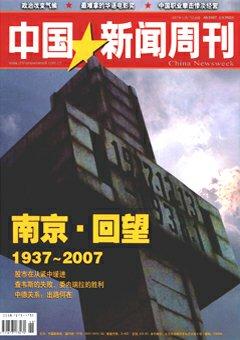中國艾滋病感染者:1000萬?70萬?
李 楯
可能從來沒有一個病像艾滋病這樣在中國有過這么大的投入。它的決策依據是什么?政策實施的投入產出如何?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使哪些人受惠?到了今天,難道不需要從公共政策的抉擇方面做一評估嗎?
前不久,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與世界衛生組織發布了新的艾滋病流行數據,估計2007年全球共有3320萬艾滋病毒感染者,比一年前估計的3950萬少了730萬。
類似情況在中國出現更早,2006年之前,盛行的說法是:2010年中國將有艾滋病感染者1000萬人。2004年,國務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和聯合國艾滋病中國專題組聯合發布的數據是:至2003年底估計中國有艾滋病感染者84萬人。2006年1月,衛生部和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世界衛生組織聯合發布的數據是:2005年中國有艾滋病感染者65萬人,今年12月新發布的數據是70萬人。
就世界而言,艾滋病感染者的估計數從3950萬減到3320萬,給出的解釋是:采用了“經過改進的數據收集和估算方法”。就中國而言,從預言的1000萬,到估計的84萬,到估計減為65萬和70萬,給出的解釋是:“采集數據的范圍擴大”,得到了更為“全面、準確的數據”,以及評估“更加細致、精確”。
看來,沒有錯誤,只有更好。
世界的事,不多說。中國的事,還要講幾句:
2010年中國將有1000萬艾滋病感染者之說,在當時為中國官員、專家、傳媒和國際組織不斷重復,而今卻沒有一個人愿意提及;實在回避不了,就解釋道:“那是說我們什么防治工作都不做,就會有1000萬。”這是應為決策提供的信息嗎?
與2010年中國將有1000萬艾滋病感染者之說同時,一些科學家、院士提出了至2000年艾滋病已給中國造成了4620億~7700億元的經濟損失,至2010年經濟損失將達77000億元。由此導出在政策抉擇上認為艾滋病是關系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國家安全和民族興衰,甚至是國家興亡的事,這些,在今天看來,是否言過其實了呢?
我們對艾滋病在中國的流行及其所帶來的問題的認知和解釋所用的方法都學自國外;我們的一些地方和部門對世界主流的在艾滋病防治中的人權保護和反歧視的理念卻在實際上予以拒絕。甚至我們在行政法規中明確設立的醫療機構不得因就診的病人是艾滋病感染者而“推諉或拒絕對其其他疾病進行治療”的規定也難以落實。
到現在,中國政府在艾滋病防治上動用大筆財政資金,國外也有許多資金投入,二者相加大致不下人民幣幾十個億,可能從來沒有一個病在中國有過這么大的投入。它的決策依據是什么?政策實施的投入產出如何?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使哪些人受惠?到7今天,難道不需要從公共政策的抉擇上做一評估嗎?
決策需要盡可能全面地掌握信息,而由財政投入支持的艾滋病疫情預測的過程是公開的嗎?前述艾滋病疫情預測對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對世界衛生組織、對美國CDC(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是做到了“公開、透明”,但對中國公民卻是“不公開”“不透明”的。在一種聲音過強的時候,日理萬機的決策者能了解數據的形成過程和辨識其可信度嗎?
今日的決策難度日增,因為我們面對的情況越來越復雜。人們的認知和判定能力是有限的,一些決策在后來出現當初始料不及的問題,就證明了這一點;人們的利益和主張是不同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又會影響到他們為決策提供的信息和建議。在這種情況下,只有良好的制度,使各種信息、主張、建議紛紛展現,使決策能夠在比較辨析不同信息、主張,平衡協調不同利益中做出,才能使我們的事做得相對好一些。
現在,問題是:在決策的理念上有些人還停留在過去的時代,拒絕界世的價值理念與規則,在測算數據、處置問題的技術層次上卻盲目遵從外國,使中國的與決策相關的知識生產、制度生產不能和外部的平等競爭,使我們于決策所需的理論、方法、經驗和制度等方面均難得有貢獻于人類文明——在公共政策與治理的層面上,我們的這種落后狀態有待改變。
最后,再說一下決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問題,仍以艾滋病為例:尊重生命,履行國家對公民健康權的積極責任,是遠重于艾滋病會影響“經濟發展”等的理由。中國對艾滋病還應加大投入——但要嚴格審計,講求績效——同時,對預防與治療別的病也應加大投入。財政資金的使用,于各類人群之間,于各種疾病之間,也應均衡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