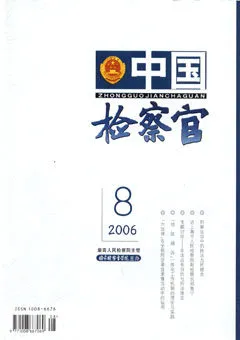“立法崇拜”與“背蒜臼”
我們正處在泛立法主義時代。據(jù)中國法院網(wǎng)統(tǒng)計,2006年1月1日,將有87部法律、法規(guī)、規(guī)章開始實施。其中,國家級法規(guī)50部,地方級法規(guī)37部。看到這則消息我是喜憂參半。建設(shè)法治國家,加強立法固然是無可置疑的。但是,每次人大會都通過那么多法律,每部法律都恨不得“超英趕美”。這一浪高過一浪的立法高潮,我們是否能夠真正承受得起?當前中國所有問題的解決,是否都可以簡單地歸結(jié)為一點:立一部相關(guān)的法律?!在去年的一場申請法學博士學位答辯會上,答辯委員會主席對答辯者強調(diào)了一句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說:“希望你能從多個角度回答我們的問題,但千萬不要說:立一部法律!”后來,由于工作原因我多次到一些基層司法機關(guān)調(diào)研,聽到最多的一句話是:“現(xiàn)在的關(guān)鍵問題不是再立多少法律,而是如何能把現(xiàn)有的法律真正貫徹執(zhí)行好。”
這一浪高過一浪的立法高潮和司法改革高潮,有學者形象地稱之為“立法崇拜”。“立法崇拜”會出現(xiàn)人們經(jīng)常看不到的嚴重后果:一方面是大量的法律文件被制定和頒布,而為了執(zhí)行和實施這些法律,就必須增加執(zhí)法機構(gòu)的權(quán)力或編制,從而造成過分的財政負擔。另一方面,由于形勢緊急難免立法粗糙,往往會破壞原有法律體系的邏輯性,甚至會造成混亂和沖突。既難以整合社會關(guān)系,又破壞了法律的權(quán)威性,使司法人員、執(zhí)法人員、廣大公民和國家都難以承受。所以“立法崇拜”的結(jié)果往往是法律權(quán)威性目標的對立面,法律秩序的好處未得,而弊病卻已先發(fā)生了。這種狀況往往又成為一種進一步“加強法治”的正當根據(jù)和理由,制定新的法律或修改立法,甚至會陷入一種惡性循環(huán)。
在德國歷史上,薩維尼曾經(jīng)極力反對制定民法典,但他并非反對民法典本身,而是反對視法典若兒戲,輒立則立,言廢即廢的天真與輕率。薩維尼關(guān)于法律與立法有過精彩的論述:所謂法律,不外是特定地域人群的生存智慧與生活方式的規(guī)則形式。法律并無什么可得自我圓融自洽的存在,相反,其本質(zhì)乃為人類生活本身。在薩維尼眼中,法律精神一如民族的性格和情感,蘊涵并存在于歷史之中,其必經(jīng)由歷史才能發(fā)現(xiàn),也只有經(jīng)由歷史才能保存和光大。法律隨著民族的成長而成長,隨著民族的壯大而壯大,隨著民族對于其民族個性的喪失而消亡。因此,立法的任務不外乎找出民族的“共同信177abc8247f77185e29fa916174c9224928a3ddbf0df56b75528d066cb00d10d念”與“共同意識”,經(jīng)由立法形式予以保存和肯定。立法可以發(fā)現(xiàn)并記載這一切,但卻決然不能憑空制造出這一切。那種希藉有一個詳盡無遺的立法制度,即刻創(chuàng)制出一個嶄新秩序的企圖,只會摧殘現(xiàn)實,增加現(xiàn)實的不確定性,強化規(guī)則與事實之間的乖張,最終使得法律失卻規(guī)范人事而服務人世的功用與價值。簡言之,薩維尼認為法律蘊涵并存在于社會生活之中、歷史傳統(tǒng)之中、民族精神之中,不能單純地為立法而立法。
盧梭曾經(jīng)形象地把人民和法律的關(guān)系比作土壤與大廈:“正如建筑家在建立一座大廈之前,先要檢查和勘測土壤,看它是否能擔負建筑物的重量一樣;明智的創(chuàng)制者也并不從制訂良好的法律入手,而是事先要考察一下,他要為之而立法的那些人民是否適宜于接受那些法律。”
一談到人的承受力,在我的腦海中就不由自主地浮現(xiàn)出小時侯爺爺講過的一個故事——《背蒜臼》:
古時候,住在平原某村的甲、乙、丙三人,步行了很遠來到了山里邊。那里盛產(chǎn)石制品,尤其是用來搗蒜的蒜臼物美價廉。甲格外高興,就用包袱背了十幾個。乙只背了一個。而丙卻無動于衷。
甲盯著丙,不解地問道:“你發(fā)什么呆?這么好的東西還不趕快多背幾個!”
丙答:“我嫌沉。我準備在路上撿。”
甲大笑:“誰這么傻!這么好的東西會舍得扔?!”
又問乙:“你怎么只背一個?”
乙答:“道遠沒輕載!能把一個背回家就不錯了。”
三人一同踏上了回家之路。
走啊走,一會兒,甲就背不動了,無奈只好扔下一個。
問丙:“你要不要?我只舍得扔一個。”
丙答:“我嫌遠。”
又走了一程,甲又背不動了,只好又扔了一個,丙嫌遠還不撿。
就這樣,走一程,甲就扔一個,走一程,甲就扔一個……
終于,遠遠地望見了村子。甲只剩下了兩個,可又背不動了,心疼地又扔下一個。
問丙:“你要不要?過了這個村可就沒這個店了,反正最后一個我說什么也舍不得扔了。”
丙答:“嫌遠。到村口我才撿。”—甲又大笑:“誰這么傻!到村口了還舍得扔!”
三人終于走到了村口。甲早已累得氣喘吁吁,怎么也背不動了,只好仰天長嘆,將最后一個也扔在了地上。丙撿起來高高興興地和乙回家去了。
我依稀記得爺爺講完后,感慨到:人生之路面臨著許多選擇和取舍,就像是在背蒜臼,不看你開始“背”多少,而看你最后能把多少“背”回家。
人如此,國家亦如此。回顧西方法治國家的法律發(fā)達史,如同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樣,大都經(jīng)歷一個極其漫長的漸進過程。所以龐德才說:“法律必須穩(wěn)定,但又不能靜止不變。”我國的立法完善和司法改革也應當認真考慮公民和國家的承受力,應當慎重對待我國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應當立足于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發(fā)展不平衡的基本國情,而不能好大喜功,搞“立法崇拜”。我們應該記住馬克思的名言: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chǔ)的,那是法學家們的幻想;相反地,法律應當以社會為基礎(chǔ)。否則,再好再多的法律也會變成廢紙,再好再多的制度也會形同虛設(sh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