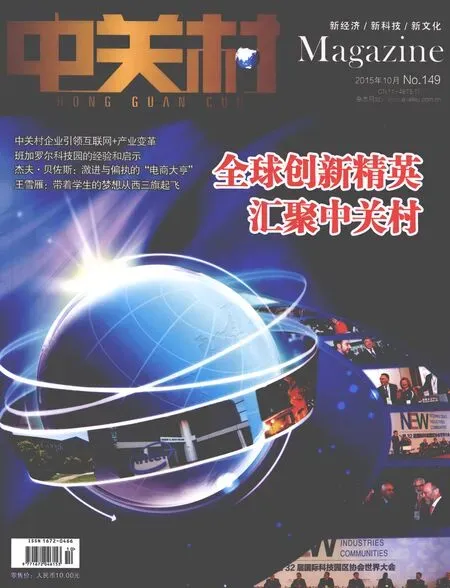千萬個男女生下了你
王宏甲

青藏鐵路終于通車了,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鐵路,像一條云中的哈達,迎接著四海賓朋。它將成為世界上最高遠、最讓人心曠神怡的旅游熱線,也將給西藏發(fā)展帶來空前的良機。它的建成,是半個多世紀來一批又一批開發(fā)西部的建設(shè)者付出非凡努力才有的結(jié)果。有許多前輩英雄已經(jīng)故去,或在老年。我們不能忘記他們。愿此文猶如一條雪白的哈達,敬獻給眾多英雄!
在青藏鐵路工程的總投資中,環(huán)保的投入占15%,這在世界鐵路建設(shè)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國家環(huán)保總局成立了歷史上規(guī)格最高的專家審查小組。在嚴格的管理中有一條規(guī)定,每一列進藏的客車,都必須在格爾木清空車內(nèi)的污物箱、污水箱和垃圾箱。
在雪域高原,為了保障原始生態(tài)與現(xiàn)代文明的和諧,藏羚羊與人類共處,青藏線建設(shè)過程中所有的環(huán)保嘗試和生態(tài)努力,都精心設(shè)計,體現(xiàn)了當(dāng)代中國嶄新的生態(tài)意識。
天邊那條路,遙遙四千里。在未有鐵路前,先有了青藏公路,后來鐵路修到了格爾木,工程要穿越昆侖山,遇到了千年凍土層會隨季節(jié)變化等一系列難題,格爾木暫時成了這條鐵路的終點。當(dāng)青藏鐵路再次動工時,格爾木就成了向高難度的鐵路工程沖刺的起點。英雄的格爾木,無論昨天和今天,都是人們建設(shè)高高青藏路的大本營,是匯聚了一代代開發(fā)者“光榮與夢想”的圣地。
將軍說:你們這些小伙子回家去,每人都搞一個婆娘來,共產(chǎn)黨員要帶頭,這是政治任務(wù)
五十多年前,一位名叫慕生忠的將軍和他的部下,帶著“噶爾穆”這個地名,猶如帶著一個傳說,來找這個地方。噶爾穆是蒙古語,意為河流匯聚之地。將軍率隊從東距西寧市1000多里的香日德向西而行,走過了600多里荒漠,看到的只是成群的野馬和野羊。
有人問:“噶爾穆到底在哪里?”
將軍說:“別找了,就在我腳下。”
為了讓官兵和民工讀寫起來方便,將軍的筆下出現(xiàn)了“格爾木”。
從此,就在這里,在將軍的帳篷升起的地方,就是格爾木。
格爾木突然來了不少男人,卻沒有女人。慕生忠將軍動員部下,給他們下命令壓任務(wù)。他說你們這些小伙子回家去,每人都搞一個婆娘來,共產(chǎn)黨員要帶頭,這是政治任務(wù)。又說,這地方不能沒有婆娘,你們搞來了,好好地干,干出小子來,這里應(yīng)該成為一座城市。
第一批家屬來了。駕駛員說到地方了。她們嘰嘰喳喳地下車了。然后問:“房子呢?”駕駛員說:“一會兒就來。”
女人們望著荒原上的落日,風(fēng)颼颼吹過一望無際的荒原,連一棵樹都沒有……房子怎么可能一會兒就來呢?但是,房子來了。隨后就到的一輛車停下來,卸下一堆帳篷。
篝火亮起來了。格爾木的篝火第一次亮照出女人們的面龐。男人們筑路已經(jīng)筑到昆侖山去了。女人們來到高原的第一個黃昏,主要是由她們自己動手搭帳篷搭到深夜。那就是她們的房子,他們的家。高原的夜風(fēng)狂舞著篝火,亮光搖曳著她們的身影和面容……世上有比這更美的夜色更美的女人嗎?你會不會譜曲會不會作畫?因為有了她們,格爾木才有了兒女情長。因為有了她們,格爾木才變成一個完整的世界。

我們常常嘆息自己或者領(lǐng)導(dǎo)人缺少個性,缺少創(chuàng)造精神,但是某個極富創(chuàng)造性工作的領(lǐng)導(dǎo)人一旦閃現(xiàn),歷史就出現(xiàn)了驚人的美景,荒原會升起一座城市。多年后,慕生忠將軍故去,骨灰撒在昆侖山上。他被高原人尊為“青藏公路之父”。
那是西部當(dāng)代史上的一個壯舉,一首凱歌。當(dāng)年慕生忠將軍所率的那支隊伍,有抗日戰(zhàn)爭時期參加八路軍的官兵,有解放戰(zhàn)爭時期投誠的原國民黨軍政人員,還有原國民黨延安第一戰(zhàn)區(qū)城防司令。此外,絕大多數(shù)是從甘肅、寧夏、青海招來的駝工和民工,最初總數(shù)約在1000多人。這支隊伍稱西藏運輸總隊,負責(zé)從西北為進藏部隊運送糧食。還沒有路,怎么運送呢?所以,最早去踩那條路的是駱駝運糧隊。
藏北,那是世上最高的高原。慕將軍的運輸總隊開始由格爾木上昆侖山,向藏北開拔。從那時起,駱駝的白骨和軍民的墓碑成為一站站通往那里的路標。那不是一次性的奉獻與犧牲,幾十年來,那兒的故事悲壯得難以描述,一如消失在歷史深處的遠征。
我尋訪到了誕生在格爾木的第一個孩子,其父是藏民,其母是漢女。父親叫頓珠才旦,曾給慕將軍當(dāng)翻譯兼警衛(wèi),并有個漢名叫李德壽。慕將軍當(dāng)紅娘,他們于1952年在香日德的帳篷里舉行婚禮,孩子于1953年生在格爾木的帳篷里,成為格爾木第一代居民生下來的第一個孩子。我還尋訪到3位把公路一直修到拉薩的退休老人,他們的姓名是陳玉生,馬正圣,杜善安。那批參加修路回來的人,絕大部分成為格爾木的第一代居民。
何謂救死扶傷,何謂白衣天使?風(fēng),還會把帳篷變成“風(fēng)箏”,把睡中的女護士也暴露在天空下……
當(dāng)格爾木出現(xiàn)街道時,街上最強烈的景觀是一片“國防綠”,穿“國防綠”的幾乎沒有男女老少之分,區(qū)別只在于有帽徽領(lǐng)章或者沒有。因為這里幾乎每個居民都跟軍人有關(guān)系,所以格爾木又被稱為“高原兵城”。
五十多年來一直駐守在這座兵城,并一直在四千里青藏線以及千里格(爾木)敦(煌)線上值全勤的一支部隊叫總后勤部青藏兵站部。如今格爾木電視臺、公園,以及許多政府部門的所在地,是當(dāng)年這支部隊開荒自給的菜地。那是怎樣的開荒呢,那不是在南泥灣靠撅頭和革命干勁就行,那里是沙漠是戈壁,缺的是土,當(dāng)然不是沒有一點土,戈壁灘上能用篩子一篩一篩地篩出土來。另一種大規(guī)模的“兵團作戰(zhàn)”辦法是汽車部隊從遠方拉來數(shù)也數(shù)不清的泥土堆出菜地。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格爾木猶如用拉來的土墊起來的一座城市。

格爾木噢格爾木,人說你是連樹都難以扎根的地方。大漠風(fēng)墻黑壓壓推過來,會把創(chuàng)業(yè)者們種活的整排樹放倒,根爬出地面,看高原的風(fēng)雪紫外線看戰(zhàn)士的淚眼……但今天的格爾木,畢竟是方圓數(shù)百里(有的方向遠達千余里)惟一有樹葉的地方。風(fēng),還會把早年的帳篷變成漫天的“風(fēng)箏”,把睡中的女護士們也暴露在天空下……那些第一代的老大姐是怎樣度過她們的青春的,我們難以想像。
格爾木22醫(yī)院,是由3頂帳篷起家的。我拜訪了當(dāng)年到格爾木的第一位女醫(yī)生周桂珍。她是廣西桂林市人,大學(xué)畢業(yè)的第二年,1956年8月1日坐一輛由蘇聯(lián)嘎斯車改裝的救護車從蘭州出發(fā),在路上,兩千多里顛簸了10天才到格爾木。那年她23歲。
許多早年到格爾木的人,都談到了格爾木的蚊子。周桂珍說,格爾木的蚊子挺怪,光在野外叮人,不進帳篷。在那種荒無人煙的地方?jīng)]有廁所不足為奇,但蚊子太多,而且總是向有皮膚的地方進攻,到野外“方便”就成為難題。婦女們用牦牛尾巴做成了一種趕蚊子的佛帚,出門就帶著,用以驅(qū)蚊。由于那揮舞著驅(qū)蚊的白色佛帚,很像電影上太監(jiān)手里拿的那種東西,看上去就像路上走著許多太監(jiān)。部隊曾多次用飛機滅蚊,加上早期居民的“滅蚊運動”,才使格爾木的蚊子不再對人的基本生活構(gòu)成威脅。
25歲,周桂珍在格爾木生下了本院人員所生的第一個男孩。去到格爾木的第一位女護士長叫賀愛群。稍后來的另一位女護士長黃素坤帶來了一個男孩,有位女護士陳淑華帶來了一個女孩。這兩個孩子已經(jīng)會跑會跳,給22醫(yī)院的創(chuàng)業(yè)者們留下深刻印象。
那時,醫(yī)生護士們用拿手術(shù)刀、注射器的手在荒原上打土坯,自己蓋醫(yī)院。兩個孩子在院子里跑,男孩叫李平,女孩叫白玲。大伙休息時,就逗這兩個孩子。喊“臥倒”,他們就臥倒。喊“匍匐前進”,他們就爬去。“白玲,李平,你們親一個。”還沒有圍墻的院子,你可以想像多遼闊,兩個孩子在天空下,相隔十幾米,跑跑跑,擁抱,親一個。
“不響,再來!”
兩個孩子又退回十幾米,再跑,再親!

“好!”大家都鼓掌。
在這藍天下白手建醫(yī)院的有不少是大學(xué)、護校剛畢業(yè)就到這兒的軍醫(yī)、護士,有不少是結(jié)了婚,丈夫或妻子在內(nèi)地的,大人們看到這兩小無猜的孩子,在高原蔚藍蔚藍的天空下快樂地擁抱、親吻,笑得流下淚來。在那么艱苦的高原生活中,這是大人們的夢想,是內(nèi)心渴望而不能實現(xiàn)的,卻在孩子的游戲中感到了美的震撼!白玲的母親陳淑華沒有活到看見女兒成為母親,是在那艱苦歲月中患高原病過早地獻身高原的女護士之一。
在那些護士的故事中,給我印象極深的還有一位來自江蘇揚州的女護士丁華琪。1960年汽車某團戰(zhàn)士韓錢忠被火燒成重傷,急需植皮,丁華琪站出來對科主任說:“我年輕,皮膚活力強,取我的吧……”科主任說:“小丁,你還沒有談戀愛……”丁華琪已經(jīng)走進手術(shù)室,脫下軍褲,躺到了手術(shù)臺上。兩小時后,從她22歲的大腿外側(cè)取下的一塊15厘米長,5厘米寬的皮膚,移植到了燒傷戰(zhàn)士的身上。
丁華琪也住進了病房。同室一位地方大娘見這位漂漂亮亮的姑娘好端端地割去一塊皮,心疼地問:“你割給他皮的那位是你誰呀?”丁華琪說:“親人。”
丁華琪在中年時轉(zhuǎn)業(yè)回到江蘇故鄉(xiāng),今年該是68歲了,不知她是否一生沒有穿過裙子。何謂“救死扶傷”,何謂“白衣天使”,假如我們承認女護士丁華琪的行為是一種美德,美得驚人,我們就不能忘記她!
也許,最清楚地目睹了那兒的犧牲與悲壯的,莫過于那兒的醫(yī)生與護士。許多年輕的從未有過戀愛經(jīng)歷的戰(zhàn)士,臨死前緊緊拽住年輕護士的手,許多同樣未婚的女護士,把淚水滴在他們漸漸冰涼的手上。那是一支我們很難譜寫的歌!是那樣的艱苦,那樣的壯烈,使那樣的一代護士,成為真正的天使!
和平時代,在這支部隊里,獻身的團職軍官已有18人,這相當(dāng)于18個縣長、縣委書記……
長江源頭第一河沱沱河就在格爾木轄區(qū)內(nèi)。如果不是到了那里,我很難想像,處在沱沱河地區(qū)的官兵怎么連喝水也有困難。
那里有個地方叫五道梁,人稱“鬼門關(guān)”。因為人到那里,互相看看,臉就變出青色來了。那是缺氧輕而易舉地弄出的形象。曾經(jīng)許多年,駐扎五道梁的官兵,每人發(fā)兩條背包帶,一條用于打背包,另一條用于背冰化水。那里的水?dāng)z氏70幾度就開了,放一滴開水到顯微鏡下,就能看到活著的小紅蟲。
那是富有礦產(chǎn)資源的地域,水的硬度很高,水里的有害物質(zhì)超過人體所能接受的健康標準。那水不只有他們自己喝,兵站是為過往部隊做飯,招待住宿的地方,每個過往的人都喝那水,也只能喝那水。
在一切戍邊守土的地方,都是很艱苦的,或缺氧、缺水、缺蔬菜,或寂寞,或紫外線太強、氣候太熱或太冷等等。在這個地帶執(zhí)全勤的部隊,陽光、空氣、水,三大項中沒有一項是滿足健康的。嚴酷的自然環(huán)境,使那里的官兵看上去臉是青的,嘴唇是紫的,眼睛是紅的。

22醫(yī)院的醫(yī)生護士告訴我:“我們并不愛哭,可是每次上線為他們體檢,經(jīng)常是哭著為他們抽血。因為嚴重缺氧造成的血濃度增高,會致使抽血體檢時血液凝固最大號的針頭。護士不得不用輸液的鹽水,推進血管,稀釋血液,然后馬上抽出的血液是醬黑色的。”血液粘稠度嚴重增高,會不可避免地造成對心臟和肝臟不可逆轉(zhuǎn)的嚴重破壞。
1986年,拉薩大站政委郭生杰,因肝萎縮從發(fā)病到死亡總共45天,終年46歲……拉薩,那是四千里青藏線的終點,團政委郭生杰病倒住進西藏軍區(qū)總院的第二天,醫(yī)院就報了病危。他都不相信自己很快就會死去。躺在醫(yī)院里,他最放心不下的是獨自一人在西寧的聾啞學(xué)校上學(xué)的啞女。
郭生杰18歲從陜北的窯洞來到格爾木的地窩子,在高原28年,從戰(zhàn)士到團政委,沒有人能說清他經(jīng)受過多少暴風(fēng)雪的襲擊。妻子劉秀英是他的同鄉(xiāng),18歲嫁給郭生杰。早年,妻子還不到隨軍資格,他在青藏線上帶著汽車連奔波,妻子帶著子女就在陜北的黃土地上艱難生活。熬到隨軍,也難得團聚。妻子在格爾木,離他2000里,格爾木沒有聾啞學(xué)校,女兒是啞巴,可女兒10歲了,該上學(xué)了。父親沒空,母親獨自把女兒送到西寧的聾啞學(xué)校去寄宿讀書。
還記得4個月前,他到西寧開會,匆匆地去看了一次女兒,女兒在聾啞學(xué)校離母親2000里,離父親4000里,一年到頭難得見到父母,一下子撲到父親身上就哭了。不會說話的女兒,哭泣的聲音跟會說話的孩子哭泣是不一樣的,哭聲婉轉(zhuǎn)有無限傾訴,當(dāng)團政委的父親也淚流滿面。
但是,只能匆匆一面,父親甚至沒有帶她上西寧的大街去轉(zhuǎn)一轉(zhuǎn)買點什么,就要分別了。分別的時候,已經(jīng)12歲的女兒咬住了哭聲,淚水汪汪地舉手跟父親再見……這是一個從小就學(xué)會的動作,她生在高原的軍營,還被抱在母親手里的時候,車隊出發(fā),就有家屬抱著孩子到營房門口來送行。
“再見!跟爸爸說再見!”在這里,這是一句祝愿,一句吉利話。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線,年平均氣溫在零度以下,冰封雪阻,什么樣的危險都可能發(fā)生。女兒說不出來,但女兒從小就學(xué)會了“再見”這個動作。西寧匆匆一面,爸爸又要走了,啞女含淚舉手再見,這是對爸爸的祝福!現(xiàn)在,這一對父女,一個在青藏線的起點,一個在終點,遙隔4000里,還能再見一面嗎?
為搶救政委,有20多名戰(zhàn)士先后為政委獻了血。1986年6月1日,這是郭生杰住進醫(yī)院一個多月后,還記得今天女兒該過兒童節(jié)了。6月3日,為政委輸血的針頭已經(jīng)流不進血液,傍晚,郭生杰政委去世,拉薩的天空依然是那么藍。

妻子劉秀英隨軍后在軍中的家屬縫紉組為軍人縫補衣服,在軍營的加工廠、軍人服務(wù)社都干過。丈夫去世后,組織上把她調(diào)到西寧,以便照顧啞女。與此同時,在格爾木讀書的男孩也轉(zhuǎn)學(xué)到西寧,入學(xué)時參加考試,百分制,孩子才考了幾分。劉秀英自己在陜北農(nóng)村只讀到四年級,現(xiàn)在丈夫去世,留下啞女,留下學(xué)習(xí)成績很差的兒子,秀英抱著兒子才考幾分的成績嚶嚶地哭了:“生杰,我怎么辦啊?”
總算有一個女兒長大后考上了西安第四軍醫(yī)大學(xué),1990年畢業(yè)時,根據(jù)總后勤部對老高原子女的特殊照顧政策,女兒郭莉敏可以分配到北京的解放軍醫(yī)院工作。但是,劉秀英卻要求讓女兒回來。
我見到劉秀英時,她告訴我:“兵站部的部長王根成把我叫去,罵了我一頓。”她說王部長說:“人家花錢要調(diào)北京還去不了,你把女兒要回來?”劉秀英說:“我沒辦法,還有一個啞女沒工作沒出嫁,我一個人怎么辦?”部長說:“你就為了你自己,不為女兒前途著想?”劉秀英于是流著淚說:“好吧,我不叫她回來了。”
可是,女兒撇不下守著寡拉扯幾個孩子長大的母親,寫信回來說:“媽媽,我從小在高原長大,我也就支援了邊疆吧!”女兒自己去要求分配回來,至今在高原醫(yī)院。
缺氧,高山反應(yīng),是到那里戍邊的官兵每個人都要經(jīng)歷的嚴重事件。“當(dāng)兵就是做奉獻。”在那里,這話不是什么宣傳,是事實。即使當(dāng)兵當(dāng)?shù)綇?fù)員轉(zhuǎn)業(yè)了,帶著被高原改變了的身體回故鄉(xiāng),仍然可能要付出很大的犧牲。
青藏兵站部政治部副主任劉進山,1945年在河北入伍,1959年到高原,離休時組織上把他安排到西安干休所。從西寧搬到西安的當(dāng)天,因行李還沒打開,他在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在自己家中住了一夜。分給他的房子很好,是有浴室的,他很滿意,只是這天還沒有來得及在那浴室里洗個澡。第3天發(fā)病,住進了醫(yī)院。第38天,住進了太平間。他因肝硬化腹水死亡。他的兒子劉洋告訴我,他的父親臨終前對他說:“如果我能在干休所的房子里住上一個月,我也心滿意足了。”又說,“如果我能在自己家的浴室里洗個澡,我也心滿意足了。”劉洋也在他父親戰(zhàn)斗過的青藏線上服役。
今日格爾木有機場,那機場首先是軍航。要建鐵路,當(dāng)年國家鐵道部門的領(lǐng)導(dǎo)人說:這樣的事,只有找軍隊。
軍隊開進去了,那是建設(shè)青藏鐵路的開端。開進去的部隊是鐵7師和鐵10師,如今那高聳入云的隧道群,那留在戈壁上的軍人墓群,那挺拔的一雙鋼軌,就是這兩個師留給高原的形象,是他們真正的紀念碑!
那墓群中還長眠著他們的一位師長,師長是在鐵路修到格爾木,工程即將竣工時去巡檢工程翻車而亡。我找不到他的墓,也不知他的姓名。那兩個師在鐵路修通后就奉命集體轉(zhuǎn)業(yè)了。
格爾木人目睹了那次告別,當(dāng)近萬名軍人向軍旗告別,集體脫軍裝時,很多人都哭了,那是很悲壯的啊!盡管曾經(jīng)多么艱苦,當(dāng)兵的歷史中也一定有過委屈,他們?nèi)匀粣鄄筷牐鞘撬麄兩凶哌^的很不平常的歷程,沒有辦法不愛。
還會被人提起的,多因他們曾有過女人。高原軍中因之有不斷壯大的“寡婦營”
格爾木烈士陵園不是戰(zhàn)爭年代的產(chǎn)物。還有些軍人,未葬在陵園。在青藏線路況、車況極差的歲月,譬如20世紀60年代,他們在氧氣也吃不飽的地域為國家建設(shè)拉礦石的歲月,部隊曾經(jīng)常常在半道上開追悼會,因為尸體不是礦石,他們無法把死在途中的戰(zhàn)友拉回來,只好就地埋在昆侖山、埋在戈壁灘……沒結(jié)過婚的當(dāng)然也不會留下后代,許多人有墓無碑,日久連墓也不存,連名字也沒有留下,他們真是奉獻得太徹底了。
還有會被人提起的,多因他們曾有過女人。高原軍中因之有不斷壯大的“寡婦營”。那些大嫂們當(dāng)初在故鄉(xiāng),說起隨軍叫“跟著男人吃政府飯”,并為此感到光榮和激動。千里隨軍隨到格爾木,才知丈夫還在千里外的險要駐地,來此還當(dāng)牛郎織女。“依俺的心思,一家人在一口鍋里吃飯就是幸福,哪曉得唐古拉離這兒,比俺在老家上趟省城還遠。”這不是哪一位大嫂的話,她們到了格爾木,才知在這兒當(dāng)兵即使當(dāng)?shù)搅塑姽伲赃@“政府飯”也太難太難!
來探親的妻子也只能住在格爾木,然后由部隊跟她們在線上的丈夫聯(lián)系,讓千里下山來相會。80年代,一位名叫茶花的4歲女孩跟媽媽來看爸爸,她爸爸姓樊,在千里外海拔4700米的安多泵站,泵站正有替西藏緊急輸油的任務(wù),一時下不來。茶花跟媽媽在格爾木等了一個多星期,媽媽的假期快不夠用了,母女就跟著運輸車越過唐古拉山口,到達藏北安多,4歲的小茶花卻怎么也搖不醒了。小茶花終于沒有見到她的爸爸,高山反應(yīng)使她再也沒有醒來。
從此軍中多了一條禁令:禁止來探親的婦女和孩子越過海拔4500米的高度。可是,對親人的想念,總是一再有家屬越過這條禁令。1989年11月,一位叫張明義的軍官的妻子,帶著一歲零一個月的男孩和氧氣,又越過唐古拉山口,一家人在安多團聚了。但是,小孩突然感冒。在那里,感冒會迅速引起肺氣腫,就是要命的病。軍車十萬火急連夜往格爾木送,才送出200多里,小男孩停止了呼吸。
母親抱著那孩子長行千里到達了格爾木,仍然不松手……直到把母親和孩子再送到22醫(yī)院,請大夫再三檢查,確認是死了,母親突然一聲哭出來,所有在場的軍人都下淚。
那孩子就葬在格爾木烈士陵園。張明義所在部隊的全體官兵參加了葬禮。格爾木冬日的風(fēng)雪中,幾百名軍人和一位母親站在一位一歲零一個月的男孩的墓前,這是一支部隊所能表達的全部心情!
兒當(dāng)兵當(dāng)?shù)胶苓h很遠的地方,兒的婚事掛在娘的心上……幾乎每一個士兵的婚姻路線,都是娘,是爹,是親戚朋友,為他們在故鄉(xiāng)的小路上,一趟趟東奔西顛踩出來的。
格爾木汽車3團有個汽車兵,叫郭群群,一米八的大個,當(dāng)兵4年多還沒有回過家。1983年元月,他被批準回家去成親,還不知將要結(jié)婚的妻子是啥模樣。請不要驚訝,很多大兵都是這樣,像他們的父親和祖父一樣,到成親的那一天或前兩天,才見到那個要成為妻子的姑娘的面。
就在這時,有個加運任務(wù),要給西藏運年貨。連長說:“回去探家的人大都走了,你跑一趟吧,回來你就走。”郭群群沒啥說的,開著車就上路。
那是隆冬1月,青藏線上氣候最惡劣的季節(jié)。車到唐古拉,遇到暴風(fēng)雪,天地混沌一色,嚴重缺氧,不但人缺氧,車也缺氧,一缺氧,汽油燃燒不充分,車也受不了,車拋錨了!
饑餓、嚴寒,郭群群胃穿孔。唐古拉山口,那是世界最高的山口之一,往拉薩去還有一千里,送回格爾木也有一千里。又遇到雪阻,送不下來,郭群群死在途中了。
3團的一位中尉軍官奉命去這大兵家鄉(xiāng)處理善后。郭群群的老家在陜西秦嶺腳下。中尉坐了很久的車,坐到?jīng)]有路了,就走。又走了很遠的山路,找到了群群在山溝里的家。
這位軍官告訴我:“那家,破舊得我沒法跟你說。”他說一眼望去,整座大屋,最新的就是大屋正中一個大酒缸。不,最新的還是缸上貼著的一張菱形大紅喜字,是個紅雙喜。
“我不敢進門了,進去咋說?”
可是必須進啊!郭群群的母親近60歲,幾乎失明的雙眼深深地陷在眼窩里,聽說部隊來人,老母親用手來摸中尉。“群群呢?”老人問。
當(dāng)聽懂了兒子的消息,老人呆住。然后顫巍巍地走到那個大酒缸邊,雙手去摸酒缸,然后突然用巴掌使勁拍打著那大缸,一下又一下,使勁拍,邊拍邊泣道:“群兒,娘給你找到媳婦了,你咋不回來呢……”
中尉拿出500元撫恤費,600元生活補助費,雙手捧給老母親。母親叫著群兒他嫂的名,說:“收下吧,讓群兒他哥再借點,加上,到山南去買頭牛,開春耕地。”
軍官告訴我,他哭了。他說他也是農(nóng)民的兒子,家里也有老母親,他本該知道一頭牛的價格,但他沒想到這事,這事像一道閃電劈在他的心上,他把旅差費掏出來,顧不上他怎么買票歸隊。他說:“我沒想到我?guī)斫唤o群群他娘的錢,還不夠買一頭牛。”
可是老母親堅持不收:“按部隊的規(guī)矩,咱不能多收。”軍官就跪下去了:“娘,娘,這是我的錢,也就是群群的錢。”
請不要震驚,這只是一個大兵的故事,一個母親的故事。
在高原,僅總后青藏兵站部這支部隊,在新中國的和平年代,已有680多個大兵,永遠長眠在他們?yōu)橹?wù)的4000里青藏線上。
“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這話出自那里,既不是豪言壯語,也不是牢騷怪話,是一句實話。許多年輕寡婦,帶著孩子,繼續(xù)在高原為吃不上蔬菜的軍人磨豆腐。那里有第一批來到高原,在那夜色的篝火中搭帳篷的家屬……大漠孤煙直,野火燒枯桑;門前樹又綠,丈夫不復(fù)還。悲壯乎!
還有父母雙亡的軍人兒女,在格爾木街頭賣酸奶,在館店端盤子,在舞廳陪人跳舞……是許許多多只能用羌笛用馬頭琴去吹彈的故事營造著高原的經(jīng)濟市場。更多的,成千上萬的軍人,帶著各種高原病,帶著因凍傷凍殘路險車翻而被鋸掉的斷肢凱旋……大道通天噢云飛揚,勇士歸故鄉(xiāng)噢,親娘淚千行。悲壯乎!
但是,青藏高原向現(xiàn)代文明走來了。
黃河,長江,都從這里起步,九曲回環(huán)飛流直下,流過萬家門前。不管怎么說,這是我們的祖國
通往拉薩的鐵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鐵路,火車飛越千里戈壁,萬丈鹽橋,飛越兩山之間橫空穿行的鋼鐵天塹,請想像一下吧,那是北京人在地面看見飛機只有一丁點兒在高空中飛行的高度。
五十多年前,格爾木還沒有一間屋。如今已是青海省第二大城市。若看格爾木市的轄區(qū),總面積12萬多平方公里,北京市區(qū)包括所轄區(qū)縣的總面積是1.68萬平方公里。格爾木市有7.5個北京市大,是世界上轄區(qū)面積最大的市。如果沒有格爾木,就沒有青藏公路,青藏鐵路的修建也不可思議。今日格爾木正以非凡的速度,發(fā)育得頗像歷史上的敦煌。
從格爾木北去千里就是敦煌。那條公路也是50多年前軍人與民工共同修通。從敦煌西出陽關(guān)就通西域,古絲綢之路是由經(jīng)濟交流帶來文化諸方面的發(fā)展,才有了漢唐的輝煌。西部高原有200多萬平方公里,這是近“五分之一的中國”。一條青藏公路和鐵路,它已經(jīng)產(chǎn)生和仍將產(chǎn)生的作為,對繁榮西部高原經(jīng)濟,從而實現(xiàn)中華民族全面的振興,其歷史和未來仍將產(chǎn)生的偉大意義,堪與古老的絲路共光輝。
今天,當(dāng)我們聽到為青藏鐵路通車奏響的凱歌,不能忘記所有的凱歌都是用青春、熱血和生命去鋪排出音符。當(dāng)然,前述的極其艱苦狀況,經(jīng)軍隊和一代代軍民極大的努力,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有了很大改善,青藏線上每個兵站都有樓房,有暖氣。嚴重缺氧的地段,往士兵的宿舍里供氧氣。進入90年代,官兵英年早逝的情況已被改變。
但大自然的艱苦狀況仍然放在那兒,青藏線上不化的冰雪、缺氧的大氣候,仍然放在那兒。直到今天,在海拔最高最艱苦,千里不見一片樹葉的唐古拉地區(qū),看看士兵在營房里栽培出那么多美麗的花,為那些花,士兵把配發(fā)給他們的維生素片也拿去溶化了養(yǎng)花,你會不會感動?世上再沒有比他們更渴望綠色,更愛鮮花的人了!格爾木,那方圓百里、千里惟一有樹葉的地方,仍然不斷在種樹。沒有人能說清那兒的樹,一棵該值多少錢。看一棵樹活了沒有,要看3年。誰敢砍一棵樹,“我槍斃你!”當(dāng)荒原成為我們生存的依靠,你不愛它,怎么辦?
即使在最艱苦的歲月,也有嬰兒誕生。格爾木,是這樣一天天長大。是千萬個父親和母親生下了你,也是千萬個從未成為父親和母親的少男少女生下了你,孕育了你!
(作者系著名作家,著有《無極之路》、《智慧風(fēng)暴》、《新教育風(fēng)暴》、《貧窮致富與執(zhí)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