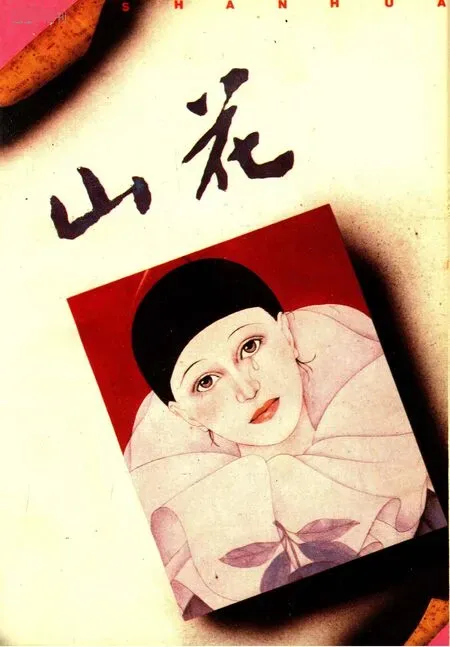回歸生活,改變詩歌
魏天無
“改變你的語言,必須改變你的生活。”2005年首屆平行文學獎頒獎期間,沃爾科特《遺囑附言》里的這句直白,被拓印在平行詩人們的體恤上,顯影在洪湖大澤的藍天碧水間,既傳達了他們對詩歌的新的體認,也顯示著他們試圖改變詩歌寫作風尚和潮流的勃勃雄心:必須跳出語言的藩籬,必須回到生活的源初。
作為網絡詩歌論壇的新生兒,平行論壇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已經在許多方面展示了它的與眾不同。一方面,每一位初上論壇的人,都會驚訝于這里的安靜:交流和爭鋒隨時在進行,但這一切都是源于詩歌、為了詩歌,沽名釣譽、謾罵攻擊在這里是絕沒有的。這在惟恐不熱鬧、竭力求人氣的形形色色的論壇中,不啻于一個另類。安靜并不是平行論壇刻意營造的效果,毋寧說,安靜來自詩人的底氣和大氣,來自他們更為高遠的寫作抱負,而不圖一時之快,逞一時之能。因此,聚集在論壇上的詩人都沉浸于寫作自身的痛苦和歡樂中,對附著于詩歌之上的贅余無話可說。另方面,以松散的方式結合在一起的平行詩群中的代表者,如張執浩、余笑忠、韓少君、李以亮等,其寫作旨趣和語體風格又被公認是各各不同的。雖然他們與網絡的連系或緊或疏,從網絡寫作中獲取的收益有大有小,但面目清晰可辨,以至很難“匿名”于論壇。不過在我看來,有志于在詩歌、包括網絡詩歌上作出探索的這群詩人,其區別于其他同人的最重要的一點,是以溫和的而非激進的、真誠的而非矯情的態度,重新擺正了詩歌與生活的關系,并對此予以了看似尋常卻別有深意的闡釋。如同張執浩在論壇宗旨里所言:“那些試圖用寫作取代生活的人不是平行者,同樣,那些認為生活大于寫作的人也不是平行者。所謂平行,首先是與生活保持一種恰如其分的對等關系,既是毅然反抗,又是當然承擔;既從容,又緊張;既明知無望,又矢志前行。”
不知從何時開始,詩人們已不太愿意談論詩歌與生活的關系,取而代之的是對詩歌與語言、繼而是詩歌與文化問題的津津樂道;詩評家們也競相追奇逐新,放棄了本應肩負的質疑、究詰習焉不察、曖昧不清的常識性問題的職責。簡言之,將生活視為任意一種寫作的理所當然的前提,因而忽視了不同的生活,個人的不同的生活觀,以及對于寫作應該呈現什么樣的生活,對寫作所發生的重要的、甚至是關鍵性的影響,是當代詩歌積重難返的痼疾;網絡詩歌對所謂寫“個人生活”的極端化,對“語言操練”的極度癡迷,進一步加劇了這種趨勢。時至今日,詩歌生存的危機依然如故,并沒有因為詩人們的強辯而稍有減弱,而這種危機其實來自詩歌自身,來自它對生活的拒絕和蔑視,來自它對人的鮮活生活的無足輕重、無關痛癢。這樣的詩歌無論是出現在紙介媒體還是網絡上,無論是貼上“貴族”的還是“平民”的標簽,都不能擺脫自生自滅的命運。誠然,自“工農兵文藝”興起以來,生活一詞一直被視為外在于寫作者的,隸屬于工農兵、意識形態,現在也叫做“主旋律”的東西,我們對將生活一詞根據政治風向和時勢的需要肆意玩弄于股掌的文學和批評的歷史記憶猶新;也誠然,沒有人否認詩歌是一門語言的藝術,否認語言的邊界就是世界的邊界。問題的實質是,語言的磨練與成熟,語言呈現世界的自足性,是不是寫作者在封閉的居室里、在文本的研讀中就可以完成的,與個人實在的生活全無瓜葛?究竟該如何理解詩人在語言上的創造性?可以明確的是,語言是先于個體寫作者存在的,是隨著時代和社會生活的變遷而發生變化;個人生活的遷移,人生體驗的積累,會直接作用于一個人對語言的選擇和運用。在西方現代詩歌傳統中,T.S。艾略特就非常強調詩的語言與詩人所處時代的語言的密切關系,主張詩人應當使用他最熟悉的語言來寫作,認為語言的變化從根本上說是思想和感受性方面的變化。而在中國傳統詩歌中,詩人的個性、氣質是在時代精神、個人際遇等多重影響下歷練而成的,而這一切又莫不微妙奇特地滲透在詩人對詩語的推敲、咀嚼上。當然,傳統中國詩論更加關注文與人的對應關系,主張詩歌應該包容更形豐富而復雜的人生體驗,以真切的性情、獨特的個性引發閱讀者的共鳴,以實現社會性的效果。在詩歌上的純形式主義觀念,所謂語言的“自足”論,并沒有成為中國詩歌的主流;這一點,對于今天仍然堅執于“語言游戲”或“游戲語言”的詩人,至少是一種提示。因此,對于近年來呼聲漸高的“回歸傳統”的主張,我更樂意理解為重新回到對詩與生活關系的審視上。
沃爾科特的直白之所以于平行濤群心有戚戚,是因為它表述了一個簡單的真理:是生活的改變帶來語言的改變,從而改變文學的面貌;而不是相反,認為文學的改變取決于語言,而語言問題被想當然地看作是文本“內在秩序”或詞語組合的好壞。這是平行詩群同人給我們帶來的啟示,雖然這遠非一個獨創的、新穎的話題。我相信他們各自對于生活—語言—詩歌的具體看法不可能完全一致,不過,集中展現在這里的詩歌,出人意料地體現出他們在關注現實生活和個人生活經驗,特別是在既目光向外又反躬自省方面的一致性,而其藝術手法又帶著他們各自的痕跡,讀者諸君自可細評。“我有渺小的痛苦,我有蒼白的生活”,生活的不同,或者,對生活體驗的不同,對詩與生活關系體認的不同,構成了“你們”與“我們”的不同。確實如張執浩詩中所隱喻的,在生活這片熱氣騰騰的沃土上,詩人要逡巡,要俯首,要有貪婪的欲望、擴張的野心,以成為一個無法撼動的“嶄新的地主”。
眼前這塊土地熱氣騰涌
多少草木奔走相告:和風雖好,但我們還需要
一個嶄新的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