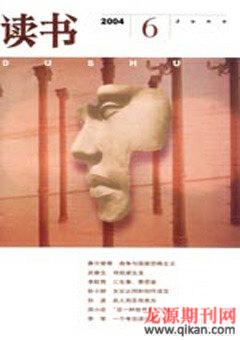一個華夏邊緣的歷史人類學研究
祁進玉
族群與族群關系是當代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研究的主題。究其原因是全球化、現代化的發展,使得不同的人群聚合在一起,或者使不同群體的接觸更為頻繁,族群與其他各種組織和群體交織在一起,構成了復雜的、多元的文化。在這種格局下,族群內部成員的適應,族群之間的協調不僅影響局部地區,甚至波及到全球。從持續半世紀的中東沖突到近來南斯拉夫危機,都說明了族群之間的沖突和協調成為當代的首要問題。
族群(ethnic group)一詞最早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使用,對于它的定義,今天仍有很大爭議。在概念上,族群與民族有一定的區別。民族一般是指被制度化了的族群共同體,而族群則僅指一種人群范疇。吳澤霖主編的《人類學詞典》對“族群”的解釋是:一個由世族和種族自己集聚而結合在一起的群體。
臺灣學者王明珂先生的新作: 《羌在漢藏之間——一個華夏邊緣的歷史人類學研究》是在《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的基礎上,更深層次研究現代羌族民族史的構建及其歷史、文化的變遷來詮釋“華夏邊緣”的歷史民族志。作者在前言中提到,《羌在漢藏之間》以在人類資源分享與競爭關系及其社會、文化與歷史記憶上的表征,來說明人類一般性的族群認同與區分。進而,基于對“族群”(或民族、社會)、“文化”與“歷史”的新的理解,作者對于當代漢、羌、藏之間的族群關系,或更大范圍的中國民族的起源與形成問題,提出一種新的歷史人類學詮釋。
羌族,目前約有二十二萬人,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的東南隅與北川地區。它的南方是分布于川、滇、黔三省,人口約六百五十八萬的彝族。它的西方是人口四百五十九萬,分布于中國四分之一土地的廣大藏族。它的東方則是更廣大的漢族——可能是全世界宣稱有共同祖先的最大族群。羌族民眾也常自豪地稱“我們族是漢族、藏族,彝族的祖先”。何一個當前人口不過二十萬的民族,可以使十多個民族聯結在一起?這也是作者自一九九四年開始進行至今的羌族田野考察工作的初衷。他先后八次進入岷江上游與羌族分布聚居的北川地區做田野調查,累計約有十一個月。除了觀察、記錄當地的一般民族志資料外,他最重要的活動是問村民一些簡單的問題,并做口述錄音。作者通過經過設計的主題與問題,以及他與羌民民眾的對話產生文本。“異文化”研究和人類學解釋性的重新思考,引起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對民族志的文本加以分析、解剖和批語的潮流。一九八二年《人類學年鑒》發表馬庫思(George Marcus)和庫思曼(Dick Cushman)名為《民族志作為文本》的文章。兩位作者主張,民族志可以作為一種文學批評研究的對象,他們運用文學批評對故事的梗概、觀點、性格化、內容和風格的劃分和分析法,對民族志的寫作法進行全面研究。而王明珂博士則認為,在研究取向上,無論是文獻、口述資料或文化現象,在《羌在漢藏之間》一書中都被視為一種“文本”或“表征、再現”。“文本”之意義在于其與“情境”之互映,而“表征、再現”則是強調它們是在某種社會本相下產生的表象。文本存在于情境之中;情境也賴文本來顯現與活化。
文本分析在當前許多社會科學與人文研究領域中,都受到相當的重視。人類學與歷史學的文本分析方法較之于比較文學與語言學和民俗學等,又有較大的差異和寬泛的理解。文本分析不同于結合各種史料以歸納、發掘“事實”的“類比法”。不過把各種文獻史料、口述資料與文化展演都當作一種“文本”,面臨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那就是進行文本分析時如何處理田野工作與文本的關系。《羌在漢藏之間》為了反思傳統的“客觀文化特征論”在族群認同與民族識別中的做法,以及構建民族典范史以及解構與重構等問題時,收集羌族當地人中廣為流傳的“弟兄祖先故事”和“英雄祖先故事”的文本并進行分析、詮釋、演繹。然而,對田野作業與文本的關系,在一些現代學者看來,研究傳說、故事、神話者,就應該進行田野作業。從理論上,傳說的地方傳統在民間,民眾解釋在民間,社會功能在民間,所以必須通過田野作業獲得這些知識,任何現代文本研究都會希望獲得田野調查的支持,那樣的工作近乎完美。可惜好的理論只能接近事實,而不等于事實。事實之所以是事實,就在于它千樣百種,變化萬端,而不是理論。所以對古代傳說做現代田野調查,用以印證古代傳說,被限定在具體問題上。另外,王明珂博士在充分運用文本分析說明當代羌族的族群認同與區分時,盡可能收集多個流傳較廣的文本,如“弟兄祖先故事”在不同地區、不同人之間的意義歧變,因此才能加以比較,使文本透露出來的信息更具有可信度,
對于羌族的族群認同研究以及典范羌族史的構建,最早約在一九一○——一九二○年,傳教士陶倫士(Thomas Torrance)曾在岷江上游地區傳教,并研究當地羌民。除記錄描述羌民的文化特色之外,他也嘗試探索、重建羌民歷史——由夏代的大禹延續到清代。由于陶倫士將羌民的宗教視為一種“一神教”,他更進一步將這支民族的歷史追溯到東遷的古代以色列人。由一九二五年到一九四八年,另一位西方學者葛維漢(David Crookett Graham),也曾幾度進入岷江上游地區做過調查。陶倫士與葛維漢對于“羌民”的興趣,主要不是在其歷史,他們以及二十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國之羌民調查者的主要研究旨趣,都在于從文化、體質及語言來尋找、建立一個典范的當今“羌民”。在二十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著名學者如顧頡剛、馬長壽、任乃強等,都投入“羌族史”研究之中,他們的研究仍然繼承前一階段的歷史研究傳統,強調“歷史上”的羌族及其與中華民族中各民族之間的關系,而對當前的羌族則關注很少。與此同時,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岷江上游的本土歷史神話,羌戈大戰故事,引起學者的關注。這流行于理縣、汶川一帶的故事,述說一個族群如何自西北地區河湟流域逐漸向西向南遷居的過程。在青海省的河湟地區經考古學家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馬家窯、半山、馬廠、齊家文化等遺存表明就已有人在此活動生息。
“羌”這個字作為一種人群稱號,最早出現在商代甲骨文中(約公元前十三世紀),其地理位置在今河南西部、山西南部與陜西東部一帶。秦與漢帝國時期,政治統一帶來疆域與族群認同的擴張。氐與羌,被秦漢時人用來分稱隴西一帶西方非華夏人群。西漢昭帝與宣帝時,漢人的勢力進入河湟(黃河上游與其支流湟水流域),于是“羌”的地理人群概念波及河湟地區,今西寧(青海省府)當時稱為臨羌。上述“羌”或“氐羌”這些地理人群概念的變遷,表現華夏形成過程中華夏的西方族群地理邊緣變化。由“羌”這個族名所蘊含的歷史記憶,以及此記憶所蘊含的歷史過程,經由“羌人地帶”形成與變遷的歷史記憶,使人了解華夏與西方異族之間曾有一個漂移的、模糊的族群邊界。
同時,在羌族史研究中無法忽略的是,自唐代以來另一個核心——吐蕃與其佛教文化——曾將它的邊緣由西向東推移,在明、清時也將部分岷江上游人群變成其邊緣。再者,近代西方基督教文明國家在東方的擴張,又曾將這些羌民變成另一個邊緣——以色列人的后裔,基督教文明人群的邊緣。然而在構筑典范羌族史的過程中,卻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歷史上“羌人”的自我認同與本土歷史記憶。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冉光榮、李紹明、周錫銀等人所著的《羌族史》糅合本地傳說、考古資料與歷史文獻,此典范羌族史被認為是最具說服力、也最具權威性的典范之作,也是一個長期的華夏邊緣建構的歷史。
《羌在漢藏之間》一書的目的借李亦圓先生的評述:作者除努力為“羌族”的民族史或民族志做剖釋外,另一重要的目標則是借“羌族”的形成過程的分析進而為“中國民族”或“中華民族”等概念做“族群理論”的探討與解構。很明顯作者是一位較近于所謂“近代建構論”的學者,所以在他的觀念中“中華民族”實是西方“國族主義”影響下的自我想像建構的產物(3頁)。為許多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更加認同的族群定義:族群,是指在一個較大的文化和社會體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質的一種群體;其中最顯著的特質就是這一群體的宗教的、語言的特征,以及其成員或祖先所具有的體質的、民族的、地理的起源。而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在其主編的《族群與族界:文化和差別的社會組織》一書則認為,自我認定的歸屬和被別人的認定的歸屬,是族群的最重要的區分特征。他從族群的排他性和歸屬性來界定族群,認為“族群”是由其本身組成成員認定的范疇,造成族界最主要的是其“邊界”,而非語言、文化、血緣等“內涵”,一個族群的邊界,不一定是地理的邊界,而主要是“社會邊界”。在生態性的資源競爭中,一個群體通過強調特定的文化特征來限定我群的“邊界”以排斥他人。二十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關于族群認同的理論分為兩派。一為根基論(Primordialists)(又譯為原生論),一為情境論(Circumstantialists)或工具論(Instrumen-talists)。根基論認為族群認同主要來自于天賦或根基性的情感聯系。但是根基論者并不強調生物遺傳造成族群,也不是以客觀文化特征定義族群。相反,他們注重主觀的文化因素,認為造成族群的血統傳承,只是文化解釋的傳承。情境論者則強調族群認同的多重性,以及隨情境變化的特征。工具論的早期代表阿伯樂·庫恩(Abner Cohen)承認族籍具有象征或情感上的召喚力,因為它就人們的起源、命運以及生活和意義等生活中的永恒問題作出了回答。同時他認為族籍之所以具有象征召喚力是因為它具有實際的政治功能,只有關注于族籍的這些政治方面,我們才能解釋為什么在一些地方族群意識高漲的同時,另一些地方族群意識卻在消失,為什么并不是在任何社會中族籍認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社會意義。
在《羌在漢藏之間》一書中,作者不僅批判、解構歷史實體論,同時不為近代建構論所囿限,而實際上是超越了兩者的境界,進而從未來世界族群和諧平等共處的觀點來“籌謀改進或規劃更理想的人類資源共享環境”,這是何等開闊的胸懷!(李亦圓語)在王明珂一九七七年出版的著作《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一書中,作者指出,無論是客觀論與主觀論,或根基論與工具論,都不是完全對立而無法相容,而事實上各有其便利之處。客觀論指出族群可被觀察的內涵,主觀論描繪族群邊界;根基論說明族群內部分子間的聯系與傳承,工具論強調族群認同的維持與變遷。
由于羌或氐羌,與漢、藏及許多西北、西南非漢族群皆有關聯,因此,“羌族史”可以成為中華民族下許多民族間的黏合劑。王明珂博士用“華夏邊緣觀點”來說明“羌”的歷史也就有更為深刻、重大的意義。在“族群”(包含民族)的了解與界定上,強調由族群成員所相信或爭論的“我族邊緣”(哪些人是異族)來認識一族群的本質;在歷史文獻上強調其社會記憶本質,以探索留下此記憶的社會情境;在考古資料上,注重人類資源競爭、分配體系與其生態環境背景;在研究方法上,強調由異例分析了解一個社會的多元本質、模糊邊緣、權力關系與歷史變遷。
在近年來人類學、社會學界“歷史實體論”與“近代建構論”觀點相悖而爭論不休時,王明珂博士推出歷史人類學的典范工作《羌在漢藏之間》,一掃人類學著作傳統的形象,將思辨與邏輯說理巧妙結合,田野作業與文本分析相結合并與歷史古典文獻做精心的比較與闡釋,給讀者以遐思與啟迪,卻又不失橫生妙趣。正如李亦圓先生在序中所言,例如他的“毒藥貓理論”,“羊腦殼”與“牛腦殼”故事,“弟兄故事”與“祖先英雄”傳說,以至于所謂“一截罵一截”的現象等等,都能引起讀者會心一笑的體認。而作者將文本分析引入人類學田野作業,也有其特殊的目的,“事實上,在此歷史中有一個重要關鍵尚未被提及,這關鍵,就是歷史上‘羌人的本土歷史記憶”(209頁)。所以,作者將注意力放在田野作業中素材的收集和文本分析上,結合與《西羌傳》、《史記》等的比較研究,挖掘羌人的自我認同以及本土歷史記憶或作者所謂的歷史心性。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族群認同與區分成為熱點問題,尤其是多民族國家這一問題更是凸現出來。不過對于全球化這一非常復雜同時又有其魅力的歷史過程,尋找同一性的定義是不可能的。費孝通先生一九八八年提出了著名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這一格局“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的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修訂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李亦圓先生認為王明珂博士在其《羌在漢藏之間》一書指出歐亞大陸東西兩半的體制未必是西歐優于東亞,西方沿大西洋岸雖有講人權、自由的富國,但其內陸則常卷入宗教與資源競爭的迫害與爭斗之中;然而東亞卻能以“多元一體”的國族主義理想,以經濟支援及行政力量來減輕內陸的貧困與匱乏,并維持族群的秩序。假如以不具文化偏見的立場論,東亞的體制實有其長遠發展的意義。很顯然對謀求更公平境界的“全球化”人士而言,應該都是可以促進他們反思籌謀的典范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