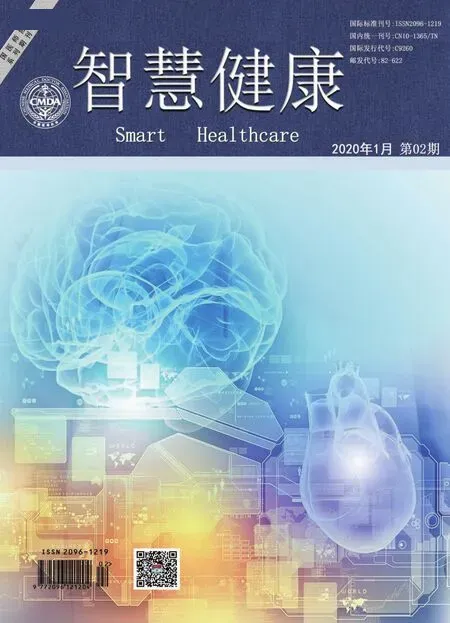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聯合保胎靈治療黃體功能不全習慣性流產的臨床療效分析
李福潔
(翁源縣中醫院,廣東 韶關 512600)
0 引言
習慣性流產通常是指女性在妊娠期持續自然流產三次或者三次以上的現象[1]。據相關研究醫學報道,近年來黃體功能不全習慣性流產已經高達全部習慣性流產的30%-60%,嚴重影響到了女性患者的生命健康[2]。黃體功能不全習慣性流產疾病目前的一部分致病原因為,患者存在染色體異常、生殖系統感染、以及內分泌紊亂和免疫性疾病等,在臨床治療黃體功能不全習慣性流產患者的用藥時,目前還沒有統一的治療方案,但是相關醫學專家提出,中醫臨床治療具有豐富的經驗[3]。本文將通過針對黃體功能不全習慣性流產患者分別使用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保胎靈和孕前黃體酮+維生素E治療的臨床效果進行深刻的研究分析,現將主要內容報告如下。
1 資料和方法
1.1 資料
根據治療方法的不同,將本院2015年10月-2018年12月收治的187例黃體功能不全習慣性流產患者,隨機分成兩組患者,其中常規組共有患者93例,年齡(24-38)歲,平均(26.5±1.3)歲;流產次數(3-5)次,平均(3.8±0.5)次;治療組共有患者94例,年齡(23-38)歲,平均(27.2±1.8)歲;流產次數(3-5)次,平均(3.6±0.8)次;納入指標:(1)連續發生3次或者3次以上流產的女性患者;(2)無內科合并以及精神類疾病的患者;(3)對本次研究分析藥物(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保胎靈;孕前黃體酮;維生素E)不過敏的患者;(4)病史資料齊全且治療依從性良好的患者;(5)對于此次研究分析已經進行同意并簽字確認的患者;兩組黃體功能不全習慣性流產患者的年齡和流產次數等一般組成資料比較,組間差異無顯著性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針對常規組93例患者實施孕前黃體酮[4](生產企業:浙江仙居制藥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33 020829;規格:1 mL:10 mg)聯合維生素E[5](生產企業:浙江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藥廠;國藥準字:H20 003539;規格:100 mg)藥物治療。通常在患者的月經前的15天左右排卵之日起給予患者進行20 mg的黃體酮肌肉注射,1次/日,當患者順利妊娠后繼續給予原劑量用藥至超過以往流產最長周數時間,并囑咐患者進行臥床休息和適當的維生素E治療,針對患者的消極情緒進行治療,嚴禁進行性生活。
針對治療組94例患者實施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生產廠家:萬華普曼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國藥準字:S10 950049;規格:10支裝)聯合保胎靈(生產廠家:黑龍江福和華星制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Z23 020357;規格:48片)藥物治療。在患者的月經前的15天左右排卵之日起隔日實施500 U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肌肉注射,連續5次,之后可根據患者的臨床癥狀進行適當調整。當其順利妊娠后可維持原劑量給藥至體內胎盤完全形成。在患者妊娠期12周左右,加服藥物保胎靈,并囑咐患者進行臥床休息,嚴禁進行性生活。
1.3 療效評價標準
療效判定:分別對兩組黃體功能不全習慣性流產患者實施流產率和足月妊娠率的計算,其中流產率=流產例數/總例數×100%;足月妊娠率=足月妊娠例數/總例數×100%。
1.4 統計學分析
應用SPSS 21.0統計學軟件對患者的相關數據進行處理分析和計算。計數資料用百分比(%)和例數(n)表示,組間值進行檢驗,如果P<0.05,表示組間差異有顯著性意義,具有可比性。
2 結果
2.1 兩組黃體功能不全習慣性流產患者的流產率比較
常規組患者的流產率為13.98%,治療組患者的流產率為4.26%,治療組顯著低于常規組,組間差異明顯,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的流產率比較(n,%)
2.2 兩組黃體功能不全習慣性流產患者的足月妊娠率比較
常規組患者的足月妊娠率為82.80%,治療組患者的足月妊娠率為93.62%,常規組顯著低于治療組,組間差異明顯,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的足月妊娠率比較[]

表2 兩組患者的足月妊娠率比較[]
3 討論
目前,針對兩組黃體功能不全習慣性流產患者的醫學研究發現,黃體功能不全是導致患者發生習慣性流產的主要原因[6]。當患者通過多次流產進行清宮手術后,都會或多或少的使子宮內膜受到損傷,從而當患者再次妊娠時,便會直接影響到胚胎和胎盤的植入和形成,甚至還會影響到胚胎的成長發育[7]。所以相關專家表示,想要改善黃體功能不全習慣性流產患者的流產率以及租約妊娠率,需要從其子宮內膜和滋養細胞及胎盤內分泌功能入手[8]。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主要是由孕婦尿液中提取的絨毛膜促性腺激素組成,其作用與垂體分泌的促黃體素相似,均可以促進妊娠患者的黃體功能,不僅可以針對妊娠其患者的黃體分泌雌激素以及孕激素進行刺激,改善患者子宮內膜的著床條件[9];同時還有利于患者子宮局部內分泌免疫細胞-細胞因子網絡功能的穩定性,保證體內胎盤以及胚胎的血管形成和生長發育。另外孫普英[10]等人研究發現,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對患者的胚胎發育以及早孕維持均具有重要作用,并且患者實施該藥物治療后,不會出現影響體內胎兒的性器官健康發育的現象。保胎靈藥物主要是由多位中藥合成的一種膠囊藥物,其主要成分包括其組成成分為熟地黃、桑寄生、五味子、杜仲、白術、龍骨、山藥、牡蜘、阿膠、枸杞、續繼、菟絲子以及白芍等,孕婦在懷孕前以及中期進行服用,均不會傷害體內胎兒以及孕婦的身體健康,且本藥具有安胎補腎的作用。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保胎靈藥物聯合治療黃體功能不全習慣性流產患者可以明顯改善患者的臨床癥狀,具有促進的作用。
本次研究分析將針對兩組黃體功能不全習慣性流產患者分別實施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保胎靈和孕前黃體酮+維生素E藥物治療,對所有患者共同治療后,根據詳細的觀察記錄分析得出:常規組患者的流產率為13.98%,治療組患者的流產率為4.26%,治療組顯著低于常規組,組間差異明顯,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常規組患者的足月妊娠率為82.80%,治療組患者的足月妊娠率為93.62%,常規組顯著低于治療組,組間差異明顯,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
綜上所述,相較于孕前黃體酮+維生素E藥物,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保胎靈更加能夠減少黃體功能不全習慣性流產患者的習慣性流產率以及復發率,同時也可以取得較好的妊娠結局,證明中成藥聯合西藥治療更具有臨床推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