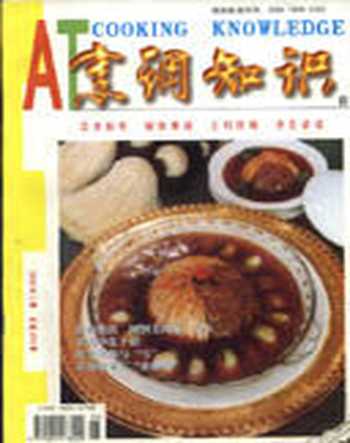食林偶拾
白忠懋
藤蘿餅
從前,北京中山公園有個長美軒,飯館在室內,茶座在露天。茶座有一樣小吃令老北京至今仍在贊頌與懷念:上世紀50年代以來,做藤蘿餅是該軒的傳統。藤蘿花取自茶座中間的幾架很茂盛的藤蘿花架。花采下后用糖腌制為餡,皮則如同玫瑰餅一樣的做法。當時一些餑餑鋪也做藤蘿餅,但與長美軒相比總要遜色不少。主要是花系現摘現做,十分新鮮,保持了花的色澤和清香,餡大皮薄,工藝講究。此外,由于現做現賣,出爐是熱的,既酥且香,所以從未出現剩下賣不出去的。
藤蘿餅也有方形的,叫藤蘿方脯——花餡像包子一樣包好,在木制印模(上有各式花紋圖案)中壓成方的餅式。餡料多用甜的,很少用菜肉的。其味甜軟清香,極為適口。如不用印模,花樣隨意;或用千層餅形式,內加松子、桃仁亦是一法。這種餅家庭可以自制。花應選開到八分和未開的,去蕊后置于碗內,用去筋豬油切成細丁,拌上白糖攪勻,約腌半日即可作餡。
梁實秋先生在北京時很喜歡這種餅,他雅興不淺——把藤蘿餅花交給餑餑鋪,讓他們代為制作。有時則把玫瑰花送去,做成玫瑰餅。
藤蘿即紫藤,也叫朱藤,豆科,莖長,能攀緣,葉為奇數羽狀復葉,春間開花,向下垂,總狀花序,蝶形花冠,紫色(變種呈白色),花后結莢長大而硬,密生絨毛。紫藤跟紫荊不同。紫荊雖也屬豆科,但它不會攀緣,葉圓心形,早春先花后葉,花紫色,孩童在它開花時摘來吃,有淡淡清香和淡淡甜味。
查清代《調鼎集》,有藤花,很可能指紫藤的花:“藤花,采花洗凈,鹽湯灑拌,入甑蒸熟,曬干,作餡食,美甚。”
其實都是“面疙瘩”
有的小吃名稱十分古怪有趣,如云南的一種粽子叫“捆綁”;無錫惠山有一種小而圓的餅叫“金剛肚臍”;浙江新昌的一種春卷叫“鑊拉頭”……清代袁枚在《隨園食單》中的“面老鼠”也屬這一類。它的制法為:“以熱水和面,俟雞汁滾時,以箸夾入,不分大小,加油菜心,別有風味。”陜西人讀了會發出會心的微笑:什么面老鼠?這不就是老鴉頭嗎?漢中人稱之為“雞腦殼”,四川話“腦殼”就是頭之意。老鴉頭也好,雞頭也好,都是象形,有形狀不規則之意。
面老鼠的湯用的是雞汁,這就使這一面食提高了檔次,如果所加的菜用上海鮮或雞鴨,那就更精彩了——上得了筵席。
在陜西,它的吃法多樣:可做成羹;也可以不用湯,拌上菜蔬調料,像北京的炸醬面;更可以炒著吃,按不同口味,拌上不同菜蔬與調料。
這種面食到了山西,名稱便改了——它叫“撥魚兒”,形如魚兒。我的文友、上海“筷子大王”藍翔曾去五臺山旅游,看師傅操作:面粉中加少許豆面,加水攪拌成稠漿狀,放半小時,使水和面滲透均勻,變成柔軟光滑的面漿。將它放入碗中,左手持碗,稍傾斜,右手拿一竹筷順碗邊將面漿撥入沸水鍋中——利用筷的彈性,快如流星地撥出兩頭尖,長約10 cm的面條入鍋。撥魚兒出鍋后澆上鹵汁、炸醬、西紅柿醬或過油肉、炒肉片等,吃來別有風味。老舍先生生前吃過山西的撥魚及貓耳朵,曾有贊美的詩句:“駝峰熊掌豈敢夸,貓耳撥魚實且華”。
撥魚在明代已有,而且是面粉與山藥攪拌在一起的:白面一斤,好豆粉四兩,水攪和調糊,將煮熟山藥研爛,同面一并調稠。用匙逐條撥入滾湯鍋內,如魚片。俟熟以肉汁食之。無汁,面內加白糖可食。(《飲饌服食箋》)
在浙江肖山,面疙瘩被稱為“田雞塊頭”,他們所以這么叫,因為一小塊落鍋的面疙瘩很像剝了皮的蛙腿。
在上海,以往主婦為圖方便,有時做面疙瘩,與之搭配的較理想的蔬菜是南瓜,偶而吃一回這種色澤橙黃面食,倒也別有風味。
“魚蛋粉”
廣州有早點鋪,供應稀粥、云吞、面條等等,有一樣很大眾化的早點,就是“潮州魚蛋粉”。
魚蛋粉不冠以“廣州”而寇以“潮州”,說明它是潮州的一種著名小吃。對北方人來說,“潮州”是知道的,“魚蛋粉”便費思量了;魚不下蛋,龜蛇才下蛋,魚的“蛋”名“卵”。其實,“蛋”在這兒是一種形狀,圓形,不是蛋的橢圓形,是彈子般,所以寫成“魚彈”更妥貼些。由北方人來叫它,就是魚丸。
最早見到“魚蛋”這一名稱我也不理解,后來,讀香港美食家蔡瀾的散文集《忙里偷閑》,有一篇《魚蛋檔》,這才得知它就是魚丸:香港學生最喜愛的食品是街邊的墨斗的須(即墨魚須)和魚蛋。它們裝在車內的鐵格中,墨斗須被染得紅紅的,魚蛋則浸在黃的咖喱汁中。好的魚蛋脆、爽,有彈性,但那種魚蛋魚肉少,粉多,入口黏軟,賣時串成串。
看來,潮州魚蛋比蔡先生所說的那種低檔次的魚蛋要好吃得多——它個兒很小,但很鮮嫩。
至于“魚蛋粉”的“粉”,對北方人來說,“粉”是什么還很陌生。在廣西、貴州,有“粉館”,即供應米粉的小吃店。北方主食不是大米,而是面粉,他們一見“粉”字,以為是面粉。上海在南方,雖吃大米,但對用大米制成米粉也十分陌生,也不知“粉館”為何物。米粉有粗細之分,“潮州魚蛋粉”中的“粉”是細的那種。這種米粉的配料主要是魚蛋,此外,尚有牛肉丸、海參片與蝦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