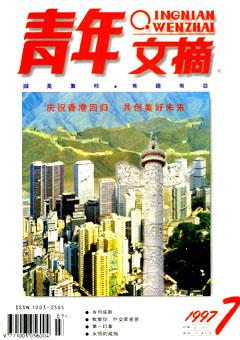初戀的記憶
〔美〕蒂姆·麥迪甘
我的家鄉(xiāng)克魯克斯頓位于美國明尼蘇達州西北角,是個有8000人的農(nóng)村。沒有什么特別,不過戈蕾琴例外。
原因之一是她姓艾克賀夫。她的家族是克魯克斯頓的豪門,住在紅湖河邊一幢磚建房子里,每年夏天到50公里外聯(lián)合湖的別墅去避暑。
戈蕾琴家境優(yōu)厚,貌美如花,卻全無架子。她在學校里總是很快就和新同學熟悉,又樂意為成績不好的同學補習。念高中時她參加許多不同的會社,和不同背景的人交朋友,包括農(nóng)家子弟、運動員、脾氣古怪的人,對所有人都和藹可親。1975年她當選中央高中“全壘打皇后”。戈蕾琴顯然是人中龍鳳。
我和戈蕾琴只是點頭之交。我是運動健將,樣子也算端正,不過自信心不足,在女孩面前更是如此。我覺得她們神秘莫測,比曲棍球比賽中迎面而來的疾飛球還要嚇人。
正因如此,1977年夏天我和她在村里一個年輕人天地重逢那夜所發(fā)生的事,教我到現(xiàn)在還迷惑不解。當時我剛在附近大福克斯市的北達科他大學念完一年級,見聞遠比我廣博的戈蕾琴則在加州斯坦福大學讀完大一,回家過暑假。
她高興地和我打招呼。我記得她拉著我下舞池時,感覺到她的手像皮革般粗糙,那是因為她常在聯(lián)合湖上劃艇的緣故。她和我差不多高,杏仁色的皮膚潤澤無瑕,眉清目秀,牙齒皓白,淺褐色的秀發(fā)垂下來披在肩上,無袖的白襯衫在舞池的閃燈下發(fā)光,襯托著一雙因為常常游泳、騎馬和劃艇而顯得很強壯的古銅色手臂。
我發(fā)現(xiàn)戈蕾琴舞跳得不好,但是跟著音樂跳得很起勁,一直輕柔地笑著。幾首音樂后,我們站住聊天,由于音樂聲很大,我們必須扯大嗓子。我送她回她的車子去時,大街上冷冷清清,交通燈只閃著黃燈。我們手牽著手走,來到她車子的旁邊,她示意我吻她,我欣然從命。
那個夏天很愉快,但我始終無法獨占戈蕾琴的芳心。她喜歡我,這是毫無疑問的。后來她終于透露,兩年前她曾是我的“守護天使”——在曲棍球比賽前把餅干和鼓勵字條放在我的儲物柜內(nèi)的那個神秘人。
可是克魯克斯頓的男孩都知道沒有人能抓得住戈蕾琴的心。那個暑假她熱情地回吻我。下一個暑假也如此,但對她來說,我只是她從童年邁向成年過程中一個插曲,還有許多更重要的事在前面等著她。
因此戈蕾琴和我很少談到一般生活以外的事。她從不談未來,也從未提過有什么憂慮或傷心事。她一直沒告訴我她讀小學六年級那年曾滑雪出事,摔斷了雙腿,之后好幾個月去哪里都要父親抱著去。后來戈蕾琴重學走路。多年后,她的家人認為,她待人熱情而性格獨立,都源自那一次意外。
我對她非常著迷,而且勇于向她坦露心跡。這顯然不怎么好,因為每次我示愛之后,她總是會暫時疏遠我。我們都還在念大學,還不宜瘋狂相愛、山盟海誓。
1978年一天晚上,戈蕾琴和我在一起,突然說出了一句在我這種處境中的男孩最怕聽到的話。
“蒂姆,”她說,“我想我們只做朋友算了。”
我告訴她,我已厭倦她玩的把戲,而且我不是她想象中那么傻。說完我就怒氣沖沖地跑掉。第二天早上我氣消了,于是給她送了些玫瑰并附了張便條向她道歉,表示希望繼續(xù)和她做朋友。
大約一個月后,我和戈蕾琴再開始約會。我學乖了,不再癡情迷戀,并且裝作矜持冷淡。
這種策略我巧妙地用了幾個星期,戈蕾琴終于忍不住,問道:“你出了什么毛病?”
“你說什么,我有毛病?”
“你在演戲,”她說,“你最近一直在演戲。”
“你說得對,”我說,然后告訴她我的用意,說我裝作冷冷淡淡是為了不想失去她。她生氣了;在我記憶中她就只發(fā)過這次脾氣。然后她建議跟我來個君子協(xié)定。
她說:“你不演戲,我就不離開你,至少這個暑假結(jié)束前不會。”
我立刻接受建議,而她也遵守了諾言。
戈蕾琴回斯坦福大學前,和妹妹在湖邊舉行大型舞會。我心想,戈蕾琴身為主人,要忙于招待貴客,大概沒有時間陪我了。
熱鬧的舞會過了一半,她示意要我跟著她走。她跑到碼頭盡頭撲通一聲跳到清涼的水中,游向遠處的浮臺,古銅色的雙臂劃水強而有力,姿勢優(yōu)美。我游到浮臺時已經(jīng)筋疲力盡,她伸手把我拉了上去。
我們在浮臺上逗留了很久,兩人用腳尖踢水,看岸上的人群。我心想,這真是向眾人表明我們友情深厚的好辦法。
那幾個星期太美妙了。簡直像生活在夢中。有天晚上我們道別時,我終于撤除最后一點偽裝,告訴她說我愛她;她只是露出笑容。
9月初我回到大福克斯上學。戈蕾琴和朋友茱莉·珍納琪從克魯克斯頓開車來看我,二人在我的宿舍房間出現(xiàn)時,我驚喜不已。她們拉我出去跳舞。
9月中旬戈蕾琴要回斯坦福大學了,我返克魯克斯頓為她送行。她收拾行李的時候,我心神恍惚地在她家的撞球桌上打球。她收拾完畢,我們到她家牧馬的草地最后一次散步。天氣已經(jīng)轉(zhuǎn)涼,我想到人生如戲,我們倆即將分道揚鑣各奔前程,不禁有些傷感。不過一想到過去兩個暑假共度的美好歡樂時光,我很感激上天對我眷顧。
戈蕾琴計劃明年暑假留在加州找工作。在她看來,生命中嚴肅的階段即將來臨;我也明白什么事將要發(fā)生。
回到她家門口,我向她道別:“珍重。”
“不要說珍重,說再見,”她說。
我回到學校,由于有了和戈蕾琴來往的經(jīng)驗,我膽子大了,不久便開始和新聞系一個同學約會。戈蕾琴則愛上了斯坦福大學足球隊一名健碩英俊的中鋒。
1978年10月9日晚上,我打電話到加州祝她21歲生日快樂。她謝謝我打電話給她,但似乎有點心不在焉。我聽得出她那里正在舉行舞會,人聲嘈雜,于是匆匆掛斷電話。
10月13日,黃葉即將落盡,藍天上萬里無云,空氣清爽涼快。我那一天的課已經(jīng)上完。人難得同時既感快樂又感滿足,但是那天早上我的確同時有那兩種感受。
我剛回到宿舍房間,電話鈴就響了。我聽出是茱莉的聲音,心里很高興。她下個月就要結(jié)婚,現(xiàn)在大概是要告訴我戈蕾琴已決定回克魯克斯頓參加婚禮。
茱莉哽咽著告訴我,戈蕾琴去世了。
茱莉說,戈蕾琴在前一天上午接受了一個同學送的生日禮物:乘坐小型飛機。飛機升空不久就失去控制,墜進沼澤,戈蕾琴和她的同學都當場喪生。
“戈蕾琴的父母問你是否愿意幫忙扶柩?”茱莉問。
“我很樂意,”我回答。
這句話一出口我就覺得很別扭。“樂意?”你真的樂意去幫忙埋葬一位朋友,一位聰慧開朗、前途一片光明的美女嗎?我離開宿舍,漫無目的地到處亂走。后來有人告訴我,我當時去找了學校的神父,但是18年后我完全記不起曾有那么回事。
那天下午我回到克魯克斯頓去,找我中學母校的曲棍球教練。他開車帶我去兜風。我對他說,戈蕾琴去世了,我不明白為什么大家還有心情去買菜、去加油站,做諸如此類的瑣碎事情。
“人傷心是怎樣的呢?”我心想,奇怪自己怎么沒有眼淚。
星期六晚上,我開車去艾克賀夫家,路上經(jīng)過戈蕾琴和我曾經(jīng)散步過的那片牧馬草地。那家人悲痛之余,把我看作他們家的一分子。戈蕾琴的母親特地去找來她女兒和我?guī)仔瞧谇昂吓牡囊粡堈掌U掌形也[著眼,手臂輕輕摟著戈蕾琴的肩膀;戈蕾琴則笑容燦爛,皓齒在杏仁色皮膚襯托下顯得格外潔白。
“蒂姆,戈蕾琴非常喜歡你,”她母親說。
喪禮后那個晚上,來追悼的親友約好在一家餐廳聚會,我在餐廳外和喬爾·魯?shù)伦谒能囎永铩N覀兡钪袑W時是校隊隊友,也是要好的朋友,經(jīng)常在星期六晚上一起開車到郊外去兜風,大談體育、學校、愛情和未來的抱負。這時和他重聚,我的悲痛終于爆發(fā),但是也感到安慰。
喬爾談到戈蕾琴時,有一陣子突然喉嚨梗塞,說不出話來。我看見老朋友哽咽,理智與哀傷之間的障礙立刻粉碎,淚如泉涌。
第二天早上,喬爾和我參加出殯行列,從湖邊艾克賀夫家的避暑別墅前往附近的樹林。戈蕾琴的姊妹輪流捧著骨灰罐。天氣清涼,陽光照耀,落葉在腳下噼啪作響。
我們來到一棵孤單的白樺前;四周全是棕色的楓樹,這白樺的白色樹皮特別顯得突出。戈蕾琴和父親、妹妹多年前發(fā)現(xiàn)這棵樹時,曾把名字和日期刻在樹身上。
有個人讀了禱詞,戈蕾琴的父親把骨灰罐放在白樺下的穴中。在我們上方,清風掠過剛掉光葉子的禿枝,發(fā)出沙沙聲響。
我?guī)缀跏亲詈箅x開的。那天我從樹林里出來,就邁進了另一個世界——成年人的世界。在這新世界里,初戀的記憶永不磨滅,夏日卻總會結(jié)束。
(摘自《讀者文摘》中文版1997年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