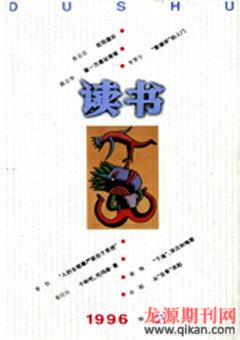也該同情日丹諾夫
張介明
日丹諾夫作為主管文藝的蘇共中央書記,在蘇聯當時的一系列文藝整肅中扮演了一個不光彩的角色,但作為那個極端嚴峻的歷史時期的產物,他也是一個可悲、可憐和可嘆的角色。盡管他的批判左琴科、穆拉杰里的文章顯得如此頤指氣使,專橫粗野,不可一世,就象王蒙寫到的那樣,但用西蒙諾夫的話來說,他只是一架“電話機”,一架“損壞了的電話機”。從西蒙諾夫的回憶錄中我們可以看到蘇聯當時的最高方面對蘇聯文藝的“指導”是多么地洞幽察微,大至文藝的大政方針、宣傳口徑、政治導向、主旋律(即最高方面所謂的“現在我們是否需要這本書?”);小及每次斯大林文學獎的人選和等次、稿酬標準、《文學報》編輯部的人員編制……在這種情況下,日丹諾夫即便主觀上不想做小人、奴才、鷹犬,還可能有所作為嗎?事實上,即使忠心耿耿如日丹諾夫、西蒙諾夫者,在當時何嘗不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西蒙諾夫寫到當他的中篇小說《祖國的青煙》發表后,一開始日丹諾夫也表贊賞,并安排了肯定該小說的評論文章,但“突然一切都翻了個過兒?”“日丹諾夫從斯大林那里回來以后,評論文章被從版面上取了下來”,西蒙諾夫被當頭一棒,“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日丹諾夫就此事對西蒙諾夫的解釋。西蒙諾夫寫道:“日丹諾夫試圖耐心地給我解釋了大約一個小時……但是他越給我解釋,我越明顯地感到:他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向我解釋文章中所寫的那些話(即評論文章);他同我一樣,既不明白為什么我的小說會如文章中所說的那樣壞,也不知道今后該如何修改。在這之前我曾看到過日丹諾夫聲色俱厲、盛氣凌人的樣子……我到他那里去的時候,曾充分做好準備,聽他一番聲色俱厲的談話。但是他卻相反,很有耐心,與人為善,我覺得,他內心里并不相信他對我說的話,所以顯得有點心虛”——讀到這些,我從心底不由得升起了一股憐憫的感受,日丹諾夫是不是也值得同情?因為作為一個黨員,怎能抗拒往往以“中央委員會”和“人民”的名義表達的最高方面的個人喜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