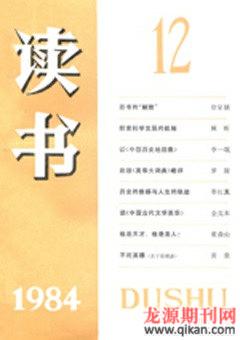關(guān)于黃遵憲的《新嫁娘詩》
浩 成
我在不久前寫的《“放鄭聲”與“遠(yuǎn)佞人”》一文(見《隨筆》一九八四年第四期)中曾談到北宋初期的文風(fēng)還承襲晚唐、五代的習(xí)尚,不少文學(xué)家喜歡在詩文中,特別在詞中說些淫詞艷語。明顯的例子是大詩人黃庭堅(jiān),他做的許多詞,在今天一些新道學(xué)家的眼中也還是很難通過的。在北宋封建王朝,這些作品的創(chuàng)作和流布,可以說是相當(dāng)大膽的了。雖然這些作品往往在他和后人正式編印的詩文集中找不到,人們處理這些作品的辦法或者是把它們“打入另冊”,例如黃庭堅(jiān)的詞除收入《山谷詞》之外,另有一本《山谷琴趣外篇》,或者就干脆把它們從詩文集中刪去,聽任其湮滅掉。后世也大抵一直采取這樣的辦法。因此,在封建主義的高壓和禁錮下,天壤間有多少真實(shí)、動(dòng)人的好作品就這樣被摧殘、扼殺了。
最近讀到文化學(xué)社一九三○年出版的《人境廬詩草》,才發(fā)現(xiàn)原來黃遵憲這位以從事“詩界革命”著稱的晚清詩人,也做過一些艷詩。這就是做為這本《人境廬詩草》附錄之二的《新嫁娘詩》四十八首。就我個(gè)人來說,更驚人的發(fā)現(xiàn)是,這些被稱為“黃公度集外詩”的,原來竟是先父董魯安發(fā)現(xiàn)并發(fā)表在《京報(bào)·文學(xué)周刊》的《中國文學(xué)研究號》(一九二五年)上面的。他在發(fā)表這些詩當(dāng)時(shí)所寫的說明中說,這些詩“是從黃公度先生的鄉(xiāng)人劉秀生君齋頭借鈔來的……此詩原題新嫁娘詩五十首(實(shí)止四十八首)和集中‘山歌詞意相近。考《人境廬詩草》卷一《山歌》題下自序云:‘土俗好為歌,男女贈(zèng)答,頗為子夜讀曲遺意。采其能筆于書者,得數(shù)首。疑這里的四十八首,便是和《山歌》同時(shí)作的(或在其前)。必是覺得詞太艷冶,認(rèn)為不能筆于書,所以刪去了。作《山歌》時(shí)的年代,大約在先生十六、七歲的時(shí)候(同治三、四年,公元一八六四至一八六五)正是新婚的前后,詩中情意的旖旎,風(fēng)格的雋永,處處流露著少年的氣分。確是未婚的少年寫不出來的。”
讀過這四十八首詩,覺得對于研究黃遵憲的思想和作品來說,是一個(gè)重要資料。如果說黃遵憲在晚清認(rèn)為詞太艷冶,不能筆之于書,那么,在偉大的五四運(yùn)動(dòng)以后,新文學(xué)經(jīng)過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洗禮,完全應(yīng)該沖破封建主義長期設(shè)置的禁區(qū)了。令人遺憾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收入《古典文學(xué)叢書》的《人境廬詩草箋注》這種供專業(yè)研究者用的本子,竟然也沒有將這《新嫁娘詩》四十八首收進(jìn)去,而且在序跋多篇中竟無一語提及這些詩。這大概也還是“為尊者諱”的正統(tǒng)思想在作怪吧!
先父在這組詩的說明中還有這樣的話:“人境廬在近代文學(xué)史上的地位,世有定論,不必多說。至于先生的人格、思想、學(xué)問、政績,談近世外交人材和戊戌政變史的,總要想到先生的吧。先生‘余事作詩人本不可以文掩行的,但如果以為先生不會(huì)有這類側(cè)艷文章,甚至以為是盛德之累,便是狗屁不通的話了。我們對于文藝的看法,若照弗羅依德一派的解釋,那便即使是晚唐的冬郎(按:這是《香奩集》作者韓
值得注意的是先父這個(gè)說明寫在一九二五年九月,也就是說,距離今天已有五十九年。然而,即使今天讀起來,不是仍然很有現(xiàn)實(shí)意義的嘛?有一同志同我開玩笑說:“如果不看令尊大人的署名和寫作的年月,我簡直會(huì)誤認(rèn)為出自閣下的手筆呢!”這真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足以證明封建主義在我們這個(gè)古老的國家里是多么根深蒂固,在思想文化領(lǐng)域里舊的傳統(tǒng)勢力是多么頑強(qiáng)!幾十年過去了,我們還不得不在原地踏步,還不得不被迫討論早已解決了的問題,還不得不做些啟蒙的工作。十年浩劫中封建主義肆虐、荼毒人民的慘痛教訓(xùn)似乎并沒有使一些同志變得更聰明些。幾年前不是還曾辯論機(jī)場上某一幅裝飾壁畫是否宜于張掛的嗎?今年初不是有人一看到《新婚第一夜》的標(biāo)題,就斷定這是一篇黃色的作品,致使秦牧同志奮筆寫出《新道學(xué)先生的笑劇》這篇極有見地的好文章來的嗎?還有,最近聽到一個(gè)例子,有人一聽到《東洋魔女》這個(gè)電視劇的標(biāo)題就嚇得要命,當(dāng)即決定禁演,后來才弄清楚,這就是目前正在放映的《排球女將》,綽號“魔女”的小鹿純子,只不過球藝高強(qiáng),可以說是日本的郎平,片中找不出任何誘人犯罪的情節(jié)。事情正象秦牧文章中所說的那樣:“我們現(xiàn)在有些人對于某些男女社交關(guān)系、某些繪畫雕塑、某些文字采取過度敏感的態(tài)度,是不是也有‘民國時(shí)期某些衛(wèi)道之士的流風(fēng)余韻呢”?如果這些人仍然總是用這樣的老眼光看問題,他們當(dāng)然就會(huì)把黃遵憲的《新嫁娘詩》也看成“黃色作品”。如果當(dāng)真如此的話,我認(rèn)為,這除了證明他們自己的不長進(jìn)以外,還啟示我們肩上肅清封建遺毒的任務(wù)是多么沉重,真可以說是“任重而道遠(yuǎn)”。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