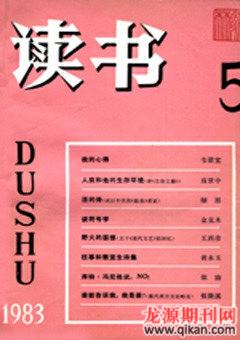從“無地起樓臺”說起
于其化
我愛讀那種古為今用的文章。但報刊上時有一些文章,從古籍中信手拈來一點材料,不辨其可靠性何如,便加引申,附會成文,讀后卻不是滋味。最近看到一篇《無地起樓臺》的雜文,即是如此。該文從引《國老談苑》發(fā)端,稱宋朝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當時有個隱居詩人魏野寫詩贊頌他:“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真宗末年遼國的使者來到宋朝也提及這位“無地起樓臺相公”。雜文作者以此斷言寇準“廉潔儉樸”,并進而發(fā)了一通“在今天看來仍然十分難能可貴”之類的議論。文章的用意是好的,但對寇準的稱譽卻未必恰當,至少不能做到“無懈可擊”吧!
宋人筆記和其他史料中,對寇準生活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說他儉樸者有之,說他豪侈者更不少。我們不妨都擺一下。
王君玉《國老談苑》這條材料,吳處厚《青箱雜記》及江少虞《事實類苑》亦有類似記載。但《事實類苑》將“真宗末年”記成“仁宗初年”。這便算得一個小小的疑點。魏野與寇準交往甚密,這在《詩話總龜》、《夢溪筆談》、《青箱雜記》中均有記載。既然兩人情誼甚深,那么魏野寫幾句頌揚寇準的詩便在情理之中;況且,他寫的是詩而不是事跡實錄,《國老談苑》以那兩句詩為佐證,我們今天又轉(zhuǎn)手用它來概述寇準的生活作風,都顯得無力。
《邵氏聞見錄》也稱寇準“居家儉素,所臥青帷,二十年不易”。邵伯溫自稱這項“遺事”得之于寇準的外甥所作的墓志。人們不難推想,作者是外甥,文體是墓志,雙重原因,當然會盡說好話了。說寇準儉樸的還有釋文瑩《湘山野錄》:“公歷富貴四十年,無田園邸第,入覲則寄僧舍。”在此一并錄上。
再看第二類材料。先舉正史。宋史·寇準傳》寫道:“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家未嘗
野史還有一些記載,高晦奧《珍席放談》說“寇公尚華侈”。還有《翰府名談》(撰人不詳)所敘更有意味。寇準在宴會上把一束束的綾賞賜給歌姬,每唱一支歌就賜一匹綾。寇準有個侍妾叫
其一: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螢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
其二: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窗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
寇準和詩道: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樽前聽艷歌。
還有一條好材料,是司馬光的《訓儉示康》。文中說:“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yè)大,人莫之非。”司馬光是歷史學家,對寇準又無政治上的偏見,加之文章又是寫給兒子看的,寓品德教育于歷史事實之中,真實性就很大了。
綜合分析兩類材料,判定寇準生活豪侈,應該說較為接近歷史的真實,較為穩(wěn)妥一些;退一步講,也不至得出“廉潔儉樸”的結論吧!我們作借古諷今之文,跟寫學術論文一樣,也要有科學性,對于古人事跡必須深思慎取,而不能想當然。如果抓到一點材料就如獲至寶,敷衍成文,那東西不過是毫無戰(zhàn)斗力的“銀樣蠟槍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