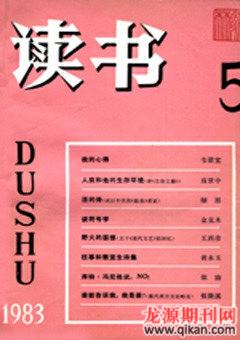現代主義和現實主義構不成一對矛盾
卞之琳
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的小說《紫羅蘭姑娘》英文原本初版在一九四五年十月,我的中譯本一九四七年二月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稍有節略的譯文一九四六年先在上海《文藝復興》雜志上發表過)距今已經三十五、六年了。從前讀過這個譯本的朋友們愿意重見到它,出版社借到一本讀了,也愿意重印它。現在就據原文校對修訂了一遍,交出付排。
譯本原有我寫的序文。作者對它還滿意(他接到我寄給他看的序文英文稿后,回信說,“如果譯文跟你的序文一樣好,那么我不能再求更好了”)。但是三十多年過去了,譯本新版問世,我自然有責任再另外說幾句話。
世界上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變化很大,五十年代以來又有了新的變化。就衣修午德說,也是如此。《紫羅蘭姑娘》出版將近十年后,他才又陸續出版了小說《黃昏的世界》(一九五四)、《單人》(一九六四)、《河畔的相會》(一九六七)等和三本自傳性著作。小說內容多寫同性愛和印度吠檀宗教哲學。他自己在回憶錄式的著作里把三十年代反法西斯的進步政治動機都加以否定。但是衣修午德,在三十年代和奧頓以及另外一批左傾過的同代作家一樣,因為客觀事實、歷史事實在那里,要否定自己過去作品的意義和作用,還是不能由自己后來的主觀愿望否定得了。就以《紫羅蘭姑娘》而論,盡管經過了作者多少年沉默,經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它的基本精神還是和他在三十年代的一致。
《紫羅蘭姑娘》基本上還是象三十年代的衣修午德小說。當然,其中就有些三十年代中期以前西方知識分子還少有的幻滅感與憂郁感、他們還沒有清醒感受到的兩難處境。尤其是其中染上了一層三十年代結束以前西方很少流行的印度哲學的色彩。而這點所引起的我寫原序當時的一些反應,也就使我在序文里寫了一些“玄”話或者廢話。但是序文的主要內容似乎還沒有什么大錯,雖然我自己也早已不同于三十多年前的自己了。
如今我把小說正文校讀一遍(我自己的著譯出書后向來再懶得通讀一遍,現在我還是第一次據原文校讀一全本譯書),象過去讀過而近年來又找去重讀的一位小說藝術家朋友一樣,還是很能欣賞其中表現的小說創作藝術。中心人物柏格曼形象鮮明,生動;他是當時中、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有才華的藝術家的典型而具有個性;通過他表現了當時具有進步傾向而未能擺脫既定身分的知識分子的典型尷尬境地。不僅中心人物,不僅也作為小說人物兼故事講述者的“衣修午德”,有點自我嘲弄的,十分逼真,周圍人物,也都躍然紙上。衣修午德能用三筆兩筆、三言兩語,描寫出一個人物。三、四十年代間曾有人說過,他在人物塑造方面是英國狄更斯以后的第一人,寄予極大的期望(不容諱言,后來這種期望是落空了)。例如季米特洛夫的形象,在法庭上,只有幾句話,一個手勢,就活生生的“站起來”了。其他許多配角也都被寫得聞其聲如見其人。衣修午德在全書中著墨不多就能把西方攝影場生活寫得十分酣暢,淋漓盡致,同時又從容不迫,還可以借人物發議論,抒情。文筆明凈,一點也不拖泥帶水。
那么這本小說就算是現實主義的?可是你能說這里沒有浪漫主義了?而且不僅有關我們所說的廣義的兩大基本創作方法,這里顯然也有象征意義、寓言意味。而整書寫作手法又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一般手法,顯然有“現代主義”的烙印。
目前國內文藝批評界喜歡用“現實主義”一詞來譽揚作品。我不嫻熟文藝理論,但是憑我自己讀書和寫作經驗,我還是有一個不成熟的想法。我認為“現實主義”這個詞不免用濫了。我多少感覺到許多人用它的時候,總隱含有把“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假、大、空”社會現象都歸咎文藝上一度明白提出的“兩結合”中的“浪漫主義”了。其實廣義的(不是作為流派的)現實主義固然與“反映論”一致,但并不等同。廣義的(不是流派的)浪漫主義,也該是反映現實的,只是藝術表現手法上側重點有所不同而已。例如,你想贊揚司湯達,就說他是現實主義小說家,但是他的名著《巴瑪修道院》恐怕更多是浪漫主義的。至于“象征”手法,那是古今中外都有用到的,只是成為流派的“主義”,自然是另外一回事。今日國內關于西方“現代主義”爭論很多,往往把“現實主義”(說成是流派的)和“現代主義”(本就是流派)對立而談,我不以為恰當。真正有價值的“現代主義”作品也是“反映”現實的,其中往往也有廣義的現實主義,也有廣義的浪漫主義。只是時代變了,表現手法也不能墨守陳規,也得有所改變而已。由于歷史原因,我國較老一代作家和評論家不大熟悉西方“現代主義”作品;由于我們過去多少年閉關自守,較年輕一代作家和評論家甚至從沒有見識過西方“現代主義”作品,如今一下子主要通過翻譯(而有的翻譯又不夠理想)而接觸到一些,就感到奇特或者新鮮。其實,例如“意識流”寫法,最流行的時期可能是西方二十年代。現在很少小說家還通篇用意識流寫法。但是后來的西方現代小說家都受過這種手法的“洗禮”,都會用這種手法,不過只在需要的時候,偶爾來幾下而已。而可能歸入“意識流”派的法國瑪塞爾·普魯斯特和應屬正統“意識流”派的英國維吉尼亞·伍爾孚,也不象被后來的先鋒派奉為大師的喬埃斯后期小說那樣的破壞文法,另拼新字等等的標新立異。
衣修午德的《紫羅蘭姑娘》這樣的小說,卻也就不同于十九世紀歐美小說,也不能不說是“現代主義”小說,雖然也不同于今日西方一些思想混亂,故弄玄虛的時髦(當然也不能廣泛流行的)小說。正常的,有意義的各種“現代派”或所謂“先鋒派”小說,總不能和傳統小說完全割裂。現代小說家E .M.福思特的小說藝術理論中提出“渾圓(多面,有發展)人物”和“扁平(單面)人物”在一部小說里的配合作用,是一種現代新說,卻是結合自己的創作經驗,從研究古典小說得來的;衣修午德在這本小說里也就加以實踐。也可以說是“現代主義”小說較近的祖宗之一的亨利·詹姆士在后期小說創作里表現的一種技巧而被小說藝術理論家闡明的“角度”說(就是敘述故事的作者不充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的上帝,而從這個或那個人物的目擊耳聞來展現情節,以求逼真的寫法)也是從古典小說里比較,推衍出來的一種手法,衣修午德在這本小說里也運用自如。所以衣修午德三十年代寫希特勒上臺前夕柏林社會色相的小說和這本小說,既是傳統小說,也是“現代派”小說。
衣修午德的這種小說,現在,特別在美國,早被時髦小說家、趨時而自命高雅的小說讀者和評論家認為保守了,落后了。雖然如此,他收在《告別柏林》里的《薩莉·鮑爾斯》(應算是中篇小說,一九三七年先出過單行本,現在有巫寧坤中譯文,發表在《世界文學》一九八0年第二期上),從五十年代初起到七十年代初,曾一再被改編為戲劇和電影,在美、英、西歐上演和放映,獲得巨大成功。《紫羅蘭姑娘》一九四五年在美國出版,十天就銷售完,隨即被收入廣泛印行的美國“部隊讀物叢書”,現在當然也算不時髦了。我始終卻忘不了它。這不僅因為我是它的譯者,而且我和作者本人也有過一點私人交往。在這里我不妨補充提一提。
我譯了《紫羅蘭姑娘》以后和作者通過信,但是僅僅幾封(現在他給我的第一封信和最后一封還幸存了),也和他有一面之緣,那都是在三十多年前了。我在客居英國期間,在一九四八年夏天,有一天在牛津忽然接到阿瑟·韋利(有名的中國古典文學翻譯家)寫給我的一張明信片,說衣修午德回英國“探親”(用我們今日的言語說),極愿和我見一面,并告訴了我他所住的老家地址。我當即給衣修午德去了信,他回信約我在倫敦請我吃午飯。正合他一貫的風趣,他約我吃午飯的地方就是《紫羅蘭姑娘》里寫到的皇家咖啡館。席間他告訴我柏格曼是有原型的,名字叫貝托爾特,我現在忘記了姓什么,是一位名導演(但不是貝托爾特·布萊希特)。他向我推薦他的同代小說家亨利·格林的新著《歸》;在美國當代小說家中,他向我夸贊當時還不是很紅的年輕小說家特魯門·卡坡第的第一本小說《那些房間,那些聲音》。飯后,和小說里奧國人柏格曼反串給英國本國人“衣修午德”作導游相反,他認真帶我到泰特畫廊去參觀。在一層的樓梯頂上,他很熟悉的給我指出嵌花地板上一組希臘神話圖像是一位和布路姆斯伯利派(二十年代小說家維吉尼亞·伍爾孚、E.M.福思特、新傳記文學家里屯·斯特雷契、藝術理論家克萊夫·貝爾、翻譯家阿瑟·韋利等的文藝圈子,T.S.艾略特和年輕一代的衣修午德本人也曾出入過它的門下)有來往的藝術家的作品。他給我指出某個女神就是用的維吉尼亞·伍爾孚的頭像,某一個神則是用的斯特雷契的頭像,引起一些外國游客的注意,誤認他是導游了。有一點說起來奇怪,當時衣修午德在思想傾向上已不同于三十年代,消沉了,但是聽我談到中國就要全面變色(變紅)了,他就說:“那你為什么不早點回去呢?”這一句話倒多少促成我在一九四八年底前,一聽說淮海戰役打響,就決心撂下手頭未完成的工作,準備回國。以后我們沒有再通過信。一九八○年我雖到過洛杉磯兩天,也沒有預先寫信告訴他約見一面。得知他因病概不見客,結果未能一晤,深以為憾。他大概早已不記得我了。這也不足為怪,無關宏旨。
至于衣修午德,特別是他三、四十年代寫的小說,目前暫時被世人遺忘,也是文學史上的正常現象,卻是值得當代文學評論家關心。我個人深信,衣修午德的這本小說和《告別柏林》(至少其中的幾篇),比諸西方現在其實也無非為趨時文學評論家吹捧而并非自然廣泛流行的一些時髦作家的新奇小說反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甚至在今日西方,一方面安于逸樂,貪生怕死的社會,在刮起的象三十年代后期的綏靖主義、投降主義風里,從這本小說里也許還可以聽到一點警鐘,一方面彷徨失路的有心人也許也可以從中得到一點深省的啟發(不是問題的解答)。所以目前可能倒還又有幾分時代針對性。而我國的讀者以至作家,撇開這本小說里確有所表現而我當年加以闡釋的玄思奇想,我想,在得到一點思考材料和藝術享受以外,還可以在小說藝術上見識到一點新東西而不致迷失于可能的旁門左道。但愿如此,不辜負出版社重印的苦心。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九日
(新訂正《紫羅蘭姑娘》譯本即將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