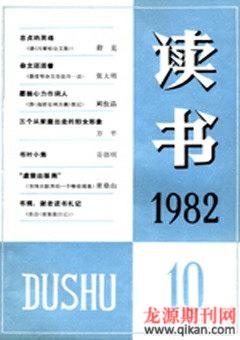小說道路上的足跡
周而復
上私塾以前,在家里父親教我《論語》,《孟子》和《千家詩》一類的書,從來不叫我讀小說;進了私塾,朱華老師教我們讀四書五經,不準我們看小說。我父親雖然不叫我讀小說,但也不完全反對我看小說,只要規定的功課做完了,看點小說并不禁止。母親喜歡聽故事,卻不識字,要佩芬姐姐讀小說,講給她聽。在私塾里,我不能看小說,一回到家里,可以參加聽姐姐講故事,有時功課沒有做完,忍不住偷偷地看些小說。我最初接觸的小說是手抄本《粉妝樓》和《兒女英雄傳》,以及油光紙印的《七俠五義》等。
看《七俠五義》,使我入了迷,幾乎廢寢忘食。俞曲園稱此書“事跡新奇,筆意酣恣,描寫既細入毫芒,點染又曲中筋節。”我入迷的并不是因為“事跡新奇,筆意酣恣”,是由于所寫的草野豪杰,游行村市,除暴安良,為國立功。這和我當時家庭貧 困,目睹社會上種種不公平的現象,對豪杰行為甚為羨慕,很希望有人出來“除暴安良”有關系,因此在我內心引起共鳴。這以后,還看了《說岳全傳》和《東周列國演義》等書。
但給我影響較大的是《水滸傳》、《三國演義》和《紅樓夢》。《水滸傳》的劫富濟貧,替天行道,我頗為欣賞,希望有這樣一伙英雄人物出現,改變社會上貧富懸殊的生活。每當我們家里靠典當還不能度日時,就希望能碰到“及時雨宋江”。當然,世態炎涼,不大容易碰見宋江的。對《三國演義》里的臥龍先生我十分傾倒,對他料事如神,指揮若定,才華蓋世,非常敬佩,可惜他壯志未酬,飲恨終身。
十歲那年,我找到一部插圖本的《紅樓夢》。我這個十歲孩子是不了解這本書的。能夠“解其中味”時,已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了。
接觸五四運動以后的第一本新小說是郁達夫的《沉淪》,接著又看了魯迅的《吶喊》與《彷徨》和茅盾的長篇小說,但看的更多的是外國小說。中學的英文課本大半是英美短篇小說。我課外特別喜歡看舊俄的小說,不管是屠格涅夫的,果戈里的,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安德涅夫的,還是托爾斯泰的,只要有,都拿來貪婪地看。
一九三三年考入上海光華大學英國文學系,做為英國小說的課本是奧斯汀的《驕傲與偏見》,薩克雷的《名利場》,狄更斯的《雙城記》和哈代的《卡斯特橋市長》等作品。老實說,做為課本來讀小說,并且聽教授講授小說發展史和每一部作品的背景、主題,結構和人物等,并不曾引起我多大的興趣。因為那些本國的和英國的教授本人并不是作家,自己沒有創作小說的經驗,不過根據《小說概論》這一類書來上課。我喜歡自己選擇小說看,這時的興趣轉到法國小說了,最初吸引我注意力的是短篇,如都德的《最后一課》和莫泊桑的《羊脂球》等。這和我處的時代有關,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后,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千鈞一發的時刻,和當年普法之戰有些類似,容易引起共鳴。
除了短篇以外,我讀得比較多的是大仲馬、福樓拜、雨果、司湯達、左拉、梅里美、羅曼·羅蘭和巴爾扎克等法國作家的長篇小說,每次從圖書館里都借來十本八本這些作品的中譯本或者英譯本,特別是巴爾扎克的作品,不管是長篇,中篇或者短篇,只要能找到,我都借來仔細地閱讀。
小說看多了,肚子里有話要說,對舊社會不滿的情緒要發泄,希望變革,自己并不是“君子”,就想學著用小說的形式來表現。大概是一九三五年吧,把我幼年和少年所知道的一些貧困生活和社會不乎之事,用短篇小說的形式寫了出來,懷著不妨試一試的心情,投給雜志,居然先后在《文學叢報》(聶紺弩、馬子華、田間和我等編輯)、《小說家》(歐陽山等編輯)《人民文學》(《文學叢報》遭到國民黨禁止發行以后,改名《人民文學》出版,創刊號也遭到禁止發行)和《東方雜志》(商務印書館刊行)等刊物發表出來了,算做“
蘆溝橋一聲炮響,敵人侵略的鐵蹄從華北進入華東,戰爭的烽火在上海燃燒起來了。上海不久成了孤島。一九三八年夏天,我離開孤島,經過香港,轉到武漢,到當時抗戰圣地延安去了。
國民黨當局雖然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要求之下不得不對日抗戰,紅軍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亦稱八路軍),但他卻調派大軍包圍封鎖陜甘寧邊區。邊區人民過著極度艱難困苦的生活,缺吃少穿。但困難嚇不倒共產黨人和邊區人民。中共中央發出大生產運動的號召,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邊區的黨、政、軍、民、學一齊動手,參加生產運動,開荒種地,紡線織布。我也參加了勞動的行列,學會種地、播種、收割、紡線。我于是寫了《開荒者》、《播種篇》和《秋收篇》,以及其他一些小說,有的發表在延安出版發行的《文藝突擊》半月刊上。
一九三九年秋天,我參加第十八集團軍總政治部所組織并領導的文藝小組,和魯藜同志一道隨總政治部干部隊,在三五九旅的一個連的護送下,一天一夜行軍二百一十華里,越過敵人同蒲路的封鎖線,到了遠在敵后的晉察冀邊區。
晉察冀民主抗日根據地是華北敵后的堅強堡壘之一。敵人每年定期有兩次大“掃蕩”:秋季大掃蕩和冬季大掃蕩,至于平時的大小戰斗就不計其數了。我在晉察冀軍區部隊里工作,一年幾乎有一半左右時間行軍打仗,即使不打仗,特別是到軍分區和團部里去的時候,隨時都有發生情況的可能,不是打起來,就是要轉移。在游擊區,一天晚上睡覺,常常要換兩個到三個地區,一有情況,便要轉移到二三十里外去宿營;剛睡到炕頭上沒有多少時候,發生情況,又要轉移,好在睡覺不脫衣服也不脫鞋子,一聽到緊急集合的通知(當時不能吹集合號,怕被敵人發覺。),站起來就走,倒也行動方便。這樣的軍隊生活,自然不能寫小說。
為了配合進行反“掃蕩”,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出版石印的子弟兵三日刊暫時停刊,改用油印機出版油印小報,發行到連隊,鼓舞斗志,和敵人進行拚搏。我為油印報寫火線下通訊,每當行軍休息,或者宿營以后,沒有桌子,就坐在地上,并起雙膝當桌子,放上一本書算是桌面,便寫千兒八百字的火線下通訊,都是真人真事,發表出來,傳到連隊,卻起了一點微末作用。一個反掃蕩與另一個反掃蕩之間,往往有一段比較平靜的時間,遇有空閑,便寫一兩篇短篇小說。
在我過去數十年業余寫作生活中,有機會集中時間寫點小說,只有兩次;一次是一九四二年冬天從晉察冀邊區回到延安,組織上安排我住在橋兒溝山上的窯洞里,給我時間寫作反映敵后戰斗生活的小說,與艾青夫婦和楊朔同志住在一起。當時作家原來大部分都住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里,因為開展整風運動,絕大部分都到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去了,只留下我們三個人從事創作。白天,大家在自己窯洞里寫作,晚飯后休息,聊聊天,種種菜。我種的是西紅柿,艾青夫婦和楊朔他們好象除種西紅柿之外,還種了茴茴白,就是洋白菜。
這段時間不久,大約三四個月的光景,整風運動深入發展了,我們也到中共中央黨校學習。雖然當時楊朔他們還沒有入黨,但也和黨員一道學習了。
另外一次是一九四六年到香港后,從事文化界統一戰線工作,日常工作不多,每天有半天以上的時間可以寫作。在三年左右時間里,我寫了兩部長篇小說一部中篇和一些短篇小說,這就是《白求恩大夫》、《燕宿崖》和《西流水的孩子們》等。
從一九三五年開始寫短篇小說,到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寫出最后一個短篇小說:《冶河》,估計不過寫了三十篇左右的短篇小說。為什么說“估計”和“三十篇左右”呢?因為一九三七年以前所寫的短篇小說全部散失了,即使在刊物上發表的,這些刊物也不大容易找到了,很難統計出一個準確的數字。
我所寫的中、短篇小說,雖然有的被選入《短篇小說選》或者《解放區短篇小說選》,甚至也有的被翻譯介紹到國外發表、出版,但我以為都是習作,并沒有編輯印行。一九四四年冬天,我到重慶新華日報社工作,參與編輯中國共產黨機關志《群眾》半月刊,這時,著名導演焦菊隱先生主持世界編譯所工作,承他垂愛我的習作,約我編一本短篇小說集交世界編譯所出版發行。對于他的厚意我是感激的,但要我編輯短篇小說集單行本,卻愧不敢當,禁不住他一再敦促,不得不勉為其難,收集八個短篇小說,名為《第十三粒子彈》交卷,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出版。這是用土紙印的,雖然個別的字不大清晰,但在戰時首都重慶,抗戰剛剛勝利就能印出這本小書來,確實很不容易。在這兒我要感激已經謝世的著名藝術家焦菊隱先生,如果沒有他的垂愛和敦促,我的短篇小說集不會較早問世的。一九四六年四月,此書改名《春荒》由上海華夏書店印行。
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我在香港工作,除了創作了上述小說以外,應新中國出版社之約,為他們編輯了一套《北方文叢》,向港澳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介紹解放區的文藝作品,每輯十本,有小說、散文、詩歌、戲劇和文藝論文等。我的兩個短篇小說集《高原短曲》和《翻身的年月》曾經收在《北方文叢》里。一九四九年初,全國即將解放,文化工作者和作家紛紛離港,我也和一百多位各界知名之士以及他們的家屬買舟北上了。《北方文叢》因此就沒有再編輯下去。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我隨第三野戰軍進入上海,二十七日上海全部解放。有一天,我碰到光華大學老同學趙家璧同志。抗日戰爭前,他在上海良友圖書公司主編良友文學叢書和中國新文學大系,頗獲好評,蜚聲文壇。良友文學叢書和美國的現代叢書(ModernLibrary)大小開本一樣,裝潢也差不多,所收作品為一時之選,甚受讀者和作者的歡迎。新中國成立后,看上去,他頗想重整旗鼓,再在出版方面干一番事業,著手編輯《晨光文學叢書》,編輯內容與開本和良友文學叢書差不多,已出版的記得有巴金的《寒夜》、《第四病室》和老舍的《四世同堂》等數十種。他約我編小說集列入晨光文學叢書。遵囑將《翻身的年月》和《高原短曲》交他出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約我出一本短篇小說選集,我便從手頭有的一部分短篇和中篇小說(因為有些短篇小說不在手邊或者遺失了)中選了十篇,加上兩篇報告文學,一共十二篇,題為《山谷里的春天》交出版社于一九五五年四月出版。
過去一共只出了五本中、短篇小說集,部分還有重復的,可見我寫的短篇小說之少,質量我更不滿意。
新中國第一面紅旗升起以后,我一直在中共中央華東局,中共上海市委,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和文化部擔任工作,比較繁忙。但我始終忙里偷閑,見縫插針。古人惜寸陰,我是分秒必爭,每天盡可能擠出一點時間來讀書和寫作,寧可犧牲睡眠和休息時間。這時我業余的主要精力化在創作長篇小說上,即《上海的早晨》,因此就沒有時間再寫短篇小說了。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六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