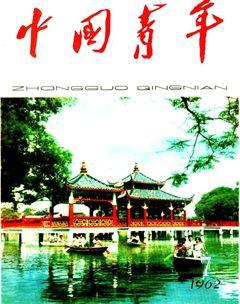拜年
浩然
農歷正月初一早晨,鄉親們仍是按照老習慣互相拜年。從第一聲爆竹響起,村子里就熱鬧了;貼著春聯彩畫的門口,打掃得干干凈凈的街道上,都活動著穿戴整潔、滿臉喜氣的人群;空氣里震蕩著歡笑聲,混和著煮餃子、燉豬肉的香味兒。
宋三爺在吉素村輩數最大,人緣也最好,往常拜年,大伙幾總是先從他家開始;今年誰也沒有跟誰商量,就都自動地改變了路線。聽說宋三爺沒結婚的三女婿來拜年,這是一件新鮮事兒,眾人要最后歸到宋家,多坐個時辰,湊湊熱鬧。
宋家三口最高興,也最忙;三個人三個心眼兒,忙得也不一樣。
宋三爺是個好體面的人。他是隊里有名兒的老積極,去年勞動一年,接連著受表揚,干活兒爭強奪勝,愛社不甘下風;就在生活里的一些細小事情上,也總要比別人高出一格。沒結婚的女婿第一次登門,他覺得十分光彩;人家又是農具廠的工人,工農本來就是兩親家嘛,加上這段姻緣,更是親上加親;這是他在眾人跟前顯頭露臉的機會,決不可放過,更不能在客人面前丟丑。
天不亮宋三爺就起來了,把院子打掃得象場板似的,建一塊石子兒、一片柴草葉都給他揀走了。他還把棚里肥滾滾的山羊,故意拴在豬圈前邊最顯眼的地方。房檐下掛著的兩大嘟嚕玉米,本來用草遮著,宋三爺把草拿掉,叉把上邊的坐土打掃凈,旁邊配上兩串鮮紅的干辣椒,把它襯托得特別金黃耀眼。廂房是他這個老保管的倉庫,他除了用春聯上的字句表示了此地重要之外,還學著鎮上糧站的樣子,裁了一張長方的紅紙,寫了“倉庫重地,謝絕參觀”八個大字,貼在門上。
這一切都是可以讓那位工人一進門就感到,這個生產隊生產搞得很出色,社員的生活安排得也滿好;這是個豐衣足食、日子昌盛的家。
院子收拾完了,宋三爺又開始布置屋子,屋子里更進了一層。平時舍不得用的一只雕花紅漆桌,擺在炕上了,桌子旁邊鋪著一條北京清河呢廠出產的花毛毯,這是女兒進京開會的時候買來的。宋三爺最熱心顯示的是北墻壁。那邊,毛主席畫象兩旁掛的是他和閨女玉娟的模范社員獎狀。那是去年抗旱播種和消滅蟲害兩次戰斗中得的。兩次戰斗,使老人家深深地懂得了“人定勝天”這旬話的意義,也讓他受了一場鍛煉。兩張售賣超額余糧的收條,本來無須保存,他卻從柜子里找出來,小心翼翼地貼在獎狀的下邊。掛在偏右方的那一面紅緞子獎旗尤其引人注目,上邊繡著“戰勝災害奪豐收”七個金黃的美術字兒。這旗子是他昨晚上從會計那里要來的,他借口保管員要保管生產隊所有的財富,實際上卻是為了給自己裝裝門面。有了它,給這個小屋子增加了無限的光彩呵!
這一切都可以無聲地向工人貴客表示:這個生產隊的生產之所以搞得好,是社員的干勁高,兩張獎狀能夠顯示這一點;搞好生產,不是憑那一個人的本事,得靠大家伙幾一條心,一股勁兒,那面紅旗可以說話;社員積極生產,并不是光為自己,是為國家建設,為支援工人老大哥,那兩張出售余糧的收條,不就是最好的證明嗎?
宋三爺手忙腳亂地收拾完畢,又里里外外地自我欣賞一遍,這才心滿意足地在那只鋪著新氈墊的春凳上坐下來,悠然自得地抽煙,等候貴客。
三奶奶是個“內熱”的人,她想得實際,做得也實際。作娘的都有一付永不滿足的心腸,玉娟是她的三閨女,是她填補心愿的柜子。大閨女才滿七歲,斗紅高粱就賣給人家當了童養媳婦,上頭①那年鬧旱災,大年初一女婿照例該來丈人家拜年,可是那邊買不起二斤粗點心的禮物,這邊也做不起一頓有糧食的飯招待;一切從簡,女婿空著手來,扶扶水缸就走,三爺又嫌丟臉,兩頭老人暗地里一商量,免了這個禮兒;年輕人不明白老人的難處,女婿一氣,十年沒登過丈人家的門檻。三奶奶覺著欠了債,對不起閨女,每逢年關佳節,別人家迎送女婿,她就痛心地流淚。二閨女攀了個高枝兒,找下闊婆家。老倆口要填補心愿,從秋天起就一點一滴地節省、積蓄,到了年根下又借了一筆吸血債,割了肉,磨了面,建細盤子、花瓷碗都借下了。她也象今天這樣高高興興的準備迎接貴客;可是那邊嫌棄宋家日子貧困、門戶不對,女婿根本沒有理他這個茬兒,面也沒有見。三奶奶無端無由地埋怨著自己,覺得對不起閨女,每逢年關佳節,誰若是提起女婿拜年,就氣得渾身發抖,牙根兒疼。
三閨女玉娟可趕上如今這個好時光了。日子過得昌盛,誰不知道吉素是全公社的豐產隊?家庭是體面的,誰不知宋家三口出了兩個有名兒的模范?沒結婚的女婿上門來拜年,已經使老人家高興了,而女婿的身份更增加了一個丈母娘的榮譽感。人家是農具廠的技術員兼副廠長,還是盤山里有名氣的老鐵匠“鋤頭李”的后代;據社員們說,隊里使的鋤、鐮、锨、鎬,還有雙鏵犁、播種機,都是女婿那個工廠造出來的。春天,正是播種的季節,滴雨不落,墑情又不好,社員決心要抗旱點種,種著種著到了山根下,離著井水遠,渠里的水也引不上去了,就在這個當口,跟天兵下降一般,農具廠送來了車拉水箱。沒見那水箱哪,一箱能裝四十多挑子水,頂四十個棒小伙子;下邊安著滾珠軸承膠皮輪,走起來風快,棒小伙子也攆不上,這一車就把一畝地種上了,多救急!六月里起蟲害,大片大片地超,莊稼棵里打疙疽,站在地頭上,就聽得刷刷響,讓人心焦!社員要在蟲子嘴里奪糧食,藥粉成車往地頭上拉,滿地的噴霧器吱吱晌,把筒子打得燙手熱,消滅一片又一片,可恨的蟲子在后邊又跟著起來了。比及時雨還要及時,農具廠又把馬拉的噴藥車送到地里。沒見那車哪,十個頭安在尾巴上,走起來象下雨,一噴一大片,走多快,噴多快,一個來回就是二畝地,看蟲子還能不能!都傳說,這兩種新東西都是三奶奶的女婿跟他爺爺“鋤頭李”發明創造的。對于女婿,她從來沒有見過,就憑他不辭辛苦,處處為農民打算的熱心腸,就實在討她歡心了!
有這樣一個女婿,怎么會不讓老丈母娘稱心呢!她比老頭子起得更早,切菜、剁肉、合面,天不亮,她就包完了兩大蓋lian小餃子。那餃子是純肉丸的,白菜、蔥花只是當作料;那面是頭羅白,雪花一般。她精心致意,施展了老手藝,把餃子捏成花邊兒、鼓肚子,一般大小,一個模樣;一圈一圈地擺在蓋lian上,一眼看去,就如同在北京城里玉石刻的浮雕。接著,她從房背后草堆里翻出個大凍柿子,這是傍年根前隊里分給社員的;她用涼水把柿子洗凈、擦干,擺在花瓷盤子里化著,活象一座紅琉璃的小塔。她又從罐子里揀出一些山里紅、大棗兒,分別放在兩只大海碗里,活象兩碗珍珠、瑪瑙。另外還炒了一盤向日葵籽兒;女婿要是不吸煙,就一邊說話,一邊嗑著吃。
現在,三奶奶總算坐下來了,她坐在離灶火不遠的水缸旁邊的蒲墩上,一邊慢慢地摘豆芽兒,一邊想著心事,打譜炒幾道菜下酒,她想得多,做得多,卻顯不出半點激動和忙亂,一如平時,有板有眼,平平靜靜。
最慌亂,最激動的要算三閨女玉娟了。她處處都隨她爸爸,就好象是一個模子里托出來的;紙糊的燈籠里外亮,肚子里的話兒掛臉上。她數了一夜窗戶格子,早晨起來,她幫過爸爸,也幫過媽媽,什么活兒她都擱過手,什么活兒她也沒有做出來。點著柴禾,她忘了添水;舀水的時候,卻抓過一把鐵絲兒笊籬。燒一鍋開水的工夫,她偷偷地跑到大門口張望了三次,中間還溜進自己房里照了兩次鏡子。
她希望自己那個人今天打扮得非常標致、漂亮,第一眼就給村里人留下一個好的印象;就討得爸爸媽媽的歡心;雖說,很多人都認識這位工人,可是人們對于最熟悉的人,一旦要當新女婿了,也總是另眼看待,仔細觀察,總要留神平時不留神的地方。等他拜了年,離開吉素村,她就可以紅著臉,噘著嘴幾,扭過頭去,卻是張著耳朵去聽取別人的夸獎、贊美,她應當,而且能夠享受到這一切的。今天她自己的打扮,就苦費了一番心思。別看她平時干起活來是個橫沖直闖的莊稼姑娘,美,卻總是她生活里缺少不了的內容,就連下地挑大糞去,臨出工之前也要穿戴得整整潔潔。今天在一個初戀的姑娘來說,是個萬分寶貴的時光,她要把自己打扮得更美!
鏡子擺在代替梳妝臺的方桌上。鏡子擦得亮光光,她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鏡子里立刻照出另一個俊姑娘。她又象玉娟,又有點兒不象;那生來就曲卷的頭發,那略有幾顆小小雀斑的圓臉,是她自然健康美的象征;那個緊閉著的、帶著挑皮神氣的紅薄嘴唇,是她對新生活充滿著信心和神往的內心流露,如今,又好象憋著多少秘密要對別人說,又不肯講出來。她看著看著,眼神漸漸模糊不清,鏡子里忽然間變成一張男子的臉。那張四方的,微黑透紅的臉,雖然依舊不失鐵匠固有的嚴肅和堅強神氣,卻掩不住地帶著一種甜蜜的,迷人的微笑;他笑的時候,黑眉毛
總是往上挑起,大眼睛卻細成一條縫兒,讓人感到他質樸又天真。工人帽斜扣在后腦勺上,分不清是蘭是青的工人服上,除了油煙子,就是被火星燒得大大小小的窟窿眼兒——老天爺,他怎么這個樣子就來了!你是來掄錘,你是來拉風匣,你還是來收廢鐵?
這正是玉娟第一次跟他見面的樣子呀!
那是前年秋天的事情。
盤山前的谷子熟了,玉娟領著社員開始收割,還跟別的隊挑戰比賽。可是不到半天的工夫,就有十幾個社員找她換鐮刀,這個說鐮刀鈍得不能使,那個說鐮刀卷了刃;開頭玉娟還是大嚷大叫地讓大伙兒對付一下,沒多久,她自己的鐮刀也變成了禿菜刀。她火了。
“這是那個倒霉的地方出的?”
“邦均農具廠唄!”
“我找他們算賬去!”
于是,她把所有的壞鐮刀裝在筐子里邊,背到鎮上,一進車間大門,就嘩啦一聲,把鐮刀倒在地下,兩手插腰,怒眉立目地喊:“喂,這是誰的手藝?”
正干活兒的工人們都給這個愣姑娘鬧懵了,一個黃白頭發的工人瞟她一眼,問道:“同志,別這的大氣,怎么回事呀?”
“我問你這是誰的手藝?”玉娟用腳尖指指地下的鐮刀說。
“這是大伙打的。”
“我看你們都不用吃飯了,鴨子也能打出來呀!”
“有話盡管說,別罵人呀!”
“罵人,這還是好聽的吶!”玉娟滿肚子火氣頂嗓子,朝那工人眼前湊了一步說:“你們耽誤了我們多少活計,谷子爛在地下收不上來,你們負責任嗎?退吧!”
“這鐮刀農具供應站包售,你在那兒買的那兒退去。”
“我不管那兒買的,是你們打的,你們就得給退!”
“這人真厲害……”
“厲害,咬你了?”玉娟翻了翻眼珠子說:“你不懂人話,你們頭呢?”
就在這個不可開交的時候,從里邊走出一個高個子工人。他方臉濃眉,斜戴著工人帽,身穿著窟窿的衣服,圍著說灰不灰,說白不白的圍裙。他一面朝這邊走,一面拿被煤屑沾黑的毛巾擦汗,和氣地對玉娟說:“別著急,別著急,有話兒慢慢講。”說著,搬過一只凳子放在玉娟身邊:“同志,請坐,請坐。”又端過一杯白開水。“同志,喝水,您有意見對我說吧。”
真怪,玉娟朝那工人的臉上掃一眼,心里的怒火,立刻消去一半。她看到那張嚴肅的臉上,洋溢著熱情和誠懇的神態,自己倒有些不好意思,聲調也自然低了,說:“照你這樣,話還好說。你們這鐮刀簡直象木頭片子,一使就卷刃!”
工人從地下拾起一把鐮刀,看了看又問:“這是麥收時候買的吧?”
玉娟說:“割麥子倒對付,麥子跟谷子不一樣呵!麥子一碰就折,割谷子可得使大勁兒!”
工人聞聽,驚奇地看了姑娘一眼,醒悟地低聲說:“這一層我們可真沒有想到。”就用大拇指試試刃,放在耳朵下邊敲敲聽聽響,又說:“火候軟。我們一定包修、包換。您先回去……”
“馬上就退吧!”
“退了你們使什么,那不耽誤生產囑?”
“你說怎么辦?”
“一起晌我就把新鐮刀給您送地里去,行吧?”
玉娟回到家,火氣一消,又覺著自己太莽撞了,實在對不起人家工人;這么熱的天頭,何必勞累人家給送來呢!她沒有吃飯,就又往回折,半路上,正巧碰見那個年輕的工人騎著車子送新鐮刀來了。
工人跳下車子,從后架子上解下一捆鐮刀,對玉娟說:“這些鐮刀又都加了一遍火,您使使看,不行的話,再找我們,反復搞幾次,慢慢地就可以摸出經驗來了。”
玉娟一再道謝,又不好意思地說:“剛才我太火性了,說話不大好聽……”
工人說:“谷子要緊著收割,這事情放在誰身上也要著急的。”
看人家多會體貼人,玉娟心里很感激,就問:“同志,您貴姓呀?”
“我叫李貴庭,您叫宋玉娟,對吧?”工人微笑地說著,又從衣袋里掏出一只小本子:“您這次到廠里去,把我們提醒了:辦工廠不能關著門兒——我們過去不就是關著門兒嗎?關著門兒開會、研究,關著門兒制造,制出來就出售;滿心是想支援農業,制造出來的東西到底合用不合用,農業還缺什么,我們可就捂著耳朵不聽了。這回我們要堅決改。您就當我們的義務參謀吧,這本子您收下,隊里對我們生產的工具有什么意見,另外還有什么要求,您就記在這本子上,您趕集時順便就跟我們說一聲,沒工夫去,求別人把本子捎去也行。”
……
這一天,玉娟從工人那里換回來鐮刀,換回了信任和鼓舞,也換回一種莫名其妙的感情,那個高個子、斜戴工人帽的身影,那張嚴肅、堅毅的面孔,常常在她眼前出現。那個白報紙本成了她的日記,她在上面寫下了許許多多的話,也寫進一個農村姑娘的熱烈的,心情。這本子在工廠和農村之間傳遞著,它象一片肥沃的田地,在這個農民和工人的汗水和心血灌溉下,結出碩果。春天抗旱播種的時候,姑娘在生產隊的燈下,把希望的種子埋在本子里;傳到工廠之后,在工廠的洪爐旁邊,一輛輛大水箱和噴藥車就誕生了……愛情,也跟著一切果實豐收來臨了。姑娘的心,漸漸地給工廠里那顆心吸住了。玉娟每次到邦均趕集,總是把牲口拴在農具廠的大院子里;有些東西臨時弄不回來,也存在那兒;她還帶著一群姑娘在工廠里看過兩次電影;八月中秋到鎮上看戲,社員們坐的凳子,都是玉娟從農具廠搬來的,農具廠食堂還專門招待他們喝茶水。這樣一來二去。風言風語就就在村里傳開了。姐妹們另眼看她了,小伙子們跟她開起玩笑,爸爸媽媽耳聞目見,也是無聲的贊許:這一切都如同金皇后②吐線、壯漿時候的一場甘露雨,催促了這顆愛情果實的速快成熟……
姑娘變得更神氣了。幸福的時代,人人都是幸福的,她卻總覺得自己比別人更幸福;她不錯過一切機會,要向村里的每一個人顯示她的未婚夫。眼下是新春佳節,人齊全,又閑暇;只要他一來,全村的男女老少,沒有一個人看不到,以后,會有多少人議論他,該給她增添多少光彩!
三奶奶在外屋喊叫起業:“玉娟,你這猴丫頭,鉆到屋里干什么去了?火都燒到灶膛外邊了!”
玉娟被嚇了一跳,立刻從夢一般的甜蜜回憶里驚醒了。她象一只小山羊似的從屋里跳出來,紅著臉,把木柴踢進灶內,又使勁跺跺腳,抖下跳到花鞋上的灰燼。
三奶奶又說:“都這個時候了,怎么還不來,說不定不來了……”
玉娟實在不愛聽這句話,把小嘴一噘說:“人家可不是那種人,說到那兒,就辦到那兒;象您說話不算數!”
“喲,瘋子,我怎么說話不算數了?”
“貴庭信上說不讓咱們破費鋪張,隨便做些吃的就行了,昨晚上您滿口答應,可是……”
“過年過節嘛,他不來,我們也是照樣吃喝;媽要是舍不得給他吃,把什么都藏起來,你該又生氣了!”
玉娟捂著嘴,嘻嘻地笑了起來。
宋三爺被母女倆的說笑聲驚動,磕打了煙袋灰,從屋里走出來,站在門口,看看東升的太陽,聽聽街上的鞭炮聲、嘻笑聲,又轉過頭來問閨女:“玉娟,你們把日子訂妥了沒有?才八里地,不要說騎車子,就是步行也該早到了,說不定忘了吧?”
玉娟又噘起嘴,說:“人家腦筋可好吶,那么復雜的機器都裝的下,這點小事情就忘了,照您記性不好?”?“嚯,我記性怎么不好了?”
“人家從保管股借筷子那么長一節兒拴口袋繩,您還要記賬吶!”
“那不是記性好不好的事情,那是規矩。”
這工夫,拜年的鄉親們把全村都轉完了,繼續行行的地朝宋家奔來,歡笑的聲浪,從街口泛進宋三爺的小院子里。
“三爺,貴客還沒到哇?”
“恭禧,恭禧。玉娟,新女婿的架子不少吧!”
玉娟自己也奇怪,為什么忽然間忸怩起來了?她臉上一熱,蹭地一步跳進自己的屋子里。堂屋和爸爸屋里那么沸騰歡樂的聲音,一點兒也進不到她的耳朵里去,她極力地注意著院子里的動靜。院子里只有肥豬撞擊著圈門的光當聲和山羊的咩咩地叫喚。她心里十分焦灼,不由得從衣袋里掏出一個小紙團,小心地抖落開,仔細地看了一遍。這是李貴庭前天求趕集的人捎來的,上邊明明寫著,今天早起來拜年,吃了飯走,這怎么會錯呢?就算臨時有了事情不能來,也會再捎個信來。喔,說不定他走錯路了。這邊好幾個村都叫吉素,西邊大吉素順道又出名,說不定他撞到那里去了。想到這幾,她悄悄地把門簾扒開一道小縫朝外看看,只見西屋的人們讓煙讓水,說說鬧鬧,誰也沒留神,她就來個閃電式,幾步跨到院子里,撒腿就跑。
過了一道溝就是大吉素村。鞭炮聲、廣播喇叭唱,和那滿街鮮紅的春聯、穿著花衣服的孩子,都不能引起姑娘的注意,她被路面浮土上的兩道自行車轱轆印吸住了,她熟悉這花紋似的印痕,就如同熟悉這車子主人的手紋一樣。李貴庭果然是走錯了路,鉆到這兒來了。她順著車轱轆印往前走,走著走著,一面通到二隊的隊部門口。一輛飛鴿牌自行車停在那兒,車把上的絲線把套是她織的,把套上垂著的兩個穗子,是她從發繩上剪下來的;車座的套子上的花是她繡的,那上面折邊花布,是她做棉襖裁剩下的;車后架搭著一個上馬上③,一頭裝著一個用彩紙包裝的點心匣子,這可真象新女婿拜年的派頭了。
姑娘的心里跳了,臉上笑了,她剛要開口喊,忽聽得屋里暴發起一陣哄笑和鼓掌聲。
“靜靜,靜靜,讓李廠長說完嘛!”有人大聲地維持秩序,好久才安靜下來。
“我沒有好多話講,今天就是來給農民同志們拜年,順便跟大家要點禮物。”這正是她的李貴庭的聲音。
“說吧,要什么給什么!”一個老人的聲音。
“工廠支援農村,農村也要支援工廠嘛!”一個女人附合。
“別的不要,就要大伙幾對農具廠的意見。”李貴庭用鐵匠常有的那種高昂洪亮的嗓門說:“去年我們制造的工具,那一些好用,那一些不好用;還有,按著你們今年的生產計劃,我們農具廠還應該增加什么新品種……。”
又暴起一陣笑聲和鼓掌聲。
“不得了,工人老大哥跑到我們門口征求意見來了!”一個人大聲地贊嘆說。
“對。去年我們跟幾個隊掛了鈞,用意見本或是請農民到我們工廠里提意見,這辦法的收效很好,可是太不夠了。從今年開始,我們工廠領導分工包片,定期下來登門拜訪。”李貴庭叉樂呵呵地說:“平常日子大伙不得閑,難得象今天這么齊全,就講各位先提意見吧。”
“不忙,不忙,吃了飯再說。”
“對,李廠長到我家吃,還有白干酒哩!”
“不了,謝謝各位。”李貴庭客氣地說:“一會兒我還要到三隊,中午前趕到小吉素,到那兒看個親戚……”
“是給老丈人拜年吧?”
“真是公私兩利,這樣咱們可不能強留了!”
又是一陣哄笑。
在笑聲中,玉娟已經跑回家。
三奶奶驚喜地站起身:“看你這鬼丫頭樂的,他進村了吧?”說著,她趕忙往灶膛里加把火,又把切好的菜和肉看了一眼。
宋三爺也迎出屋:“怎么這時候才到?是騎車子還是步行,沒帶別的朋友來嗎?”他說著,看了看拴在院子里的山羊和倉庫門上的紅色的方紙塊。
來拜年的鄉親們也涌到門口,擠著朝外看。
玉娟喘著氣,忍住樂,對眾人說:“都請屋里坐,屋里坐,還沒到吶!”等大伙兒都轉回屋里,重又坐定,她急忙從抽屜里拿出那個白報紙本子,又抽出鋼筆,往雕花的小炕桌旁邊一坐,說:“大家給農具廠提些意見吧!去年他們打出來的東西那些應該改進;按著我們隊今年的生產計劃,還需要他們制造什么新工具……”
宋三爺一楞:“怎么回事兒呀?”
三奶奶把嘴一噘:“這丫頭真瘋了!”
玉娟撒嬌地把頭一晃:“這樣先下手,節省他一點時間,好多走幾個村。”
“節省什么時間?”三爺問。
“走什么村呀?”三奶奶也問。
玉娟認真地說:“人家正在三隊,一會兒就到咱們這里來;人家不光是為了拜年,還要征求對農具廠的意見……”
老倆口和拜年來的鄉親們這才恍然大悟。
一九六二年二月六日草
①上頭即正式結婚。
②玉米的一種。
③有地方稱褡褳,類似布口袋,兩端裝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