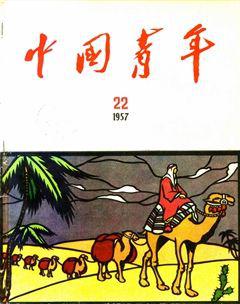怎樣認識提高業務和勞動鍛煉的矛盾?
吳榮立
黃玉麟說,領導批準他到農村參加勞動生產,他最大的顧慮是業務問題。黃玉麟所提出的業務和勞動鍛煉的矛盾問題,正是我兩個月以前報名參加農業生產的時候所存在的思想問題。現在把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過程談一談,或許對黃玉麟有些幫助。
我是一個共青團員,1949年參軍,1953年轉業后,考入北京土木建筑學校,1956年8月畢業,分配到機關做技術工作。參加工作以后,深深感到技術能力不高,一直認為我最迫切的問題是提高業務。正當這時候,機關里卻提出了下鄉參加勞動生產的號召,我和黃玉麟一樣,思想的確想不通。我的學習計劃被打破了。在討論參加農業生產的會上同志們發言很熱烈,我卻不敢堅決表示態度。
但我的思想長久不能平靜下來:像我這樣一個參加革命工作不久的知識分子干部,政治和業務都不強,都需要提高,但什么是最迫切的呢?我把這個問題向團支部書記談了。他反問我說:“小吳,回想一下你在整風和反右派斗爭中有什么問題,想清楚后,你就知道該怎么辦了。”
團支部書記的話提醒了我。反右派斗爭以來,對我的思想震動很大。在這以前,我認為自已在政治上是有本錢的:革命人生觀基本是堅定的。但經過整風反右派才真正考驗了我。整風初期社會上的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我們機關里的右派分子也乘機蠢動,他們說什么“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囂張狂妄到極點。可是我卻看不出問題,只是感到他們有情緒,而對他們的某些論點還有些同情。社會上反右派以后,我還認為我們機關里沒有右派,經過同志們揭發出他們的大量言論和行動,我才警惕起來,但思想感情上又沒有激起深刻的階級仇恨,對右派分子的批判也不是很有力的。而這時候,工人農民卻教育了我。當時我看到報紙上工人農民對葛佩琦的反動謬論嚴厲駁斥,北京印刷一廠的工人拒絕排印反動刊物“廣場”。不有,當時我為了抓緊鉆研業務,天天跑到工地上去研究問題,而工地的工人卻對右派的言論忍無可忍,要求停工一天到北大去向右派分子說理。我呢,對機關的整風學習卻不感興趣。這是多么鮮明的對比啊!這不得不使我猛醒,我為什么會這樣呢?我的革命熱情是怎樣冷淡下來的?我這才想到這幾年來,我的思想在變化。自從轉業以后,我接受了資產階級單純技術觀點,認為革命已經勝利了,今后就是靠技術吃飯了。我把一切業余時間和精力都集中在鉆技術,真是做到“兩耳不問窗外事,一心只讀技術書”。這樣我對國家政治生活就逐漸疏遠了,漸漸失去了政治敏感,所以在這次風浪中表現了立場不穩,受到右派的迷惑。我難道不是也學過一套理論嗎?但是為什么我的政治覺悟遠遠不如理論程度比我差的工人農民呢?歸根結底,是我一天天掉入個人主義的泥坑,缺乏勞動人民那種對黨和國家血肉相連的感情,所以在黨受到攻擊的時候,我沒有切●之痛,對人民未來的命運表現漠不關心。對一個青年來說,提高政治覺悟,提高業務能力都是重要的,但政治是一個人的靈魂,它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如果我的思想不改造,即使有很高的技術,我怎能為人民服務呢?而事實巳經告訴了我,要真正具有勞動人民的感情,單純靠學習理論,顯然是不行的。
思想斗爭勝利以后,我向組織堅決表示下農村去的決心,要求第一批批準我。我現在認識到如果說我今天有些技術知識,這是黨用三年時間培養了我,為的是用技術知識建設社會主義。今天,黨要把我送到農村中,是更進一步培養我,要我在勞動中鍛煉勞動人民的立場和勞動的本領,也是為了使我更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我下去以后,雖然在技術上荒廢了幾年,但卻能獲得寶貴的工農感情,把思想武裝起來,有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這對一個共青團員來說,才是最寶貴的。在一個人一生的事業中將發生不可估量的影響。黃玉麟和我同樣是共青團員,我希望他不要辜負黨對青年知識分子的教育和期望,我希望他堅決到農村去,徹底改造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