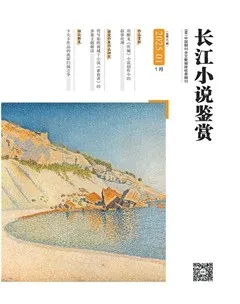女性的位置:從“啟蒙”到“革命”
[摘 要]《傷逝》和《我們夫婦之間》是兩部探討婚姻與愛情主題的小說,均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一篇聚焦“啟蒙”主題,另一篇圍繞“革命”展開,在歷史發(fā)展和文本內(nèi)容方面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從妻子的角色定位、夫妻關(guān)系的變化和文本敘事三個方面對比分析兩部作品,我們能在比較研究的視角下發(fā)現(xiàn)一些新的問題和現(xiàn)象。
[關(guān)鍵詞]《傷逝》" 《我們夫婦之間》" 女性位置
[中圖分類號] I207.4" " "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 A"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5)01-0003-06
五四運動以來,女性獨立于家庭之外的自我主體意識不斷覺醒。作為魯迅唯一一篇以愛情為題材的小說,《傷逝》表達(dá)了他對女性處境的擔(dān)憂、關(guān)切,以及對女性獨立的呼吁,同時也是他對五四運動后個性解放、戀愛自由、婚姻自主熱潮的反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涌現(xiàn)出許多以女性解放為主題的作品,其中《我們夫婦之間》便是蕭也牧對女性重構(gòu)社會身份的思考。
首先,兩篇作品都是以知識分子為第一人稱進(jìn)行敘事,這在客觀上造成了作品與主流話語之間的疏離。《傷逝》中,作者作為隱藏敘述者與“我”產(chǎn)生了不同程度的分裂,這體現(xiàn)了作者對知識分子身份的內(nèi)在焦慮和反思。而《我們夫婦之間》中,敘事的作者與“我”的分裂感并不明顯,缺乏敘事上的張力,反而更多地表現(xiàn)了作者試圖繞過主流話語進(jìn)行自我表達(dá)的欲望。其次,兩篇作品都塑造了妻子的形象。盡管《傷逝》描繪的是五四時期知識青年的戀愛悲劇,探討的是啟蒙與被啟蒙關(guān)系,而《我們夫婦之間》則呈現(xiàn)了根據(jù)地時期知識分子與勞動人民結(jié)合的革命者婚姻,敘述了革命背景下的故事。兩篇作品都以獨白式的敘事手法描寫了失敗的婚姻,刻畫了兩位性格鮮明、異中有同的妻子形象。本文將從妻子角色定位、夫妻關(guān)系變化、文本敘事等角度切入,分析兩篇作品從“啟蒙”到“革命”中顯現(xiàn)出的問題。
一、妻子的角色:女性主體重構(gòu)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指出,女性并非在自我認(rèn)同,而是在男性目光的影響下自我物化。女性之所以成為女性,是被社會所建構(gòu)的[1]。約翰·伯格在《觀看之道》中也表達(dá)了類似的觀點:女性展現(xiàn)氣質(zhì)的行為具有自反性,因為女性的主要觀察者是男性,因此女性往往會將自己視為一個獨特的景觀來對待[2]。對于女性而言,她們既是觀察者又是被觀察者,不僅要讓他人感受自己的美,還要自我審視這種美,甚至觀察他人對自己的觀察。女性通常根據(jù)他人的觀察來審視自己,通過父權(quán)制社會的標(biāo)準(zhǔn)來塑造自我。在父權(quán)社會中,女性只能是被觀看的“第二性”,而男性則通過各種媒介和渠道享受“麥茨式的窺視愉悅”(指觀眾通過電影窺視他人生活和體驗隱秘內(nèi)容時獲得的心理滿足和快感),人們將“男性凝視”視為理所當(dāng)然,使其成為主導(dǎo)性的觀看行為。
自古以來,由于女性生理特點和社會分工的不同,社會更多地以家庭婚姻的完美程度作為評判女性是否成功的標(biāo)準(zhǔn)。女性因自身的母性特征,會積極地把孩子以及與孩子密切相關(guān)的丈夫作為保護(hù)的對象,這使得包括子君在內(nèi)的大部分五四時期的女性選擇以家庭作為人生的重心。《傷逝》中,子君投身于家庭,卻未意識到工作與經(jīng)濟(jì)獨立才是擺脫女性困境的唯一方法。而涓生打著男女平等的旗號,卻將女性的主觀能動性壓抑得更厲害。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女性邁出了追求平等和自主的第一步,女性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數(shù)。小說的最開始,子君代表著五四時期婦女婚姻解放的新要求:反叛家庭,毅然出走,追求自由的愛情,并自主決定自己的婚姻。在與涓生交往半年后,她曾“分明地、堅決地說‘我是我自己的’”[3]。在與“鼻尖的小平面”和“半瓶雪花膏”的對立中,她順應(yīng)了五四運動后個性解放旗幟下青年知識分子的趨同心態(tài),加快了追求愛的步伐。但步入婚姻后,她的生活逐漸脫離了詩詞歌賦的浪漫,開始面對家庭瑣事,而導(dǎo)致這一切改變的根源便是她曾經(jīng)追求的愛情。婚姻被視作愛情的墳?zāi)梗媪俗泳龑D女解放抗?fàn)幍慕K止,同時也預(yù)示著20世紀(jì)20年代中國作家群體對于女性主義和女性解放的思維疆界,即他們的認(rèn)知與審視更多地停留在通過反抗傳統(tǒng)封建男權(quán)而實現(xiàn)走出原生家庭、實現(xiàn)婚姻自主的階段,卻很少真正考慮女性進(jìn)入婚姻后可能會面臨的各種問題。那么,女性將走向何方?子君這類人物要以何種方式才能真正獲得解放,而不是穿新鞋走老路?
時代語境的制約似乎超出了社會所能為女性提供的物質(zhì)條件保障。作為生活在社會轉(zhuǎn)型期的新女性,她們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啟蒙,在情感和理智上追求人格獨立、婚戀自由。但同時,作為社會上剛剛覺醒的“少數(shù)人”,她們依然被周圍嚴(yán)苛的社會環(huán)境與濃厚的傳統(tǒng)文化氛圍所禁錮。大量工作崗位對女性的偏見和拒絕,也剝奪了她們實現(xiàn)經(jīng)濟(jì)獨立的可能性。由于這些現(xiàn)實條件的“硬約束”,她們追求真正解放的理想始終難以實現(xiàn)。甚至連魯迅的妻子許廣平作為新式知識女性,以她在社會的知名度和個人能力,在上海找份工作并實現(xiàn)經(jīng)濟(jì)相對獨立并非難事,也選擇了放棄,回歸到傳統(tǒng)家庭結(jié)構(gòu)中。在五四時期新女性追求解放的呼聲中誕生的那些“妻子”們,并沒有找到魯迅在《娜拉走后怎樣》中所提出“毀滅或是回來”[4]之外的第三條路,最終也難逃墮落或回來的命運。
五四新文化運動雖然對封建思想進(jìn)行了猛烈的沖擊,但其突破仍然不夠徹底,深植于人們意識深處的封建價值觀并不容易消除。涓生的利己主義本性與封建的價值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涓生仍有男主外、女主內(nèi)的思想。在與子君結(jié)婚后,涓生沒有繼續(xù)以進(jìn)步的新思想來支持子君的個人發(fā)展,相反,他的行為逐漸回歸到傳統(tǒng)儒家道德觀中男主外、女主內(nèi)的舊有模式。日本社會學(xué)者上野千鶴子在其著作《身為女性的選擇》中指出,將養(yǎng)育后代與照顧家庭的重?fù)?dān)完全落在妻子一個人肩上的父權(quán)制婚姻與生育模式是不正常的[5]。
子君被新文化先驅(qū)者視為婦女解放過程中面臨精神困境的典型人物,她的經(jīng)歷反映了同時代眾多女性的生存狀態(tài)。20世紀(jì)30年代出版的巴金的《家》以及老舍的《駱駝祥子》中,我們同樣能從書中的女性角色身上觀察到作為妻子所共有的部分特性。而到了20世紀(jì)中葉,《我們夫婦之間》中的妻子角色定位則發(fā)生了顯著的變化。近代以來,女性形象的建構(gòu)不僅關(guān)乎性別,還作為一種具有深刻意義的女性符碼,承載了豐富的文化意涵。在根據(jù)地時期的革命實踐中,傳統(tǒng)的性別分工模式被打破,女性通過提升經(jīng)濟(jì)地位的方式從家庭走向社會,重構(gòu)了性別關(guān)系并改變了中國傳統(tǒng)的家庭關(guān)系。正是由于張同志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與子君不同,才使她能夠成為具有鮮明個性和獨立性的妻子形象的典型。從革命視角來看,子君的出路不僅需要獲得一份工作,還需要一個保證性別平等的社會制度,即需要對社會關(guān)系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進(jìn)行根本性的改造。否則,即便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張同志這樣的女性也可能會遭遇與子君相似的命運。小說中,張同志展現(xiàn)出極強的性別平等意識,比如女性應(yīng)該有自己工作、識字的權(quán)利,以及在夫妻關(guān)系上的獨立見解。這些觀念的形成,與她曾經(jīng)的根據(jù)地經(jīng)歷密不可分。她從小是一個“童養(yǎng)媳”,后來參加革命、實現(xiàn)自由戀愛,婦女解放、婚姻自主的理念在她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xiàn)。小說還通過細(xì)膩的情感描寫,展現(xiàn)了張同志豐富的內(nèi)心世界。比如,在小娟被誤會后,她主動去道歉并流下眼淚等細(xì)節(jié),可見她不是一個只有一腔正義的概念化人物,而是一個具有深度、較為立體的健全人格。
需要說明的是,這樣的對比閱讀,并非旨在簡單重申“革命”一舉解決了“啟蒙”所未能解決的那些問題,從而確認(rèn)“革命”為女性帶來了解放感(毋寧說,“革命”時代的女性也有需要進(jìn)一步解決的問題),而是指出娜拉出走后的困境,以及子君作為妻子在看似新式家庭中遭遇的難題,并非僅憑“以思想文化解決問題”的思路就能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女性解放與社會關(guān)系改造兩者相結(jié)合的視野,唯有如此,女性的主體地位才能得以改變。另外,在“張同志的時代”和“子君時代”中女性所面臨的問題,并非完全失去其現(xiàn)實意義,它依然是我們審視當(dāng)下問題的一個重要參照。
在“張同志的時代”,婦女參與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勞動成為實現(xiàn)男女平等的重要途徑,隨后在全民所有制背景下,女職工人數(shù)日漸增長。同時,“勞動模范”“勞動英雄”成為社會贊揚和鼓勵的典范,社會要求女性既要有政治覺悟,又要有一技之長。1958年,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怎樣做一個好家屬》,號召廣大婦女要“走出家庭”,成為“國家的良母,民族的賢妻”[6],可見那一時期的女性依然處于以男性為主導(dǎo)的話語體系中。《我們夫婦之間》結(jié)尾處描寫了夫婦二人重歸于好的情節(jié),但這種“我重新認(rèn)識到了妻子的美善”的敘述,或許在本質(zhì)上反映了女性意識在面對男性凝視時的讓步與妥協(xié)。當(dāng)然,我們也應(yīng)看到,這一時期的社會變革和女性參與也為女性地位的提升和女性意識的覺醒提供了契機。
張同志可以代表那些從根據(jù)地走出、解放后進(jìn)城的革命工農(nóng)女性。她們雖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擁有豐富的革命歷練。《我們夫婦之間》被視為最早觸及“鄉(xiāng)下人進(jìn)城”敘事的小說作品之一,也是后期大量涌現(xiàn)的知識分子與鄉(xiāng)村女性婚姻結(jié)合的先鋒作品。進(jìn)城后,張同志因受到城市文化氛圍的影響而備感拘束,而丈夫李克則逐漸適應(yīng)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并表現(xiàn)出一些與之前不同的生活習(xí)慣和態(tài)度,這些差異導(dǎo)致了兩人之間的隔閡。在經(jīng)歷了內(nèi)心的掙扎后,張同志最終選擇回歸到小說開頭處所描繪的“賢妻良母”角色,她嘆了口氣,把頭靠在丈夫的胸前,“半仰著臉問道:‘這該怎么是好’”?[7]這樣的回歸,讓她重新扮演起了小鳥依人的溫順形象,也再次滿足了丈夫作為男性的凝視需求和知識分子的啟蒙欲望,于是李克的“心又突突地跳了”“被她那誠懇的深摯的態(tài)度感動了”[7]。此時,夫婦之間的生活看似又回到了“初戀時幸福的時光”,但實際上,這只是張同志重回傳統(tǒng)妻子的角色定位和父權(quán)制話語體系中[8]。
二、夫妻關(guān)系:從單向啟蒙到雙向改造
男性與女性分別居于“第一性”與“第二性”的地位是導(dǎo)致性別關(guān)系不平等的根源之一。男性更易占據(jù)知識優(yōu)勢,在福柯看來,知識與權(quán)力相伴相生,這也是過往歷史中男性占據(jù)“第一性”地位的重要原因。涓生作為文職人員及知識分子,擁有教育及社會地位上的優(yōu)越性。在與子君的交流中,他對易卜生、泰戈爾、雪萊以及男女平等的思想信手拈來,故而在這段關(guān)系中,他借助知識這一權(quán)力自然而然地處于高位,俯視著自己的伴侶子君,而子君則被誤解為無知者。也就是說,傳授與被傳授的關(guān)系隔斷了二人之間的相互交流,涓生借助知識進(jìn)一步深化了二人間的不平等關(guān)系。在整個故事中,子君處于失語的狀態(tài),因為這是涓生的手記,子君的態(tài)度和處境被忽略,她只能被涓生所敘述,而涓生的敘述對子君又形成了一種壓迫[9]。
一方面,對子君來說,師生情誼與愛情難以區(qū)分。五四時期,男性對女性的啟蒙往往帶有傳教的意味,少女們總是仰著頭,好奇地仰望著傳授學(xué)識與新思想的男性。而男性們除了教導(dǎo)之外,也會由此產(chǎn)生一種自豪感,認(rèn)為少女們充滿求知欲,他們便是這求知欲的引領(lǐng)者。在這一啟蒙過程中,一種隱蔽的不平等關(guān)系被重新確立起來。
另一方面,涓生將子君視作中國女性的輝煌曙色。子君堅定地說出:“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quán)利!”[3]這句話讓涓生感到欣喜,并認(rèn)為子君與他的靈魂契合:“知道中國女性,并不如厭世家所說那樣的無法可施,在不遠(yuǎn)的將來,便要看見輝煌的曙色的。”[3]作為五四新青年,涓生期望子君能成為革命的斗士、新生的力量,因而,子君這一句口號式的宣言深深打動了涓生,讓他以為這便是子君的全部心聲。
《我們夫婦之間》中的夫妻二人則具有更加平等的性別關(guān)系和社會地位。小說中的夫妻關(guān)系不再是常見的“男性是女性精神導(dǎo)師”的模式,反而男性變成了受教育者,女性則處于教育者的位置,引導(dǎo)男性走出小資產(chǎn)階級的價值觀陷阱。但李克并非單純被動受教育者的形象,而是與他所認(rèn)為的“落后”保持一定的距離,這使得他在作者筆下并不是一個令人厭惡的形象,而帶有某種滑稽甚至可愛的特點。此時,夫妻關(guān)系具有了平等這一新的屬性,這體現(xiàn)在兩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閑時,她教我紡線、織布;我給她批仿,在她寫的大楷上劃紅圈,或是教她打珠算,討論土地政策……”[7]可以說,張同志與李克已不再是啟蒙與被啟蒙的關(guān)系,而是各有專長,相互學(xué)習(xí)、共同進(jìn)步的關(guān)系。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時期形成的特殊的“革命夫婦”模式,其本質(zhì)上是女性對取得話語權(quán)的嘗試。在這種模式下,“革命”先于“夫婦”而存在,女性爭取婚姻家庭中的平等,既有其進(jìn)步合理的成分,也是當(dāng)時的歷史選擇和時代需求。
在子君生活的年代,女性的身份是由擁有話語主導(dǎo)權(quán)的男性建立的。女性因此喪失了自我表達(dá)的機會,其話語權(quán)實際上源于父權(quán)制文化中的男性凝視以及性別規(guī)范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女性失語不但是一種社會現(xiàn)實,也是基于男性權(quán)力擴(kuò)張和異化而產(chǎn)生的一種現(xiàn)象。女性要想獲得話語體系的主動權(quán),就需要自覺地將自我納入男性所認(rèn)同的思維模式,借用男性的口吻,以被規(guī)定的符號來表達(dá)自己的思想。這一過程中,她們必須經(jīng)歷男性話語原則的過濾與選擇。張同志與子君都有反抗包辦婚姻、追求自由戀愛的經(jīng)歷,但結(jié)局卻大相徑庭。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子君與涓生是單向的啟蒙關(guān)系,而張同志與李克則是雙向的改造關(guān)系。《我們夫婦之間》一開始就明確夫婦二人“真是知識分子和工農(nóng)結(jié)合的典型”,李克在張同志面前并沒有優(yōu)越感,他愛上張同志,是因為后者是勞動英雄,是當(dāng)時的“先進(jìn)人物”,李克反而要向她學(xué)習(xí)。但子君崇拜涓生,將愛情視為精神支柱和生活的全部,一旦愛情的樓閣倒塌,她就會失去依附,因巨大的落差感而喪失生活的信心。
隨著女性社會地位的日漸提高,女性開始在家庭之外主動表達(dá)自己的政治觀點和立場,從“被講述”的狀態(tài)逐漸走向“自述”,在伴侶的選擇上也更傾向于尋求價值觀的一致。這使得“知識分子與工農(nóng)相結(jié)合”的敘事中,“女性”與“革命”交織在一起,女性在選擇戀愛乃至婚姻對象時,也更加注重與對方在價值觀和政治傾向上的一致性。譬如《我們夫婦之間》結(jié)尾處,張同志表現(xiàn)出如同女兒般的依賴與順從,李克表現(xiàn)出如同父親兄長般的體貼與寬厚,類似情節(jié)在之后許多革命戀愛題材的小說中都能看到。似乎無論女性在心理狀態(tài)、生理條件上存在何種差異,她們在根源上都擁有一個相同身份的上位者——作為父親形象而存在的男性。這一男性形象通常也代表著政治主體話語,從而使得這種關(guān)系在一定程度上凌駕于夫妻關(guān)系、男女關(guān)系之上,并且相較于兩性關(guān)系更加持久穩(wěn)固。看似性別的對立性被消解,然而一旦“女兒”成長為女人,那么作為“父親”的男性就喪失了原有的優(yōu)越性和權(quán)威,這在某種意義上形成了對女性追求解放的隱性阻礙。
《我們夫婦之間》結(jié)尾處,張同志有妥協(xié),李克也有所反思。作者的主觀動機似乎是想表現(xiàn)二人各自改正缺點的過程,然而,這種站在懺悔立場的寫法也引發(fā)了批評。有觀點認(rèn)為,結(jié)尾將嚴(yán)肅的思想問題趣味化、輕松化,從敘事流程來看,大團(tuán)圓結(jié)局也顯得倉促和突然,缺乏內(nèi)在動因。張同志的“妥協(xié)”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受到了組織的批評,而這些批評話語與此前李克對她的指責(zé)有相似之處。也就是說,張同志在李克身上看到了他可能代表了正確的一面,這成為小說結(jié)尾處張同志對李克妥協(xié)并反思自己的重要原因。但張同志的主體性已經(jīng)確立起來,以后二人在一些問題上應(yīng)該還是會有分歧。誠然,中國婦女面臨的解放問題仍然充滿歷史和現(xiàn)實的雙重挑戰(zhàn),但要譜寫新的篇章不能只從個體身上尋找解決措施,張同志對于自我的認(rèn)知有所進(jìn)步,已經(jīng)站在了重塑女性性別意識的成長起點上。然而,要想實現(xiàn)全面性的改變還需要從社會根源出發(fā),使男女平等的宣言不再是空洞的口號,而真正讓女性“浮出歷史地表”,走向群體意識的覺醒和自我成長的道路。
三、敘事裂隙:敞亮與遮蔽
《傷逝》中,小說文本雖然全篇使用第一人稱敘事,但副標(biāo)題“涓生的手記”說明涓生是真正的敘述主體,透露出作者對于讀者在場的預(yù)設(shè)——作者特意站在第三人稱視角,為讀者注明這是“涓生的手記”,暗示這是悲劇制造者涓生寫的懺悔文字。這一設(shè)定形成了作者和涓生之間明顯的裂痕。全文呈現(xiàn)出雙重的敘事運動:一方面是顯性的敘事,以涓生個人的回憶為線索,表現(xiàn)其對子君的深情、強烈的懊悔和愧疚;另一方面則是隱性的敘事,作者藏在涓生背后,對其自我洗白的唾棄。涓生的回憶中常常或明或暗地流露出對子君的抱怨。例如,“她愛動物”,緊接著便是“也許是從官太太那里傳染的罷”,遣詞造句中充滿了貶損和埋怨。涓生的講述越真誠越自我暴露,也就越顯得反諷,從而使文本傳出兩種聲音。如婚后涓生抱怨子君:“管了家務(wù)便連談天的工夫也沒有,何況讀書和散步。”[3]下一句又說,“我們總還得雇個女傭”,看似是在指責(zé)子君后表達(dá)了自我安慰之意,但實際上包含了作者的敘事邏輯,即正是因為涓生沒能力掙錢請女傭,而生活中總要有人操勞,于是妻子主動承擔(dān)家務(wù)讓丈夫有時間繼續(xù)“風(fēng)花雪月”。由此可見,敘述的表層是涓生的話語,而深層則是隱含作者對涓生話語的反諷。涓生的手記被題為“傷逝”,與其說他“傷逝”的是子君的死,不如說他“傷逝”的是自己逝去的“愛”。
而《我們夫婦之間》的敘事對張同志的批評確實居多,尤其是前半部分,主要是從李克的視角展開。李克的自我反思出現(xiàn)在后半部分,但這個自我反思實際上是在李克部分看法正確的前提下進(jìn)行的,因此其力度不足以抵消前半部分對張同志的貶抑。李克一直是以一種輕薄、嘲弄的態(tài)度對待妻子的優(yōu)點,他利用妻子微小的錯誤來掩飾自己的重大錯誤。李克一直沒有意識到自己錯誤的嚴(yán)重性,甚至他對自己思想的揭露都顯得不夠深刻和徹底。他雖然經(jīng)常提到妻子的“樸素”“熱情”與“奉獻(xiàn)”精神,但又不斷地被妻子粗俗、莽撞的言行所顛覆。在兩人的爭執(zhí)中,讀者能感受到在敘事主體與“我”之間產(chǎn)生的裂痕,這主要體現(xiàn)在李克精神上的優(yōu)越感。尤其是結(jié)尾處看似表達(dá)李克自我批判的“和解”部分,實則是李克對妻子貌似表揚、實則批評教育的一種隱性“施壓”,妻子“聽得好像很入神,并不討厭,我說一句,她點一下頭”[7]。這表明張同志在與李克所代表的城市中產(chǎn)階級生活方式的碰撞中,原先秉持的理念逐漸經(jīng)歷了調(diào)整和融合,她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李克的觀點。小說中涉及的城市生活方式,在日常層面上并未被賦予更深層的意義,而是被工具化了。
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從作者的文本呈現(xiàn)和敘事方式上看出,盡管他在后期為李克辯解稱“并沒有當(dāng)作一個肯定的人物來寫”[10],但文本中第一人稱敘事方式的運用以及作者并沒有如同《傷逝》那樣刻意劃清明暗敘述界限,使得作者對李克的批評顯得模棱兩可。這也因此引發(fā)了批評家丁玲等人對蕭也牧是否具有與李克思想同構(gòu)性的質(zhì)疑[11]。顯然,這種批評在今天看來,或多或少都帶有那個時代的烙印。
總而言之,《傷逝》通過明暗敘述視角對男主人公涓生進(jìn)行了明褒實貶的反諷,是“將真實深深地藏在心里的創(chuàng)傷中”[3],而《我們夫婦之間》的敘事則呈現(xiàn)出一種裂隙,這種裂隙表現(xiàn)了作者在主流話語體系之外試圖自我表達(dá)的一面。
四、結(jié)語
女性話語權(quán)問題的探討日益受到重視,在這個層面上,從女性主義角度對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語境中的人物形象進(jìn)行研究,便有了理論與實踐價值。劉思謙在其著作《性別:女性文學(xué)研究的關(guān)鍵詞》中提出,“性別”是女性文學(xué)研究的理論支點。有了性別理論的內(nèi)在支持,女性文學(xué)研究“將會發(fā)現(xiàn)文學(xué)作品中一些以往習(xí)焉不察而不見的被遮蔽的問題和意義”[12]。本文選取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上兩篇具有典型意義的作品進(jìn)行對比,旨在從女性文學(xué)視角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進(jìn)行解構(gòu)剖析,為當(dāng)代女性文學(xué)研究回歸特定歷史文化坐標(biāo)提供有益的挖掘和探索,力求在研究的視域和角度上有所拓寬與突破,并以此向經(jīng)典作家和作品致敬。
參考文獻(xiàn)
[1] 波伏瓦.第二性[M].鄭克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2] 伯格.觀看之道[M].戴行鉞,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7.
[3] 魯迅.傷逝[M]//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
[4] 魯迅.娜拉走后怎樣[M]//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
[5] 上野千鶴子.身為女性的選擇[M].呂靈芝,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23.
[6]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婦女聯(lián)合會宣傳教育部,武漢市婦女聯(lián)合會宣傳部.怎樣做一個好家屬[M].北京:工人出版社,1958.
[7] 蕭也牧.我們夫婦之間[J].人民文學(xué),1951(1).
[8] 陳雨辰.話語權(quán)力爭奪之中女性意識的再覺醒與妥協(xié)——以《我們夫婦之間》為例[J].名作欣賞,2023(20).
[9] 劉高峰.《傷逝》:男權(quán)意識與男性話語[J].焦作師范高等專科學(xué)校學(xué)報,2005(3).
[10] 蕭也牧.我一定要切實地改正錯誤[J].文藝報,1951(1).
[11] 丁玲.作為一種傾向來看——給蕭也牧同志的一封信[J].文藝報,1951(8).
[12] 劉思謙.性別:女性文學(xué)研究的關(guān)鍵詞[J].洛陽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2005(6).
(責(zé)任編輯" 余"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