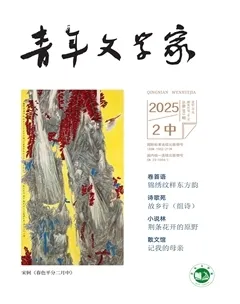列斐伏爾空間理論視角下張岱《西湖夢尋》的空間美學(xué)建構(gò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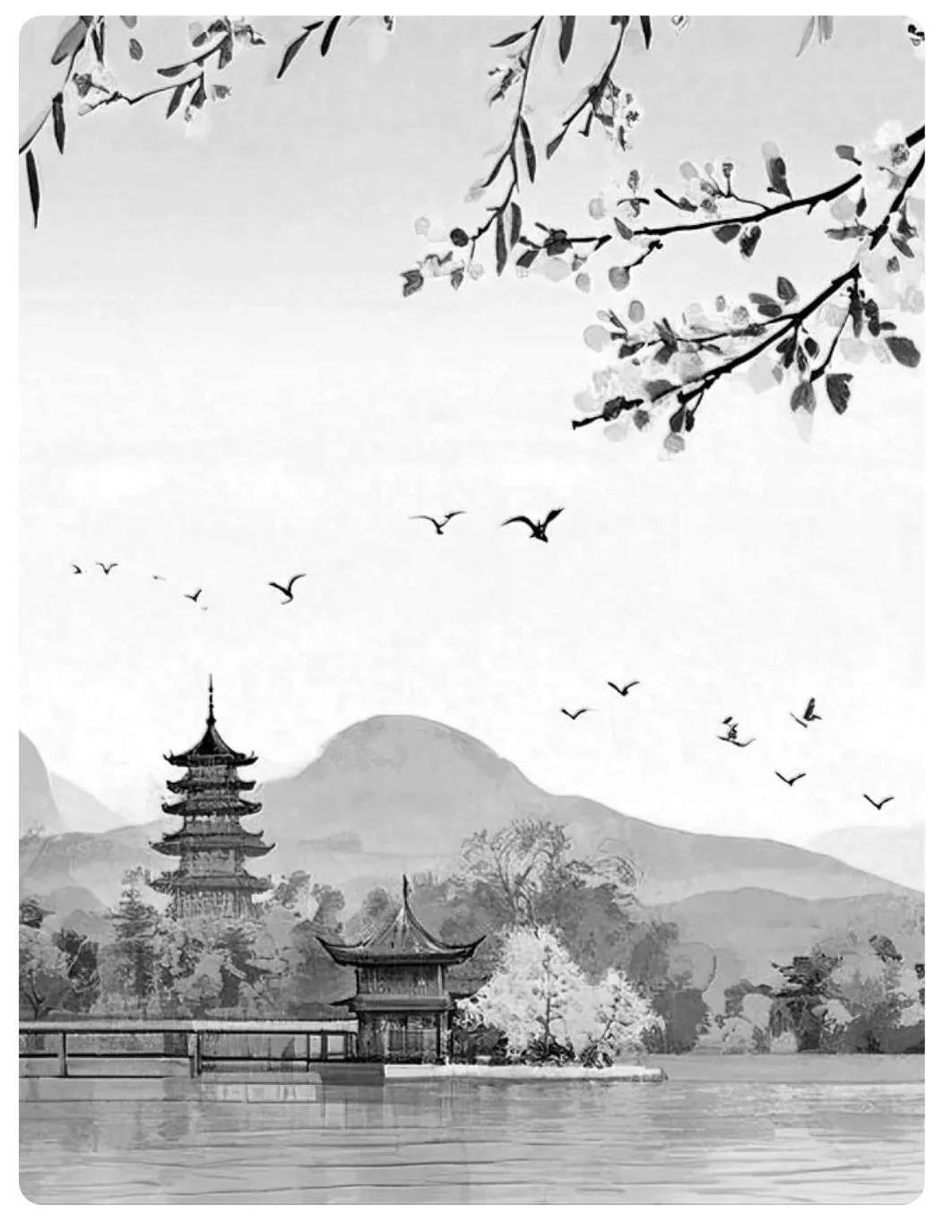
張岱(1597—1689),名維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天孫,號陶庵、蝶庵、古劍老人,晚號六休居士,出生于山陰(今浙江紹興),祖籍四川綿竹,常自稱“蜀人”。張岱出生在一個書香門第,自幼家境優(yōu)越,聰明好學(xué),深得祖父張汝霖、父親張耀芳的喜愛,被舅父譽為“今之江淹”。張岱作品頗多,著有《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瑯?gòu)治募贰兑购酱贰犊靾@道古》《石匱書》《續(xù)石匱書》《一卷冰雪文》《三不朽圖贊》等。張岱以小品文見長,其中《西湖夢尋》和《陶庵夢憶》,合稱“二夢”。《西湖夢尋》將西湖空間以“路-點”的分層方法,分為五路七十二則,以西湖為中心,對重要的山水景色、佛教寺院、先賢祭祠等進行了全方位的描述。《西湖夢尋》所展現(xiàn)的西湖空間具有相當(dāng)?shù)拿缹W(xué)價值。
空間和時間一樣,都是文學(xué)中的重要研究對象,但時間歷來為學(xué)者們所看重,而空間直到西方學(xué)界的“空間轉(zhuǎn)向”才可以說得到了真正的重視。20世紀中葉發(fā)表的《現(xiàn)代小說的空間形式》拉開了帷幕,而戰(zhàn)后西方社會的轉(zhuǎn)變也讓空間得到了更多的聚焦與關(guān)注。其中,福柯、列斐伏爾、愛德華·蘇賈等人都對空間理論做出了詳細的闡釋和解讀,可以說構(gòu)成了空間轉(zhuǎn)向的主力軍。
1974年,列斐伏爾出版的《空間的生產(chǎn)》,指向資本主義空間的矛盾沖突和問題。它批判空間生產(chǎn)的玄學(xué)論和機械論,批判被分割化的知識體系,認為需要從綜合和辯證的角度看待和認識存在的問題。列斐伏爾在書中的核心觀點是:“(社會的)空間是(社會的)產(chǎn)物。”列斐伏爾為解決資本主義空間的矛盾沖突和問題,建構(gòu)了社會空間生產(chǎn)的三元辯證法。列斐伏爾的社會空間三要素是三組概念叢群,而不僅僅是三個名詞或三個單一要素。列斐伏爾明確提出兩組分別由三要素構(gòu)成的對應(yīng)性名詞來闡述社會空間構(gòu)成。第一組是空間實踐、空間表征和表征性空間。
本文從這三重空間來闡釋《西湖夢尋》中的西湖空間,探尋張岱是如何在《西湖夢尋》中構(gòu)建西湖空間美學(xué)的。
一、空間實踐
“空間實踐”是通過對社會空間的占有和取用,改變和生產(chǎn)新的社會空間。列斐伏爾通常舉例為道路和交通網(wǎng)絡(luò)。這兩者是空間實踐的主要內(nèi)容。然而,空間實踐不只是指向社會實踐的產(chǎn)物,還表現(xiàn)為日常生活與城市現(xiàn)實之間所形成的空間緊密聯(lián)系與高度分隔及其空間感知。
《西湖夢尋》這個整體就是張岱筆下所產(chǎn)生的西湖的空間,西湖既是一個自然空間,也是一個社會空間。西湖作為社會空間的形成,是人的物質(zhì)生產(chǎn)活動的結(jié)果。它先是地理意義上的湖泊,以最具代表性的“潟湖”說而言。竺可楨在《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中指出,“西湖也不過是錢塘江左邊的一個小小灣兒。后來錢塘江沉淀,慢慢地把灣口塞住,變成一個潟湖”。然后,它逐漸為杭州居民所開發(fā)利用,為歷任杭州長官所修建,比如白居易在長慶年間任杭州刺史,疏浚六井、筑湖堤;蘇東坡在熙寧四年(1071)于杭州任職,其間治理河道、筑就蘇堤;明弘治年間,杭州太守楊孟瑛花費五年時間說動朝廷重修西湖。西湖經(jīng)歷了漫長的修建治理歷史,才最終形成了今日所能見到的西湖。在西湖本湖之外,居民和官員們還圍繞西湖周邊,不斷延伸西湖空間,制造出了新的非西湖地理職能的其他空間,比如寺廟、庭院、官署等。這些其他空間與居民們的日常生活緊密聯(lián)系,同時又相互分隔,分別位于西湖地理空間的不同方位。張岱在展開景物時也會提到它們之間的聯(lián)系,比如《冷泉亭》中的“冷泉亭在靈隱寺山門之左”,《北高峰》中的“北高峰在靈隱寺后”,《韜光庵》中的“韜光庵在靈隱寺右之半山”。
二、空間表征
“空間表征”指的是被概念化的空間,是專家和官僚們的空間,是他們腦海中的那種知識性的、概念性的空間,是能夠代替日常的現(xiàn)實空間的一種符碼系統(tǒng)。空間表征與生產(chǎn)關(guān)系及其構(gòu)造的、維護的社會秩序有關(guān),空間表征利用空間實踐將其意圖“投射”在社會空間之中。列斐伏爾把這些權(quán)力的、規(guī)劃的、知識性的空間看作能夠建構(gòu)和維系資本主義秩序的重要對象。
在《西湖夢尋》中,張岱把西湖分為五路,每路依次展開景物。有的景物看似是天然的,如《飛來峰》的奇石,但這些奇石們也深受權(quán)力的塑形,元代僧人楊髡將這些奇石“遍體俱鑿佛像,羅漢世尊,櫛比皆是,如西子以花艷之膚,瑩白之體,刺作臺池鳥獸,乃以黔墨涂之也。奇格天成,妄遭錐鑿,思之骨痛”。飛來峰奇石受楊髡“毒手”,奇石們本為自然,但在歷經(jīng)改造后,具有了社會的和概念性的意義,是楊髡所代表的權(quán)力將它們塑形為“他者”,成為一種無聲的宣揚,也成為楊髡所建構(gòu)的秩序的組成部分。此時,奇石這一空間就成了知識性、概念性的空間。再到田汝成、張岱錐碎被鑿奇石,“寺僧以余為椎佛也,咄咄怪事,及知為楊髡,皆歡喜贊嘆”。在《飛來峰》和《岣嶁山房》中,都出現(xiàn)了“山靈”,“山靈”可以說是張岱文化信念里的重要一部分,即對西湖自然山水、景物的“靈化”,奇石的被椎,增加了這一空間的社會的意味,即要求對自然空間的復(fù)歸、受權(quán)力胡亂改造的空間終將消失。奇石的“自然-被鑿-被椎”過程,也象征了文化信念的復(fù)歸,畢竟張岱的命運正如奇石,經(jīng)歷“富貴-易代-貧苦”。明清易代之際,不僅有生靈涂炭的社會現(xiàn)實,更有潛移默化之中文化信念的更迭。飛來峰奇石這一空間,在張岱的筆下,也具有了更多的文化意味。
三、表征性空間
列斐伏爾所提出的“表征性空間”,與空間表征相比,稱得上是隱藏的,或者說是晦暗的。它是私人性的、想象的、經(jīng)驗性的空間,是用戶體驗的空間,或者用福柯的說法,是微觀空間。總之,它是空間的使用者和居民的空間體驗和想象。這個空間里既有非符碼化的感受,也有符碼體系。表征性空間更多地指向個體的特殊性。
《西湖夢尋》就可以稱為是張岱的表征性空間。在表達個體感受之外,里面歷數(shù)的每個西湖景點中又暗含了數(shù)個他人的表征性空間,它們互相輝映,使得這一景點的空間成為由張岱主導(dǎo)而多人共同建構(gòu)的獨特空間,代表了他們的獨特體驗和想象。《十錦塘》一篇中,張岱在本文中寫孫堤風(fēng)景與司禮太監(jiān)孫隆修筑裝塑西湖之功。而文后所附的詩文小記中,袁宏道《斷橋望湖亭小記》則言朝日始出、夕舂未下的西湖之妙與太監(jiān)孫隆之事,只是相較于張岱所明寫的“不得一見湖光山色”“大為鯁悶”,袁宏道則是感慨“腐儒,幾敗乃公事!”將矛頭對準了官僚對于孫太監(jiān)功勞的忽視。張京元的《斷橋小記》則寫西湖游客眾多,將目光投注到了“與東風(fēng)相倚,游者何曾一著眸子也”。譚元春的《湖霜草序》則寫舟居之五善以及以五善于西湖中的閑適人生。袁宏道、張京元、譚元春等人與張岱時代相仿,但他們不同的遭遇和個體經(jīng)驗會對同一空間產(chǎn)生不同的表征性建構(gòu),導(dǎo)致空間在風(fēng)景、掌故之外,更有一層獨特的個體體驗。
張岱在《陶庵夢憶·自序》里講了兩個關(guān)于夢的小故事:“昔有西陵腳夫為人擔(dān)酒,失足破其甕,念無以償,癡坐佇想曰:‘得是夢便好。’一寒士鄉(xiāng)試中式,方赴鹿鳴宴,恍然猶意非真,自嚙其臂曰:‘莫是夢否?’一夢耳,惟恐其非夢,又惟恐其是夢,其為癡人則一也。”一個人認為“是夢的話就好了”,另一個人認為“難道是夢嗎?”(意思是唯恐眼前的是夢)。如同張岱看到自己動蕩波折的人生一般,以“大夢”作為自己人生的定義,而對于回首種種過往,他將其稱為“大夢將寤”“又是一番夢囈”。這樣的“夢囈”貫穿了“二夢”,因此《西湖夢尋》的關(guān)鍵詞是“夢”,西湖作為《西湖夢尋》的展開空間,無疑寄托了張岱的深厚的情感,“夢”是張岱根據(jù)自身遺憾所抒發(fā)、記錄的夢境,西湖正是張岱“夢”的載體。他從記憶中的西湖山水出發(fā),以西湖為基底,聯(lián)系自身與社會所發(fā)生的“天崩地裂”,著成一“夢”。而他的“夢”所尋找、所體現(xiàn)的,是黍離之悲,是江南文人的文化信念。
(一)黍離之悲
張岱所寫的西湖,所“夢”的西湖,在地理空間之外還為時間所支配,這一特殊的時間節(jié)點就是明末清初之際。這個時間節(jié)點不僅影響了西湖空間,而且還極大地改變了張岱的個體命運。
明朝士大夫被迫發(fā)生了身份的轉(zhuǎn)換,成了明遺民。明亡于崇禎十七年(1644),同年即順治元年,是清代的開始。而“清初”這一時間節(jié)點,應(yīng)該止于何年,卻沒有一個嚴格統(tǒng)一的界定。這里采用的界定是從順治元年(1644)到康熙四十年(1701)前后,約六十年時間。“明遺民”這一概念,也需要一定的厘定。首先,必須是生于明朝而明亡后不仕于清朝的士人。其次,以其自我認定和當(dāng)時人們對其認可程度作為判斷的標準。其三,對人生歷程比較曲折的士人的判斷不能“一刀切”。其四,應(yīng)當(dāng)把因拒不與清廷合作,不愿意放棄故國之思而流亡海外的明朝士人,視為“明遺民”。從這些界定標準來看,生于明萬歷年間、明亡后拒不出仕清廷,隱居避亂、潛心著述的張岱可算入明遺民行列。
明朝滅亡,張岱一邊要面對兵亂,一邊失去了曾經(jīng)的富裕生活,要自己耕作才能養(yǎng)活一家數(shù)口。他于剡中避兵災(zāi),又移居快園。在生活窘迫的情況下,“布衣蔬食,常至斷炊”(張岱《自為墓志銘》)的張岱依舊堅守著明遺民的身份,并且在《西湖夢尋》中凸顯了他的氣節(jié),他不喜“凡炎涼勢利者”,而贊賞“高尚其志”,對大義凜然者“一往情深”,如《岳王墳》《伍公祠》《施公廟》。他題寫《岳王墳》詩云:“泥塑吾侯鐵鑄檜,只令千載罵奸雄。”《哇哇宕》中寫烈士祠中諸人皆宋時死金人難者,未嘗不是寫當(dāng)時明末死清難者。
(二)江南文人的文化信念
江南的名士文化底蘊深厚,隨著江南經(jīng)濟文化的發(fā)展,名士文化也由清賞演變?yōu)閷ξ镔|(zhì)的極度追求。講求精致,崇尚奢靡成為明后期江南一帶名士文化最突出的特征。張岱早年深受這種文化的熏染,至晚年回憶中仍不能忘懷。《包衙莊》《青蓮山房》分別記載了張岱祖父的朋友包涵所的風(fēng)雅逸事。這位包副使打造了西湖樓船,蓄養(yǎng)聲伎、歌童,北園修建八卦房,八床面面皆出,可見打造心思的精巧。“金谷、郿塢,著一毫寒儉不得,索性繁華到底。”包氏可以說是《西湖夢尋》中名士雅好的一個經(jīng)典。張岱以兩篇寫包氏之繁華,以包氏之風(fēng)雅趣事為樂,難忘之際,包氏也是張岱自我的一面鏡像。張岱《自為墓志銘》道:“少為紈绔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他與包涵所同樣深受晚明精致風(fēng)雅的風(fēng)向,雅好日常生活之物,講求奢華。張岱在山陰望族的家族熏陶與紈绔子弟的歲月中培養(yǎng)出了江南文人的文化信念。張岱在《祁止祥癖》中品評自己的好友祁止祥:“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據(jù)張岱記載,祁止祥“有蹴鞠癖,有鼓鈸癖,有鬼戲癖,有梨園癖”。在《西湖夢尋》中,張岱的“癖”體現(xiàn)在很多地方,比如《十錦塘》后附的《西湖七月半》中寫到他在杭人趕會散去后,“吾輩縱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氣撲人,清夢甚愜”。《明圣二湖》中張岱引“董遇三馀”,闡明特殊的游湖的時間能夠欣賞到不同的西湖景象。
張岱的好友王雨謙在《西湖夢尋》的序中說道:“張?zhí)这直P礴西湖四十余年,水尾山頭無處不到;湖中典故,真有世居西湖之人所不能識者,而陶庵識之獨詳;湖中景物,真有日在西湖而不能道者,而陶庵道之獨悉。今乃山川改革,陵谷變遷,無怪其驚惶駭怖,乃思夢中尋往也。”可以說《西湖夢尋》所夢所尋的,是張岱一生所凝結(jié)的文化趣味,而這些“癖”與“獨詳”“獨知”寄托在了西湖這一空間中,逢著明清之際的時代節(jié)點,蛻變?yōu)榻衔娜藢τ谕砻魑幕囊环N堅定信念,即“夢所故有”和“其夢也真”。
張岱在《西湖夢尋》的自序中坦言:“惟吾舊夢是保,一派西湖景色,猶端然未動也。兒曹詰問,偶為言之,總是夢中說夢,非魘即囈也。因作《夢尋》七十二則,留之后世,以作西湖之影。”《西湖夢尋》是張岱關(guān)于明清之際西湖景象的溫情留念。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西湖的景觀已經(jīng)逐漸消失在人們的記憶當(dāng)中,如《九溪十八澗》寫道:“老于西湖者,各各勝地尋討無遺,問及九溪十八澗,皆茫然不能置對。”他要將西湖歷史長留于世,將西湖文脈傳承下去。在《石匱書》中,張岱認為,以死殉國固然保存了氣節(jié),但既保全名節(jié)又存活于世,才是更大的忠勇。因此,他愿飽嘗世間之艱辛困苦,立志為西湖著書,為故國著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