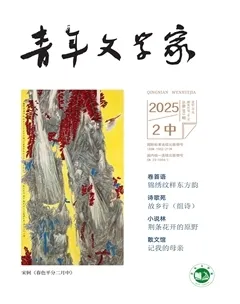《額爾古納河右岸》中兩性聲音共振的研究

朱麗葉·米切爾認為“小說的精髓就是兼具男性和女性的聲音”(湯擁華《文學批評入門》)。“女性聲音與男性聲音共振的出現是女性書寫真正成熟的標志。”(陳曦《〈額爾古納河右岸〉的性別敘事研究》)遲子建的兩性觀帶有鮮明的“雙性和諧”傾向,她的作品《額爾古納河右岸》描繪了中國北方鄂溫克部落的生存與發展歷程,書中一個個動人的愛情故事詮釋著作者對兩性關系的理解,其中女性聲音與男性聲音的交織,形成了一種美妙的復調,共同譜寫出一曲動人的樂章,呈現了一幅美好的人類社會畫卷,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性別關系和社會角色的嶄新視角。
一、女性聲音的多面呈現
(一)自我之聲—女性的主體意識與溫暖柔情的展現
“聲音是存在最好的證明,對于那些處于被迫長期保持無聲的非主流群體或邊緣化個人來說,能夠發聲彌足珍貴,聲音便是身份和權利。”(陳曦《〈額爾古納河右岸〉的性別敘事研究》)小說的敘述者“我”是鄂溫克民族最后一個酋長的女人,“我”的聲音是結構上優越的聲音,高于其他人物的聲音。通過“我”的第一人稱視角,讀者見證了鄂溫克民族近百年的歷史畫卷,同時也感受到了現代文明入侵帶來的沖擊。在面臨人生抉擇時,“我”始終堅定地用自己的聲音表達內心世界,為追求真實與自由而努力,這充分體現了女性注重自我主體性的意識。“我”作為敘述者,不僅僅是在講述故事,更是在傳遞一種女性的力量,一種敢于追求自我、珍視自我的力量。這種力量在鄂溫克族的歷史長河中,雖然可能只是微弱的存在,卻如星星之火,在一定程度上挑戰了傳統父權文化對女性的壓制。
此外,“我”的敘述中常常包含著女性特有的溫暖與柔情,“我”善于用比喻、擬人等修辭手法,將生活中瑣碎的事物描繪得栩栩如生。例如,“我”用“朝我們跑來的白色馴鹿”來比喻半輪淡白的月亮,用“香味舔著我們的臉頰”來賦予香氣舌頭的感知能力,詩意化的表達不僅展示了女性對美的敏銳感知,也體現了女性內心的柔軟與溫情。
(二)順從之聲—女性對傳統文化與角色價值的認同
在我國傳統社會中,對女性角色的定義和期望深受父權文化的影響。女性被認為應當具備一系列特定的品質,以便履行她們在家庭和社會中的角色,如溫順、聽話和照顧家庭等。在這樣的文化傳統中,女性的價值取決于她們是否能遵守這些規范。所謂的“在家從父,出門從夫”成了衡量女性言行舉止的準則。這意味著,女性應當無條件地支持和服從男性,無論是父親還是丈夫。而當丈夫不幸離世,女性更是被強烈要求從一而終,終身守節,以彰顯她們的忠誠和貞潔。鄂溫克族女性群體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到了這種傳統父系文化的影響,她們的發聲雖然隱晦,卻透露出對這種文化的維護和對傳統女性價值觀的認同,在生活中不自覺地遵守著這些傳統規范,她們的價值和角色也被嚴格限定。
林克去世后,尼都薩滿和達瑪拉互生情愫。可是這種情感卻是氏族不允許的,依芙琳指出,按氏族習俗,弟弟去世,哥哥不能娶弟媳;哥哥去世,弟弟可娶兄嫂。依芙琳自從知道尼都薩滿和達瑪拉的感情后,常常在大家坐在一起商議事情的時候故意地提到林克,試圖澆熄他們的愛情之火。而“我”也始終對尼都薩滿滿懷警惕,甚至對母親達瑪拉也冷嘲熱諷:“云和水在一起是對的,哪有火和水在一起的?”部族人對他們情感的敵意,加之父系文化對女性的禁錮,讓這段感情注定無果,也讓他們因痛苦而癲狂。在鄂溫克族的社會結構中,這種順從之聲體現了女性在傳統族權文化面前的無奈與妥協。她們在遵守傳統規范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氏族的穩定和秩序。然而,這種穩定和秩序是以犧牲女性的自由和幸福為代價的。
(三)反叛之聲—女性的挑戰傳統與勇敢抗爭的吶喊
在傳統的兩性模式中,男性通常被視為主導者,負責家庭的外部事務,如采集狩獵等,而女性則被視為依賴者,承擔起內部的織布縫紉等家務。鄂溫克族遵循這種模式,男女相互扶持,共同應對生活的挑戰,從而使婚姻和睦,家庭幸福。而總有顛覆傳統形象的反叛者,在艱難生活中發出勇毅的吶喊之聲。
歪鼻子的依芙琳則恰恰是這一模式的反叛者,在婚姻生活里,她對坤得那萎靡不振的精神狀態極為不滿,常常指責坤得毫無可取之處。作為懲罰手段,她采取了拒絕與坤得同房的方式,并且在盛怒之下宣稱,自己絕對不會與傾慕自己的人同榻而眠。而當部落中的男性被日本人強行帶往東大營接受訓練,部落里僅剩下女性成員時,依芙琳展現了她的堅強、勇敢和反抗。當女人們為沒有新鮮的獸肉吃而抱怨時,她毅然帶槍下山出獵,決心自己解決問題。盡管連續去了三個夜晚,仍未有所收獲,但她并未氣餒,反而更加堅定了信念,頂風行動,做足準備,最終成功獵到一頭小鹿,解決了食物難題。此外,當她發現居住地已經沒有馴鹿可食的苔蘚和蘑菇時,她毫不猶豫地成為拿主意的領頭人,她說“我們必須離開這里”,于是她帶領大家沿著貝爾茨河向西南遷移,以尋找新的食物來源。更為令人敬佩的是,當白災降臨,馴鹿失蹤時,她依然是第一個站出來尋找馴鹿的人。在小說中,“她不再是男性的附屬品,她用反抗日本人、帶著女人遷徙、打獵等具體實際行動承擔起氏族社會中男性的部分責任,反抗著男性的話語、秩序與霸權”(任毅《鄂溫克民族文學〈額爾古納河右岸〉中的女性形象》)。
依芙琳雖在婚姻家庭中被視為“惡女”,但她的反叛與不屈側面展示了女性的力量和勇氣,她打破了傳統的性別角色定位,用實際行動證明,女性不僅能夠承擔起傳統的女性角色,也能夠勝任男性角色,為家庭和社會作出重要貢獻。她的形象挑戰了傳統的性別觀念,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性別關系和社會角色的嶄新視角,發掘了作品中女性力量的當代價值。
二、男性聲音的核心表達
(一)欲望之聲—男性對生育繁衍的崇拜
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中,作者巧妙地引入了部落男性與女性群體在發言權方面的對等格局,讓男性群體得以坦陳其真實的內心所想與見解。在這部作品中,男性群體的聲音主要聚集于生育繁衍這一關鍵主題之上,這種聲音成了女性聲音的重要補充,豐富了小說聲音的層次,揭示了他們內心深處對繁衍生息的渴望,也映射出他們對自然文明和古老傳統的敬重與推崇,令整個敘事更富感染力與吸引力。
“父親看我和列娜像兩只蝴蝶離不開花朵一樣繞著母親飛,就嫉妒地說,達瑪拉,你一定得送給我個烏特!”達西只要一說話,就與瑪利亞的肚子有關,“我的奧木列在哪里?”這些都透露出他們對新生命的深切渴望。新家庭成員的降臨,不僅延續了血脈,還帶來了尊嚴的重生,為生活注入了無盡的活力與希望。拉吉達在找尋馴鹿前,還惦記著讓家中再添新丁;坤得在依芙琳二次懷孕時,全心全意照顧她,期盼丟失的孩子能以某種形式回歸;魯尼面對不愿再孕的妻子,時常當眾落淚,他以淚水表達渴望,最終讓妻子轉變態度,這份對新生命的期盼最終打動了妮浩,而新生命誕生的希望與喜悅拯救了絕望恐懼的妮浩。
在生死交替、輪回不息的漫長進程中,鄂溫克民族頑強地存續著。面對民族危機,鄂溫克人將對生育的尊崇、對生命本體的敬重,奉為最終依歸。作家借助男性集體的聲音,揭示出那蘊含神性光輝的生育崇拜,不只是民族文化在性別層面的展現,更是整個民族堅定不移的信仰基石。盡管現代文明的浪潮洶涌襲來,使鄂溫克族顯得脆弱而渺小,但鄂溫克族所展現的民族精神中,卻包含著如磐石般的堅韌與永恒不朽的特質,這些特質將永遠閃耀,永不磨滅。
(二)失落之聲—男性對傳統文明淪落的傷感
傳統文明秩序無疑是男性本位的,與此相關,當這一秩序受到現代化進程的猛烈沖擊時,作為在民族文化內部長期處于“本位”地位的男性所感受的文化焦慮日益加重。被閹割的男性人物形象則是一種文化隱喻,反映了作家對現代文明的思考與批判。
文明的本質其實就是壓抑,文明的不斷發展就是對人的本性的不斷壓抑過程。這些抑制在文學中體現為對“男性去勢”現象的描寫。拉吉米在尋找“我們”的時候,途經一片松樹林,盤旋的蘇軍飛機投下了兩顆炸彈,劇烈的爆炸聲引發馬兒狂奔,在這一過程中他的陰囊被撕裂。作為現代文明縮影的熱兵器戰爭導致了拉吉米的悲劇。坤得從精神上被閹割,自從自己來到烏力楞,依芙琳沒有接受過他一次求歡,她的拒絕使坤得的欲望長期處于禁錮狀態,坤得也確實在日復一日的折磨中逐漸失去男性話語權和行為自主權。正是由于女性自由意志越發強烈,才導致男性精神逐漸消亡。
《額爾古納河右岸》中男性的去勢可以看作現代文明對傳統文明的吞噬與對人性的異化,傳統文明秩序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然而,在現代化進程的猛烈沖擊下,這一傳統秩序發生了劇變。面對新的社會環境,男性無法按照傳統方式尋求出路,他們在掙扎中尋找適應現代文明的方法,卻依然無法適應變革,成為現代文明的附庸。他們被迫放棄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融入現代社會中。然而,這種融入并非真正的心靈契合,而是一種無奈的妥協,他們最終為了維護尊嚴便選擇了緘默與退席。
三、兩性聲音的共振呈現
遲子建的兩性觀帶有鮮明的“雙性和諧”傾向,她認為上帝造人時只有男女兩個性別,意味著二者必須相互扶持才能維系世界的正常運轉。男人與女人的關系就像太陽和月亮,緊密聯系,不可分割,任何一方處于絕對主導都是不合理的。這也體現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中,男性聲音和女性聲音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像音樂中的復調一樣同時出現、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的,男性和女性也始終維持著一種和諧平等、彼此尊重的關系。
(一)平等與愛的相互依存
小說敘述者“我”代表了那些渴望并享受平等男女兩性關系的群體。“我”以真摯的情感和兩任丈夫建立起了相敬如賓、相濡以沫的關系。拉吉達愛開玩笑,夏天捉瓢蟲塞進“我”的褲腰里,冬天下雪時悄悄攥上一把雪塞到“我”的脖子里,以此要挾“我”說一大堆肉麻話;瓦羅加自己是一名酋長,卻為了和“我”在一起,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部落一分為二,帶著十幾人和“我”的部族合并。當“我”依偎在拉吉達的懷抱時,“我”覺得自己如同在山谷間自由穿行的風,無拘無束,暢快淋漓;而在瓦羅加的懷抱里,“我”則覺得自己宛如一條在春水中盡情暢游的魚,舒適自在,悠然自得。敘述者以這種方式展示了男女兩性在原始生命中自然流淌的美好。“如果說拉吉達是一棵挺拔的大樹的話,瓦羅加就是大樹上溫暖的鳥巢。他們都是我的愛。”這句話寓意著他們在彼此的生命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相互依賴、相互尊重、相互滋養、相互陪伴。
文章通過敘述者“我”的親身經歷,向我們傳遞了一個深刻的道理:在男女兩性關系中,平等與愛是相互依存的,只有彼此尊重、相互滋養,才能共同構建和諧美好的家庭生活。這種觀念在鄂溫克民族中傳承,成為他們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忠誠與包容的彼此融合
在遲子建的筆下,兩性關系并非全然被圓滿的光環籠罩,其間亦不乏悲情與灰暗的色調交織。然而,和諧且健康的兩性關系仿若強勁的主旋律,縱有偶爾彈錯的音符,卻依然能漾出幾分曼妙的余韻。見過了達瑪拉與尼都薩滿的愛而不得,馬糞包與妻子的相互背棄,瓦霞與安道爾的分釵斷帶等眾多悲情的愛情故事,達西和杰芙琳娜的愛情故事充滿了濃墨重彩,表現了同生同死的兩性之愛,猶如一顆璀璨的明珠,閃耀著忠誠、包容與堅韌的光芒。
杰芙琳娜失去丈夫金得意欲尋死時,達西主動求婚,用自己的真誠與堅定,試圖喚醒杰芙琳娜對生活的希望。瘦弱的達西在那個時刻看上去就是一個威武的勇士,她不愿意看到杰芙琳娜的淚水,不忍心看她剛剛新婚就馬上成了寡婦,于是寧愿等她守寡三年,寧愿被母親責罵也要主動承擔起照顧她的責任。這種無私的愛,讓杰芙琳娜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溫暖。然而,命運的捉弄讓他們的生活充滿了曲折。達西在杰芙琳娜最絕望的時候伸出援手,不離不棄,用自己的行動詮釋了忠誠的含義。而杰芙琳娜在達西遭遇困境后,沒有選擇離開,而是以殉情的方式表達了她對達西的忠貞不渝。這種生死相隨的愛情,超越了世俗的考量,體現了鄂溫克族對愛情純粹性的追求。達西明知杰芙琳娜曾經歷過巨大的痛苦,可能會有情緒上的波動和行為上的異常,但他依然選擇包容她、理解她,給予她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去愈合傷口。杰芙琳娜也同樣包容了達西為日軍效力這一復雜的歷史背景下的無奈之舉,沒有因為外界的壓力和指責而放棄對達西的愛。這種包容體現了鄂溫克族在面對生活困境和人性弱點時的豁達與寬容,他們相信愛情的力量可以超越一切困難和瑕疵。
本文通過對《額爾古納河右岸》中男性聲音、女性聲音及兩性聲音共振的分析,加深了讀者對鄂溫克族中兩性相敬相守的理解與認同。在作品中,遲子建積極構建男女兩性和諧共處的美好畫面,她用鄂溫克族男女樸素的愛戀治愈了現代社會中兩性關系失衡所帶來的愛情困擾。這種和諧的關系不僅僅是作品中的一種理想描繪,更是她對現實生活中兩性關系的一種期待和呼喚。作品為現代社會提供了寶貴的啟示,能夠引發人們對兩性關系的深入思考,促進現代社會兩性關系的和諧發展,讓每個人都能在平等、尊重、忠誠和包容的兩性關系中找到真正的幸福感和歸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