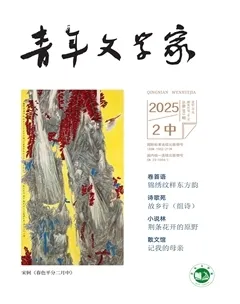步履如刃,心光不滅
我站在皇帝寢宮外,手中緊緊攥著竹制的笏板,汗珠沿著額角滑落,涼風拂面,寒意從脊背直透心底。我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戰,心中忐忑如潮,暗涌不斷。楊一清的低語仿佛仍在耳邊回響:“我相信,公公是大勇之人,大明的存亡,全系于公公一身!”我深吸一口氣,試圖穩住紛亂的心緒,思緒卻不由自主地飛向那段渾噩的往昔……
那時,我還是先帝身邊的小太監,作為太子的伴讀,日夜陪伴于他左右。我們的職責不過是哄他歡心,逗他玩樂。世事無常,先帝早逝,太子倉促登基。然而,這位新皇帝耽于享樂,絲毫無意于政務之理。朝局動蕩之際,劉瑾如同一只老謀深算的鷹,靜靜地等待著出擊的時機。某日,他低聲對我們說道:“機會只留給那些勇于把握的人。皇上迷于玩樂,這正是我們掌控朝政的良機。文官素來輕視我們,此番若不行動,恐再無翻身之日。”
出于本能的自保,我隨劉瑾一道,將朝中三位股肱大臣逐一拉下馬。朝堂大局易手,但自那一刻起,我內心便不曾有片刻平靜。那從未停歇的低語一次次在心底響起:“這就是你想要的勇敢嗎?這是你想走的路嗎?”我知道,答案始終如針般清晰刺骨。那不是勇敢,只是一種卑怯的隨波逐流。
劉瑾的權勢如日中天,他將朝政視作個人的棋局,隨意安排親信、清除異己。正直的大臣們雖心懷憤懣,卻不敢言語;而那些敢于直言者,則一一被構陷下獄。我看不慣他的跋扈,卻沒有勇氣與他翻臉,只能竭盡所能,在暗中庇護一些忠正之士。那段歲月,我如行于刀鋒之上,隨時可能滑入深淵。
忽然,寧王舉兵反叛的消息傳遍朝野。皇帝不顧勸阻,心生豪興,意欲御駕親征。尚未動身,王守仁便已平息叛亂。我奉命出使寧夏,前往慰勞楊一清所部,并安撫那些因無故調動而心懷不滿的士卒。
在寧夏軍帳中,我與楊一清把酒言談,本以為此行至此便可畫上句號。豈料,他在臨別時忽然將我喚住:“公公請留步。”我轉身看他,心生幾分鄙夷:“掌兵將領私通內廷,可是死罪!楊大人,寧王的下場你當心知肚明,何須我多言?”不料楊一清目光一凜,眼中燃起一抹決絕:“我并非求結黨之利,只是以天下之名,求公公一件事。”
我不由微微挑眉:“何事?”他深鞠一躬,語氣莊重:“請公公上疏彈劾劉瑾。”我冷笑道:“彈劾?前面已有無數人上疏彈劾他,皆被他輕易化解。楊大人何以認為我會不同?一個聲名狼藉的太監,有何膽識做這等事?”楊一清昂然挺立,目光如炬:“我知道公公是有良知之人。若非公公出手,李閣老豈能逃脫劉瑾之毒手?如今那劉瑾專權,私養兵馬,罪證昭然若揭。思來想去,唯有公公有這個能力,也有這個勇氣。勇敢從不是助紂為虐,而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若無人敢為,則天下何以為天下?公公,愿你以無畏之心,上疏進言!”
楊一清的言辭如同晨鐘暮鼓,敲擊著我內心深處最柔軟的角落。我心頭微顫,不知從何而來的熱流涌上心間。我低聲應道:“好,我答應你。”
回到京城,劉瑾特意為我舉辦了慶功宴,話里話外盡是試探與拉攏。然而,宴席間觥籌交錯,我只覺手中笏板沉重無比,幾乎難以握持。宴畢,劉瑾因家中喪事離宮。我親自送他出城,看著他的身影消失在黑夜的盡頭。那一刻,我猛然轉身,在寂靜的長街上跪倒在地。
“皇上,臣彈劾司禮監掌印太監劉瑾,犯謀反大罪!”
那句話一出口,仿佛壓在心頭的巨石瞬間消失無蹤。我靜靜地跪在地上,望著暗夜中無邊的星辰,一股難以言喻的輕松在胸口彌漫開來。此刻,我終于明白—這一步,不是為他人而踏,更非為虛名而爭,而是為了心中那一線微光,為了不再背離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