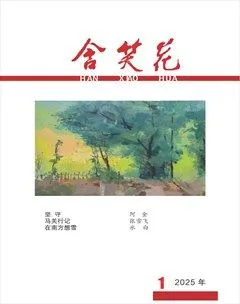孤貧瘠旱渡春秋
又見仙人掌。
從來沒有想過時隔30余年再次見到仙人掌是這樣的讓人措手不及。
那是一篇宣傳報道,一片黃土地上,長滿綠油油的仙人掌,一位身著白襯衣,胸前戴著黨徽的工作人員正在向參觀學習的人們介紹仙人掌的情況,我一翻而過,只是黃土地上綠油油的顏色有些許的印象。
再次邂逅仙人掌是在友人聚餐的餐桌上,它變成了一道涼菜,伴著鮮紅的小米辣、濃香的醬油,散發著誘人的味道。我沒有嘗試,因為我心中有道越不過的坎。
那要從故鄉的小山村說起。
故鄉的小山村,是我人生的起點,是先輩們人生的終點。它悄無聲息地演繹著生命的生生不息。村里只有一條連接鄰村的鄉村小路,向西向南向北都是崎嶇山路,鄉親們前行在致富路上的步伐并不輕松。
記憶里永遠是祖輩、父輩彎腰在石旮旯地翻土的影子。那貧瘠的土地上總是有一些仙人掌,老一輩在整理土地的時候,總是把它們挖出來,堆放在石坎上,在山里掏鳥窩、在地里撿石頭的我總是吃它的虧。
盡管爺爺總是叮囑道:“小心點,不要碰到仙人掌,它有刺,扎手里是挑不出來的。”但我總是嗤之以鼻,它那么丑,還長滿刺,怎配那仙氣飄飄的名字。一不小心“啪”,我摔在石坎上,手心上、膝蓋上都扎滿仙人掌的刺。
世界終于安靜了,仙人掌的刺讓我坐在地埂上安安靜靜、小心翼翼地拔刺。爺爺滿嘴嘟囔地抱怨著我不聽話,又忙不迭地過來給我拔刺。
仙人掌的刺真是讓人一言難盡,它有粗壯精亮的老刺,也有纖細的小刺,這小刺細小易斷又微乎其微,要在適合的角度、恰當的陽光下,才能看到它纖細的刺頭。
爺爺耐心地給我拔刺,他的手很是粗糙,手指就如同蒼老的樹木,被歲月的鋒刃劃出了一道道溝壑,冬天總是用布把手包裹起來。他的手指甲又厚又硬,由于平時他都是用鐮刀割他的指甲,使得他的指甲不平整,他總是夾不住我膝蓋上的那幾根小刺。
我沒有耐心了,跟爺爺說:“不拔了。”聽從村民的偏方,用頭發在膝蓋上和掌心上戳摸幾下,又跑去野去了。爺爺的聲音遠遠地飄來:“刺長到肉離去,到時候有你受的”。
那根刺真的長到了手心里。
它隱隱的疼,時不時地疼,若有若無的疼,偶爾的疼。
村里早就沒有了仙人掌,在我記憶里,仙人掌就沒有長到爺爺的兩個手掌那么長過。
說是要去看仙人掌,我不曾上心。
那有啥好看的!
很快就到了新平鎮的莊子田村。這個村莊的名字一看到就讓人不會忘記。
看到這個名字總是莫名地想到戰國時期的那位大哲莊子,雖然理智告訴自己,莊子和莊子田,一為名士,一為地名,兩者并無直接聯系,只是有些名字上的巧合罷了。但文藝的觸角又讓我有更多的臆想,再次讀了他的《逍遙游》以后,我甚至去查看了他周游過的地方,但我總是不死心,總覺得這位寫出南冥的大哲,知道有南海的存在。
但當我站在近兩米高的仙人掌面前時,我才知道我想象的世界比之沙漠還要枯竭。
莊子田村莊的盡頭,群眾紅墻墨瓦的屋后,一轉彎,成片成片的仙人掌順著山勢蜿蜒而上。一抬頭,綠得晃眼。令我驚訝的不是仙人掌的多、廣,而是它的高。立于我面前一排排參差錯落的仙人掌2米有余,最底下的根莖有大碗口那么粗,外表像樹皮一樣,蒼勁粗糙灰褐有力,延伸至3—4個葉莖之后顏色才慢慢地變成墨綠色,再往上是碧綠色然后青綠色,有的葉莖上還有鵝蛋那么大的果子,同行的文友告訴我,這是仙人掌的果子,很好吃,他還摘了一個給我吃。避開它的小刺掰開,一口吞下,清清甜甜,有一股清涼味兒,很好吃。
或許,這才是仙人掌。
我記憶里那個是另一個品種?
我站近了看,踮起腳尖,挨近了看。因為它下面的根莖已經完全沒有了最初的形態。
就是它,一個品種。
因為小時候我吃仙人掌的虧不止一次。有時候爺爺會把地埂上的仙人掌帶回家,用布包好著手,用刀把仙人掌的刺和表皮削了,搗碎了包在扭傷的地方。討嫌又好奇的我總要上去撥弄兩下,不小心又被刺到。是不是所有人的童年都是這樣,老人再三警告不可以做的事情,我們都要親自嘗試,撞了南墻也不回頭,所以我對它很熟悉。
其實,我對它也不熟悉。我一直以為它就像山里長的樹、地里長的草一樣,是土生土長的,直至30余年后,我才知道它是外來物種。據百度資料記載,仙人掌原產于南北美洲熱帶、亞洲熱帶大陸,1645年由荷蘭人引入中國臺灣,1702年《嶺南雜記》首次記載。根據明朝末年學者劉文徵于1625年的著作《滇志》中記載,當時云南已有引種栽培。現在才知道這個品種的仙人掌會開花、會結果,果實還蠻好吃的。
莊子田的仙人掌種植面積已達4000多畝,2023年僅采摘外銷的300余噸仙人掌果就有600萬余元的收入,戶均增收1.2萬元,村集體增收50萬元。這個數字著實驚到了我。
小時候令人除之而后快的仙人掌竟然使群眾走上增收致富的道路。原來,莊子田的后山這片地向陽時間長、土地貧瘠,種植糧食產量上不去,當時的地埂上有一些仙人掌,群眾用來當作圍欄、邊界線等,一直由著它生長。可能是某一天它開花結果了,地里勞作了一天的人大著膽子嘗試吃下了第一個以后,發現味道還可以就由著它一直長了。可能是某一個人跌倒扭傷后,用去皮去刺搗碎的仙人掌包扎后有消腫祛瘀的作用,所以它一直長到了現在。
不管是什么原因,它留了下來,并成長了一大片,并拓展到現在的4000多畝,以后可能還會更多。
或許是因為它的倔強吧,被人隨意丟棄、認為可有可無之物,在丁點的雨露陽光下依然能保持活力,用力生長。每當人們拖著疲憊的身軀歸家時,它開出了燦爛的花,恭迎主人遠道凱旋。在赤日炎炎似火燒的季節,地里的莊稼都屈服地低下了頭,唯獨有它,依然像門神般巍然挺立,蓬勃向上,甚至結出了香甜的果實,為饑渴難耐的人們帶來清甜。現在,更是為群眾帶來了經濟價值。
突然想到莊子《逍遙游》的句子,“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或許我就是《逍遙游》里譏笑商湯的斥鴳,認為鵬鳥能飛到哪兒去?
突然接到一位遠嫁河北的親戚打來電話,說她已經到文山了,馬上就回西疇了。好快呀!是昨天還是前天才接到她的電話說要回來了,這就到了?
莊子在《逍遙游》寫道:“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他是否感知到,他那扶搖九萬里的鵬鳥到南冥也需要六個月,現在走航空僅幾個小時。
走在莊子田的鄉村道路上,想著這些,我相信了莊子和莊子田真的沒有關聯。但他遵循宇宙萬物的規律,遨游于無窮無盡的境域是無處不在的。
生產車間里,采摘下來的仙人掌被放到銀白色的機器里,被機器脫皮脫刺后,綠油油、滑溜溜得出來包裝打包后被銷售到全國各地。不由得想起爺爺佝僂著背,包著手、拿著刀費力地把仙人掌削皮削刺的樣子。我還在原來的鄉村里,但鄉村的仙人掌已經不在了。
搖晃手的瞬間,總覺得有個手指頭的側面刺刺的,有時碰到刺一下,有時又沒有感覺,同行的文友說,你是不是被仙人掌的刺刺到了。難道是我貪吃那個果子的時候被刺到了?
學員很熱心,她要幫我拔刺。迎著陽光,我舉著手指,我看到了那根刺,比牛毛還細小,又短,若有若無。她的手指纖細修長,指甲圓潤飽滿,泛著淡淡的粉紅色,大拇指和食指修剪整齊的指甲捏住了那根刺,拔了出來。曾經兒時困擾了多次的仙人掌的刺就這樣被拔了出來。
“哎,快!走啦、走啦,我們去參加新中國成立75周年的活動去了,你在發呆想什么。”同事喚醒了飄遠了思緒。
我在想什么,我在想那一株仙人掌。
【作者簡介】謝常春,文山州作家協會會員,現在西疇縣文聯工作。散文、詩歌作品散見于《民族文學》《云南日報》《含笑花》等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