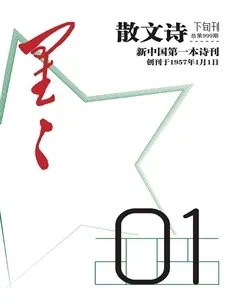每一口古井都虛懷若谷(組章)
一口古井,押中了時(shí)光旋轉(zhuǎn)的韻腳
攜一縷暗香遠(yuǎn)去。荷塘邊,小路悠遠(yuǎn),伸向田野的盡頭,山的那一邊。
雙井,從傳說中直起身來,多情的眼睛憂郁:還有什么在漸行漸遠(yuǎn)?
祖輩們的身影迷失在蒸氣的朦朧中,煤油燈下的寂寞,是磨坊寫出的又一曲哀怨。被磨亮的明月,曾照見小村女子的背影,搗衣聲此起彼伏,替古井說出過現(xiàn)實(shí)。
天再干而井不干,雨再大而井不滿。
肩挑手提的生活在過去里漸漸沉默,文脈的輪廓在時(shí)代的情懷中不斷成長(zhǎng)。面前的莊稼一茬茬收割,養(yǎng)育身后的村莊一層層長(zhǎng)高。洗腳上岸的青年,背著行囊出發(fā),目送的古井佇立成鄉(xiāng)愁。
此刻,誰(shuí)在古井旁聆聽,聽被井水洗過的鄉(xiāng)音——那些押韻的方言,為生活描繪出又一條走向春天的路徑。
曾經(jīng),它喊回過一棵樹的魂魄;把高于流水的鳥鳴從夏天的干燥里救起;目睹過一位母親從雨中的泥濘中挑回一擔(dān)隱忍……現(xiàn)在,它把一切都收了回來:陽(yáng)光的熱情、屋頂上的火苗、季節(jié)的另類……從清朝鑿開的文脈開始,一步一步,走出百年,走進(jìn)歲月里既定的一行。
時(shí)光還在流轉(zhuǎn),以村之名,以路之名,以田野之名。雙井巋然,不偏不倚,押中了小村時(shí)光旋轉(zhuǎn)的韻腳。
沉醉的人還未從活用的詞性中醒來
是你獨(dú)擁的汪洋。
它是平面的,也是立體的。它在你眼前,也在你身體里。它叫鄱陽(yáng)湖,也叫大宗三眼井。
一只眼打量世界,一只眼反觀內(nèi)心。那第三只眼呢?
一定有更多的秘密等待發(fā)現(xiàn)。
曾經(jīng),你發(fā)現(xiàn)身體里有暗流涌動(dòng),蕩滌著朝代的秘史,時(shí)光簡(jiǎn)史。民間有無窮智慧!你用粗糙的肉身摁住了洶涌。擁擠的生活越過等待,你用平靜安撫了七上八下的吊桶,安撫了一小片煙火人間。
現(xiàn)在,你發(fā)現(xiàn)一個(gè)被傳說勾引的人,在章節(jié)里爛醉如泥。最是一口井的牽腸掛肚,讓他從故鄉(xiāng)來到異鄉(xiāng),又仿佛從異鄉(xiāng)回到了故鄉(xiāng)。這樣的千回百轉(zhuǎn)!他沿古老紋路彳亍回走,又從唐風(fēng)宋韻的高貴中掙脫出來,在思想的宣紙上解構(gòu)現(xiàn)實(shí)的微瀾。
多少曾經(jīng)拋棄了現(xiàn)實(shí)。多少現(xiàn)實(shí)被詩(shī)意的字詞敲打。是什么被搬上舞臺(tái),紅進(jìn)綠出。花期如潮,湮沒了荷塘。青苔與衰草努力讓時(shí)光倒流,而一座村莊已脫胎出三座……
所有的經(jīng)歷都寫意成曾經(jīng),萬(wàn)物都在現(xiàn)實(shí)的工筆里瘦身。青山、秀水、白云、候鳥擠進(jìn)同一個(gè)畫框,懸于炊煙的舊址,醉了人間。
夕陽(yáng)西下,沉醉的人還未從活用的詞性中醒來。你仍在心靈的一角隱居,古老成色偏安了大宗村整個(gè)春色。
每一口古井都虛懷若谷
大地遼闊。古老的詞語(yǔ)色彩繽紛,為遼闊大地畫像。
什么才是古老?村莊,河流,山岡……所有被時(shí)光做舊又被時(shí)光保鮮的,都在給我感動(dòng):大地遼闊,只有我最渺小;萬(wàn)物古老,只有我最易朽。
是什么創(chuàng)造了古老?比如一口井的誕生,讓古老有了深意。定居,是井創(chuàng)造出的又一個(gè)感念的詞,它系住了生活跋涉的腳步,有著與河流截然不同的生命朝向。
每一口井都虛懷若谷。它可以選擇天涯,卻甘愿據(jù)守眼前。它本可高于人間,卻甘愿生活在低處。它是平靜的,又是沸騰的。它是個(gè)體的,也是群體的。它是村民的孩子,也是村民的祖先。
我愿是井水的一滴,被沉默的水桶提起,升騰新生活的炊煙。也澆灌從朝代里走出的詩(shī)行,沿著淺淺深深的韻腳,走進(jìn)一張新時(shí)代的紙,隨春風(fēng)蕩漾。也有見到光的歡愉,那一刻,星星、太陽(yáng)、月亮都是神明,給我指引,在去處驗(yàn)證來處。
具體到一個(gè)村莊,我愛一個(gè)叫安山村的地方。愛它的一口井,養(yǎng)大一個(gè)村莊;愛它的許多口井,養(yǎng)活一代代村民;愛它斑駁井欄,生活冊(cè)頁(yè)被時(shí)光磨出的毛邊;愛它古老方言,被井水洗亮,在漫長(zhǎng)故事里映出鄉(xiāng)村底色。
此刻我或已成為一口井,站在安山村的某個(gè)角落,看炊煙再起,聽云淡風(fēng)輕。時(shí)光如流,我卻心如止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