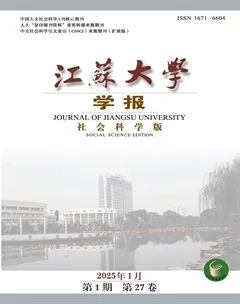中華文化主體性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價值取向
摘 要:主體和主體性是西方哲學的概念,屬于價值關系的范疇。文化主體性是一種精神價值創造能力及其價值影響能力的體現,所以,文化主體性所呈現出的是共同性價值與獨特性價值的統一,具有相應的主觀能動性。中華文化主體性分為古今兩部分,二者都屬于價值關系的范疇,并且都具有延續性和獨特的價值內涵。中華文化主體性決定了中華民族的價值取向,即共同性的價值觀體系、一體性的內部固有共同體屬性、內部天下的價值共同體、人民性的建設目標和方向。
關鍵詞: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主體性;價值取向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課題(21ZD044);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社科學術社團主體學術活動資助項目(21STA014);國家民委民族研究項目(2024-GMG-008)
作者簡介:都永浩,渤海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民族理論學會副會長,從事民族學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
主持人簡介:金炳鎬,中央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哲學博士,從事民族理論、民族政策、民族關系、民族學研究;孟凡東,中央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歷史學博士,從事中華民族發展史、近現代中華民族復興歷程研究。
中圖分類號:G122;D6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6604(2025)01-0001-13
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這一主體性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的;是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建立起來的。創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這一文化主體性的最有力體現。”【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J].求是,2023(17):4-11.】中華民族、中國人民是中華文化、中華文明的創造者,中華文化主體性必然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價值取向。
一、 中華文化主體性是價值關系的體現
主體和主體性是西方哲學的核心概念,是思考人類社會的必要途徑。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Protagoras)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羅素.西方哲學史:上[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吉林音像出版社,2005:88.】如果從人的整體性理解,這句話表明了人類主體性的一個重要面向,即人類作為主體的命題奠定了主體性概念的邏輯基礎。在人類早期社會的漫長時期,人類依附于自然萬物,受到“萬物有靈”觀念的約束。最早使用主體范疇的亞里士多德也未能擺脫主客混淆的認識——實體并非專指人類的范疇:實體“便是一個個體的物或人或動物。但是在次要的意義上,則一個種或一個類——例如‘人’或者‘動物’——也可以叫作一個實體”【同①:231.】。將人類與主體融合,并將主體性賦予人類主觀能動性的作用,是近代工業和科學技術突破的結果。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人類不再完全附屬于自然萬物而存在,而是能夠對自然萬物形成較大的影響,成為具有主體性的創造者。
近代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突破和工業革命的出現,人類的主觀能動性更加凸顯,人類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對大自然的絕對依附。因此,主體性就與人類統一起來,成為人類在價值創造領域的專屬概念。人類的主體性體現為自主性、自覺性、能動性、自省性和先進性,這五種屬性是主體和主體性歷史演變的結果,即從古希臘的人與物同性、同源的實體主體,到近代以認知為特征的主體,再到現代以人為中心的屬人主體,最終完成了從本體論、認識論到人本主義的轉變。所以,現代的主體概念是指作為價值體現的人類;而主體性是指由人類的價值體現所形成的價值能動性。確切地說,人類本身并不是主體,只有與價值結合才能成為主體;同樣,主體性只能在一種價值關系的范疇中才能成立,單純的價值性也不一定能實現一種主體性,只有那種在價值關系中居于主導、標桿、引領作用的價值性才能轉化為主體性。因此,主體性是指人類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共同價值性和從世界意義衡量的價值能動性以及在人類社會的地位、作用,其主體性價值在價值關系范疇處于核心地位。主體性是在主體間性的比較中反映出來的價值交互評價和定義。主體性既不是孤立的,也不能由主體本身認定,而是要在世界范圍的交往實踐過程中來驗證。
揆諸上述,我們面臨第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就是:現代的主體、主體性概念的核心是人類,那么為什么會出現文化主體性的概念?其邏輯在于,人類的靈魂是文化,社會、政治、經濟、倫理的人等均受制于文化的人的影響和制約,國家、國民文化是人類價值最集中的體現。由此,文化主體性也就等于人類主體性。第二個問題是“文化主體性”的文化指的是什么?“文化主體性”的“文化”不是指族裔(中國古代的族類)文化,而是指國家文化或國家與區域文明,即便是指某一個族裔(族類)文化,亦是指跨族裔(族類)文化屬性的核心價值觀、信仰之類的因素。概而言之,“文化主體性”的“文化”不是宏觀的文化概念,而是狹義的文化概念——以價值觀、政治信仰等為主要內涵的文化精髓或某一種文化共同性的精華概括,這種“文化”的載體為國民共同體(比如中華民族)和國家。由此而言,“文化主體性”也可以理解為國家文化主體性、國民文化主體性或文明主體性。
研究中華文化主體性,必須對“中華”的內涵有透徹的理解,否則就無法對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概念、要素進行深入的研究。“中華”是文化主體性的載體,文化主體性是“中華”主體性的一部分。關于“中華”,可從“華”和“夏”的含義入手理解,如《尚書正義》釋曰:“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冕服采章’對被發左衽,則為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尚書正義·卷十·周書·武成第五》)。綜合上述內容,先秦時期將華夏與四夷視為一個整體,也就是內部的“天下”,即“王言華夏及四夷皆相率而充己,使奉天成命,欲其共伐紂也”(《尚書正義·卷十·周書·武成第五》)。華夏即“諸夏”,也是在周王的“天下”秩序統轄范圍之內。“夏”可稱“大國”,但也指禮儀之大:“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春秋左傳正義·卷五十六·定公十年》)。“華”“夏”均指禮儀之大,文明之邦,擁有先進的禮法制度,以此區別相對落后的四夷。歷史上“中國”在相當長的時期指的是華夏集中活動的區域,是“內部天下”的一部分。然而事實上,“諸夏”活動的地域亦為華夷雜居,夷狄的人口數量眾多,京師、王畿亦如此:“洛陽為王城,而有楊拒、泉皋、蠻氏、陸渾、伊雒之戎。京東有萊、牟、介、莒,皆夷也”(《容齋隨筆·卷5·周世中國地》)。歷史文獻相關記載比比皆是,所以,在“夷夏互變”的歷史背景下華夏無疑是“五方”大融合的結果。由于中國“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呂氏春秋·審分覽第五·慎勢》),“天下之中”除了地理空間的含義外,“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荀子·大略》)。“四旁”指諸夏和四夷,而“禮”既指正統性,亦指“有德”。揆諸上述,“中華”可以作為華夏的族類代稱,有文明的蘊含;但更重要的是指位于“內部天下”中心區域的中原政權(國家)和文明區域,即“中華者,中國也。親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儀,故謂之中華”(《故唐律疏議·唐律名例疏議釋義》)。所以,“中華”作為族類(華夏)名稱和歷史上的“中國”概念,具備了主體地位;而作為文明區域的象征,其在價值關系范疇中同時又具備了主體性的資格。更為重要的是,“中華”作為族類身份、文明的象征、國家的代稱和國家政權正統性的基礎和條件,成為夷狄逐鹿中原的理由。比如,通過“以夷變夏”融入華夏族類;通過中原文明獲得“內部天下”的文明話語權、文明資源的支配權;通過在中原區域建立政權(國家)獲得“內部天下”的正統地位和維護“天下”秩序的資格。
綜合文明、政權(國家)、族類等概念并且具有開放性代表意義的“中華”與“文化”結合而形成的“中華文化”概念,其內涵與外延極具包容特性。首先,廣義的古代中華文化等同于“內部天下”文化,包括“中國”文化與夷狄文化兩部分,華夏-漢族文化脫胎來源于早期的“中國文化”,逐步從“諸夏”文化演變成華夏-漢族文化。以此維度而言,古代的中華文化(“內部天下”文化)的構成部分為“中國”文化、華夏文化和夷狄文化三部分。第二,從狹義的角度理解,中華文化等同于“中國”文化,具有古代國家文化的屬性,并帶有超越族類性的特征。因為早期“中國”雖然以華夏族類為主,但仍然包含眾多的夷狄成分在內。
所謂中華文化的現代形態,是一個外延比較寬泛的概念。如果從廣義的角度理解,它既包括56個民族的基礎層級文化,也包括屬于中華文化認同內涵的頂層文化,即國家文化和國民文化。所以,廣義的中華文化不是“中華文化主體性”所指的“中華文化”,其內部層級間的關系是指“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都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中華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葉”【習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強調 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 推動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J].中國民族,2021(8):4-7.】,“中華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習近平.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3.】,但“各民族文化”不等同于中華文化(即狹義的中華文化),而是中華文化的來源和高度的概括。狹義的中華文化是指中華文化認同方面的內涵,即核心價值觀、政治信仰等文化精髓,是跨族裔(族類)、政權(古代)、地域的體現共同性的精神價值。“中華文化主體性”中的中華文化,亦與國家文化內涵有諸多的要素重疊。狹義的中華文化與中華文明在基本內涵上是一致的,當然要排除物質文明方面的要素。
我國關于古代文明的標準不同于西方盛行的“三要素”標準——城市、金屬和文字,而是根據中國歷史發展的特點,提出的中國化的古代文明標準:出現城市、階級、王權與國家【王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獲[EB/OL].(2022-10-20)[2023-06-13].https://www.cssn.cn/wkskjh/wkskjh_qkjj/202210/t20221020_5550490.shtml.】。這與恩格斯關于“城市、階級分化、商品生產的古代文明社會標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84.】的論述基本吻合。上述標準或標志最重要的體現是古代國家的形成,恩格斯因此指出“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93.】。中國古代文明的主要內涵可以概括為包容性、協和性、轉換性、一體性、正統性、一致性、進取性等,與中華文明現代形態的主體性、共同性、人民性、本土性一起構成了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五個特性【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J].求是,2023(17):4-11.】。中華文明的上述內涵與特性,與狹義的中華文化或者中華文化認同的內容是基本一致的,質言之,中華文化主體性也就是指“狹義的中華文化”主體性或者中華文明主體性。
中華文化主體性處于價值關系的范疇之中,其主體“中華”體現出自主性、自覺性、能動性、自省性、先進性等價值屬性,是促進人類文明不斷進步的價值體系的創造者。中華文化主體性分為兩部分:古代中華文化主體性和現代中華文化主體性。現代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核心要素來源于古代中華文化主體性,“是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J].求是,2023(17):4-11.】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中華(中華與中國同義)文明內涵基本重疊,屬于狹義中華文化的范疇。中華古代文化主體性的主要內涵是“內部天下”文化中超越族類性的那部分內涵,即核心價值觀、政治信仰等內涵。現代中華文化的承載主體是中華民族和國家,中華文化主體性的主要內涵包括古代的文化主體性因素和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華文化的現代形態)的主體性因素以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主體性因素。
二、 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歷史表現
古代中華文化主體性與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古國和區域的文化主體性存在著本質的差異,其他文明古國和區域的文化主體性覆蓋空間比較狹小,而且不存在主體和主體性在固有空間的自我擴展問題。與此不同的是,中華文化主體和主體性是一個在固有空間持續擴大的歷史過程。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如果處在不同區域人類交往能力比較薄弱的時期,空間的相對封閉性對其內部的諸多要素會形成明顯的影響。比如在中國古代相當漫長的時期,廣闊空間的相對封閉性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抑制了文化、文明的特征以及內部秩序規律的運行。譬如古代中華文明的形成,呈現為多樣性與內斂性相統一的特點,雖然文明的起源表現為多點興起、自成體系,但在空間內部性和整體性的抑制下,統一性、整體性成為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這種內部性趨勢可以用“旋渦內聚”來形容【趙汀陽將這種內部互動關系概括為“漩渦效應”,即以中原作為逐鹿的核心,在強大向心力“漩渦”的誘惑下,“主動”或“被動”地加入游戲成為競爭者,博弈“漩渦”逐步擴大,最終達到穩定而形成了廣域的中國(參考趙汀陽《天下的當代性:世界秩序的實踐與想象》,中信出版集團,2016版第149頁)。筆者認為,“漩渦”是對“天下”內部性特征的形象描述,反映了中心約束下互動空間的共存形態。這個“漩渦”的形成是固有性的,建立在相對封閉的廣闊自然地理空間基礎上。“漩渦內聚”指“內部天下”在中心與邊緣的互動中,所形成的內部聚合屬性以及內部聚合化的實踐過程,并伴隨著相對應的觀念、政策措施等的形成。】。
古代中華文化主體性集中體現在古代中華文明上。早期的古代文明從“滿天星斗”到“月恒日明”,長江中下游流域、黃河中下游流域、西遼河流域成為中華早期文明的引領者,其中,距今五千多年的長江下游的良渚文明、西遼河的紅山文明成為中華文明的引領者,這兩個文明區域的居民屬于四方夷狄的一部分。隨后進入早期文明的還有川西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河套地區在文明化進程中走上了一條不同于中原地區的道路”【國家文物局領導:《中華文明起源研究有關情況:從“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國”重大項目談起》[EB/OL].(2023-06-13)[2023-12-10].http://www.ncha.gov.cn/art/2023/6/13/art_722_182278.html.】。以上早期文明區域有四個屬于四方夷狄聚居的區域,其后成為早期“中國”的核心區域,是古代中華文化主體性的主體。該主體顯然是五方的融合體,是“內部天下萬民”的概括。不同文明區域統一趨勢的轉折點開始于距今3 800年左右,其核心是夏商王朝時期的二里頭文化,標志著新石器時期“滿天星斗”向具有中心控制廣域空間能力的“月明星稀”時代的演進,即中原文明主導“內部天下”文化時期的到來,也標志著早期“中國”(王權時代)文明主導“內部天下”秩序時代的到來。中原地區成為“內部天下”的主體,除了居于相對封閉地理空間的中心區域外,以下因素更加促成了這一格局的形成:一是同緯度自西向東流動的大型河流為統一的文明區域的形成創造了必不可少的條件,比如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西遼河流域共同構成了統一而廣闊的中原文明,其中黃河中下游流域擁有更加適宜的氣候、更適合黍粟麥種植的土壤、抵御自然災害能力更強的旱地農業,因而成為文明的核心。二是形成于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發現于河南省安陽殷墟。文字是古代文明的重要標志,是廣域控制能力的基礎。文化主體性如果沒有文字的要素,其價值關系就無法建立起來。三是距今5 000年前“銅的冶煉和制作技術也從西亞經中亞地區、河西走廊傳入黃河中游地區”【王巍,趙輝.“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獲[J].中國史研究,2022(4):5-32.】,距今4 000年左右在中原地區出現比較成熟的青銅器。四是比較成熟的大型古代城市在中原出現,成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都邑,“其特征是,聚落規模巨大,面積達數十萬乃至百萬平方米。聚落內有明確的功能分區,有宮殿區、手工業作坊區、墓葬區、一般居民區等”【同②.】。“城市是文明社會的概括”【黑龍江大學滿學研究院.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研究文摘[J].滿語研究,2023(2):5-13.】,是人類主體成熟的前提條件,所以,我國的考古學家非常重視用古代城市作為文明社會的標準。
在古代,作為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早期主體是立足于中原地區的“中國”居民,通常稱之為諸夏-華夏,而實際上更準確的稱呼應該是由“五方之民”共同構成的中原居民,是具有文化性和地域性的超越族裔性(族類性)的共同體。華夏是在不斷“夷夏互變”的過程中發展壯大的,這一歷史過程始終沒有停止過。更為重要的是,中華文化主體性的主體——“中國”居民并不是完全同質的,而是由華夏和部分四方夷狄構成。與一般四方夷狄不同,這部分夷狄經過了主體的“聲威教化”,納入了“天下”的內部秩序之中。歸入“因俗而治”“修教齊政”管理范圍的夷狄與華夏共同構筑了精神疆域,即在各族類的精英階層形成了共同的價值觀紐帶。綜上所述,中華文化主體性的主體是在中華民族歷史上創造了古代中華文明的“五方之民”的精英及其政治共同體——“中國”,其核心是擁有共同價值認同和政治信仰的“五方”精英群體。歷史上的主體處在持續的壯大過程中,既包括“以夷變夏”(化異為我)的積累過程,也包括經過“聲威教化”納入“內部天下”秩序的夷狄精英(化異為和)。這樣的主體在清經康雍乾三代治理,實現了“長城內外皆一家”,實現了空前的大一統【中華民族共同體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3:257.】,即“中國”與中華民族的固有地理空間的大致重疊;從精神范疇上而言,這一時期基本實現了“五方”精英群體在“內部天下”對共同的“精神疆域”的構筑,因而成為中華文化主體性的牢固基礎,正如康熙所言:“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清實錄·第五冊·圣祖仁皇帝實錄》)。
中華文化主體性在先秦時期即已形成。主體性體現于人類之間的價值關系范疇,從文化角度而言,主體性形成于以儒家為核心的思想體系中。先秦時期是存在主客混淆的思想認識時期,在《周易》中還未形成主體性意識:“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易經·上經·乾》)。也就是天人合一,甚至是人神合一,人類只有與自然萬物甚至是超物質的神靈融為一體才可能作為主體存在。在這樣的認識下,不可能形成現代意義上的文化主體性。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老子將人從道、天、地中分離出來,作為其中一部分,本身就是一種觀念革命,特別是否定了天命至高無上的地位。但是,人的因素仍然在“四大”中居于末位,而初始的、本體的、生生不息的“道”是天下萬物的本源,居于“四大”之首,所以決定了人類的主體性缺乏存在的基礎。雖然孔子、孟子、墨子等仍然探討“天命”“天道”等觀念,但根基已經動搖。比如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篇第十一》)“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論語·雍也篇第六》)這無疑提高了人類的主體地位,減弱了人類對神靈、鬼魅的依賴和恐懼,掃除了人類通向主體性的障礙。
古代中華文化主體性最大的躍升來自儒家思想。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論語·衛靈公篇第十五》)“忠信”“篤敬”是指孔子倡導的德——“仁義禮”,這是“中國”被“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戰國策·趙策二·武靈王平晝閑居》)的基礎,也是中華文化主體性與“內部天下”擴展的基礎。歷史上的中華文化主體性僅限于在“內部天下”的范圍內拓展,在中華民族的內部建立起價值關系,并形成共享的價值認同主體。主體性的內部性色彩是中華古代文明有別于外國古代文明的突出特點。構筑內部價值關系的文化主體性的主要方式是“教化”,即“以德懷之”,孔子將其概括為“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篇第十六》),即通過針對“五方之民”統一價值標準的“教化”建立共同的價值體系,也就是構筑共同的精神疆域。孔子描繪了一個理想的“內部天下”:“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篇第十二》)“教化”成功的標志以“聲威”作為驗證,但“教化”是自愿的、自然而然的過程,“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禮記·經解第二十六》)。
古代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核心價值內涵的確立,始于西漢的董仲舒,他在孟子“四德”——“仁義禮智”的基礎上,提出構建“五常之道”,即獨尊“仁義禮智信”,“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第二十六》)。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的核心價值標準進行的“教化”,使得“內部天下”處于一個統一的價值體系或主體之中,“四海之內若一家”(《荀子·非十二子》)“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禮記·禮運第九》)等,形成一個在人類核心價值范疇內具有主觀能動性的古代中華文化主體性。
古代中華文化主體性強化了其主觀能動性,形成了對外來文化的強大本土化能力。比如,漢唐時期佛教傳入和傳播,最終形成了中國化的佛教。明清之際、晚清民初的西學東漸,盡管從交往角度來看收效甚微,但對中國的思想、文化、政治、社會、經濟、科學等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最直接的結果是使得中國社會進入近代民族國家行列。從表面上看,這一過程體現為中華傳統文化主體性弱化的趨勢,但最終是西學東漸的成果被本土文化所消化。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是近代以來西學東漸的結果,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中國的傳播體現為中國化時代化的動態過程。新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對西方文明成果的吸收同樣伴隨著本土化的過程。
三、 中華文化主體性決定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價值取向
文化主體性是一種精神價值創造能力及其價值影響能力的體現,所以,文化主體性是優秀文化所呈現出的共同價值,是獨特性與共同性的結合,具有相應的主觀能動性,其價值的評價不是自我的、孤立的,而是在文化主體間性中體現出來的比較價值。
當代中華文化的主體性最有力的體現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過程中不斷得到體現和驗證。當代的中華文化主體性體現出獨特的價值,是文化自信的基礎,是自我性、自主性的前提,在具有自身特殊性價值的同時,也具有全人類共享的價值觀。德國近代著名哲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提出:“民族既非語言的單位,也非政治的單位,也非動物學上的單位,而是精神的單位。”【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上冊[M].齊世榮,田農,林傳鼎,等,譯.北京:群言出版社,2014:227.】在歷史上,華夏和中華民族(“五方”的“內部天下”共同體)均是以統一的文化為標準形成的。中華民族是由56個民族成員組成的國民共同體,國家文化或中華文化、中華文明是中華民族的靈魂,決定了中華民族和國家的發展方向和底色。作為文化、文明的價值體現和在價值關系范疇的主觀能動性,中華文化主體性決定了中華民族的價值取向。
(一) 中華文化主體性構筑了共同性的價值觀體系
中華文化主體性是主體(中華民族)共享的核心價值觀并在價值范疇形成的主觀能動性,具有共同性的價值體系并對其他主體形成引領、借鑒作用。
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共同性價值就是中華民族的價值取向,其具有如下突出特征:其一,共同性價值是穩定的、延續的。如“這些圣王所講的理念、所持的治國方略就是‘王道’。若能以此道來教化、治理天下,就是‘王化’”【晁福林.中華民族一體化過程中若干重要認識問題[J].文史哲,2023(3):5-15.】。這種統一的價值觀(周禮),被視為“天下”正統(“大一統”)的標準和“教化”的基礎。其后始于《春秋》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確立于西漢兼容諸子百家的中華文化主體性,貫穿了中國思想史的全過程,在內部天下互鑒的過程中不斷完善、成熟。因此說,當代中華民族的共同性價值來自歷史的延續性。其二,政治共同性貫穿中華民族歷史全過程,最典型的表現是“大一統”思想。“大一統”成為華夏和夷狄共同追求的政治理想,其內涵不斷豐富,“從正統性逐步擴展內涵要素,是中華民族向內凝聚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思想核心”【孟凡東,翟成鵬.論“政治大一統”的現代意蘊、現代共同體價值及世界意義[J].社會科學輯刊,2024(4):219-227.】。如,“天下”的中心成為正統的依據和“大一統”的有利條件;“有德者居天下”成為非華夏族類進入中原逐鹿的依據;“疆土開拓廣遠”成為元朝、清朝統治正統性、合法性的佐證,將“大一統”演化成了“大統一”;清朝統治者從同屬于“內部天下”秩序“猶中國之有籍貫”的角度驗證統治的正統性。其三是歷史上中華民族的精神疆域是廣泛共同性的形成過程。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價值觀對“內部天下五方之民”的“教化”所形成的穩定、持續的跨政權、族類的認同區域,就是中華民族的精神疆域。中華民族歷史上有三個空間形態,即固有的、相對封閉的地理空間、“教化”空間(化內)、“聲威”空間(政治勢力范圍),三者重疊就是“大一統”真正實現的標志。歷史上,精神疆域的擴展往往領先于“聲威”空間,不受政權分立狀態的影響。其四,中華民族具有共有精神家園的當代構筑。共有精神家園的根源是歷史上的精神疆域,精神疆域是核心價值觀、政治信仰等方面共同性最充分的體現,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所在,必然是當代共有精神家園的核心內涵之一。共有精神家園內涵與中華文化主體性、中華文化認同、中華文明現代形態具有緊密的邏輯關系,中華文化認同、中華文明現代形態是中華文化主體性核心價值的體現,也是中華民族共同性的最集中體現。“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增進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重要舉措”【潘岳.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J].中國民族,2023(12):14-17.】,是增進中華民族共同性價值的重要途徑。
(二) 中華民族具有一體性的內部固有共同體屬性
相對封閉的地理空間的意義在于,有利于作為主體的中華民族(歷史上“內部天下”的“五方之民”)在空間上形成并保持一體性,即空間外的力量難以進入更不可能立足,同時亦有利于空間內的“五方”共存、共在觀念的形成。為了共同的利益,必須兼利兼容,而不能搞零和博弈。
空間的相對封閉性是一體性、內部性形成的根本原因。首先是作為主體的古代中華民族(“內部天下”共同體)很難突破內部空間而無限拓展。譬如先秦時期不可能認識到固有的內部空間的存在,但還是將“天下”賦予一定范圍的內部性,如“九州天下”(《尚書·夏書·禹貢》)。在《左傳》中,“天下”空間更為清晰,并且將“聲威”與“教化”效果同時作為“天下”的條件,這成為其后判定是否為“化內”的不二法則。固有“內部空間”的邊緣最終成為中華民族的邊界,原因在于即使“教化”可以跨過這一空間邊緣,但“聲威”(武力和秩序)很難維持,而在“聲威”未及或不穩固的情況下,“教化”本身不能單獨支撐內部性的形成。與此同時,在中國歷史上精英階層的觀念中,空間的拓展不能以疲敝“五方之民”為代價,最理想的空間范圍是從“方千里”起步到“方萬里”。因此,相對封閉的地理空間在歷史的消磨中構成中華民族對外的內部性和對內的一體性,最典型的描述是“一家”“一人”“一同”“一體”等。其次是古代中華文化主體性不主張突破內部空間的范圍。主體性的擴展是“教化”的過程,“教化”范圍一旦突破相對封閉的地理空間,就會直接面對與外藩和外部文化的沖突,這對于以“協和萬邦”為維護“內部天下”秩序的“中國”而言,無疑豎起了一道天然的倫理屏障。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文化主體性是內斂的,不主動向外藩推銷自己的價值觀,也不會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于人,但同時也歡迎外藩學習中華文化,比如《禮記》對于這種內斂性進行了經典的概括:“禮不逾節,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禮記·曲禮上第一》)。仁和禮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是內涵,禮是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體現“中和位育”(《禮記·中庸》)思想,強調協和自然、不偏不倚、各安其位,不主張文化霸道輸出,提倡以德服人是誠服,以力服人則非心服,“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孫丑上》)。在此認識下,“禮,聞取于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禮記·曲禮上第一》)。中華文化主體性依靠自身的內在價值來體現,而不是靠人為的文化價值輸出和取代其他文化價值來體現。中華文化主體性從精神上鞏固了中華民族一體性、內部性的觀念。中華民族的對內一體性、整體性與對外的內部性并不會影響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因為中華民族的內部性并不排斥外部性,“春秋之法,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蓋來則懷之以恩,畔而去者不窮追之”(《明宣宗實錄·卷三十八·宣德三年二月》),既堅守自我性和獨特性的內部天下互鑒,又在文明互鑒中吸收一切文明成果中的有益要素,促成中華文化主體性中包含了全人類共同的價值觀。中華民族追求協和的全球人類觀,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協和萬邦是中華文化主體性發揮能動性的方式,也是中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原則。
中華民族固有的一體性、內部性決定了各民族的先民及其政權不存在何時加入“中國”和中華民族的問題,也不存在“跨境居住的同一民族”的主權歸屬問題,因為經過“聲威教化”的某個民族或某個民族的一部分已經納入了“內部天下”的政治秩序和核心價值認同體系之中。
(三) 內部天下的價值共同體
先秦時期“大一統”觀念的本質內涵是通過尊奉周朝立法為正統,達到以周天子為天下四方諸侯共主以及統治秩序正統性、合法性的目的。因此,“天下一統”成為統治者的最高政治目標。文化主體性要求在“內部天下”形成共同的價值觀,因而也必然需要內置其中的“國”和族類的位置下移,將崇高性讓位于“內部天下”共同體。荀子說:“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荀子·正論》)將“國”的地位置于遠低于“天下”的位置,這是“內部天下”觀的根基,決定了“內部天下”觀的靈魂是“大一統”思想。中華文化主體性則是實現“大一統”國家的精神動力。墨子提出“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墨子·法儀》),其表達的觀念更為透徹,將“天下一統”“萬民一體”神性化、理想化。
歷史上中華民族“內部天下”的這種至高地位,說明其下大小國和族類均是“巢下之卵”,屬于局部的范疇,在層級上是上下級的關系。從共同性與差異性的角度來看,先秦時期形成的“和”的觀念,即差異性基礎上的和諧,也可以理解成多樣性基礎上的統一。在“天下”內部性的影響下,諸族類無論強弱、大小均不被看作“天下”主體,只有“五方之民”和“天下國家”才能成為主體。總體而言,差異性或多樣性包含于共同性或統一性之中,兩者并不是平等的范疇。“內部天下”從“邦畿千里”、方三千里的“冠帶之國”,到“方萬里”固定下來。“方萬里”的“天下”在精神上始終是統一的、完整的,不受內部政權分立和局部一統的影響;在內部空間內,無論居于中原的政權與分立其邊緣的其他政權處于何種關系,都不會影響整個“內部天下”的完整性與統一性。今天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及其共同性就是其歷史延續的結果。
(四) 中華文化主體性蘊含著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人民性目標和方向
人民性是當代中華文化主體性最主要的價值內涵,也是有別于其他國家文化主體性的鮮明特征,是當代中華文化主體性內涵中自我性、獨特性、先進性、主觀能動性形成和發揮作用的主要原因。
“人民”概念產生于歐洲的古羅馬,當時的人民還是一個限定性的范圍,即只有擁有參政資格的精英階層和平民才屬于人民。但這樣的限定并不是固定不變的,人民的范圍最后甚至與公民概念重合,人民與公民適用一套共同的準入標準。人民的范圍不斷拓展,“法律是從人民的意志中得到可強制性的”,“所以,馬西利烏斯將全體公民的總和稱為‘人類立法者’”【沃爾特·厄爾曼.中世紀政治思想史[M].夏洞奇,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205.】。到了法國大革命時期,人民的概念最大范圍覆蓋了以平民和下層民眾為代表的平民階層,甚至可以將人民定義為“除王室、君主主義者、貴族、邪惡的人、富人、演員、雇傭作家之外的全部法國居民”【卡羅爾·布拉姆.盧梭與美德共和國: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語言[M].啟蒙編譯所,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230.】。也就是說,人民具有了階級屬性。馬克思從階級對立的角度使用人民概念,排除了“統治階級”,為了革命的需要而將農村、城市小資產階級納入人民的范疇【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61.】。列寧同樣堅持人民階級性的觀點。
在中國,人民觀念的萌芽形成于先秦時期,當然這一思想從來沒有在古代政治實踐中得以實現。比如,《禮記·禮運》中的“天下為公”思想,想象出一個公有而公平的社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呂氏春秋·孟春紀第一·貴公》);“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墨子·法儀》)。
黨的十八大以來,團結更多的積極力量成為人民概念變化的原因。“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擴大為“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者”,人民概念與國民、公民概念基本重合,范圍略小于后者。
中華文化主體性最鮮明的自我性和特殊性體現為價值體系的人民性,黨的二十大報告將其概括為人民至上、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的目的一切為了人民,發展的途徑一切依靠人民,發展的最終結果由人民共享。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文明現代形態和人類文明新形態建設和實現的途徑,其本質是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共同富裕,堅決防止兩極分化。這些思想價值是我們建設中華文明現代形態的基礎,也是在世界文化主體間的價值關系范疇中勝出一籌的有力證明。
人民性同樣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目標和方向。在近代的中華民族建構中,大多數學者雖秉持有不同的學術維度,但基本上沿襲了孫中山“中華國族”“國族團體”論的基本觀點——各少數民族融入漢族再建構統一的國民共同體【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一九二四年一月至三月)[M]//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孫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239-242.】。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從來不用單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匯聚成共同文化,化解沖突,凝聚共識。中華文化認同超越地域鄉土、血緣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內部差異極大的廣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認同和維護,就越會綿延不斷。”【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J].求是,2023(17):4-11.】這一論斷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指明了方向。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要遵循人民性的方向,將中華民族共同體作為人民共同體和國民共同體來建設,在包容差異和多元的前提下,將人民屬性作為最大的共同性來建設,通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從公民身份的角度實現共同富裕,防止兩極分化;通過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法治的途徑,實現各民族身份公民的真正平等;通過匯聚法治內涵的共同性,解構差異、多元因素對共同性的消極影響。
基于上述對主體和主體性內涵及基本概念的分析,本文重點探討了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歷史過程以及對中華民族價值取向的影響。中華文化主體性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主體性,其核心因素是歷史上中華文明的形成和演變具有明顯的特殊性。中華文化的主體性源于地理空間的相對封閉性而呈現出不同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運行軌跡,對外具有內部性,對內具有一體性或整體性,“向內凝聚”“漩渦內聚”成為中華民族歷史的主旋律,奠定了中華文明連續性的基礎,也是中華文化主體性具有頑強生命力的根脈所在。對外內部性也決定了中華文化主體性首先是具有自我價值,不向“化外世界”帶有目的地傳播自己的價值觀,而是秉持文明交流互鑒、共享共存的協和觀。及至當代,中華文化主體性在堅守自我性的同時,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的發揮“引領力、輻射力”,堅持包容性、和平性的文明觀。在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價值內涵中,包括了中華文明、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觀以及代表性的科技成就,對中華民族的價值取向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并形成“以共同奮斗力、共同融合力、共同凝聚力為主要內容的向內凝聚發展源力”【孟凡東,翟成鵬.向內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源力論析[J].東疆學刊,2024(4):1-10.】。
(責任編輯: 張向鳳)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Du Yonghao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Bohai University, Jinzhou 121013, China)
Abstract: Subject and subjectivity are western philosophical concepts in the category of value relationships. Cultural subjectivity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creativity and influence of spiritual values. Therefore, it presents the unity of universal values and unique values, and has thus corresponding subjective initiative.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is divided into ancient and modern parts, both of which fall into value relationship category and are continuous and unique in value connotation. It determine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on values, a unison community that regards “the world” as the highest value, and a people-centered communal building goal and direction.
Key words: Chinese nation; Chinese culture; subjectivity; value orien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