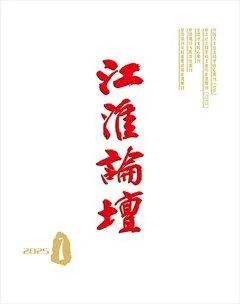馮契的知行觀與中國(guó)傳統(tǒng)哲學(xué)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
摘要:隨著世界步入現(xiàn)代化及西學(xué)漸入中國(guó),中國(guó)傳統(tǒng)哲學(xué)的知行觀面臨著倫理主體如何轉(zhuǎn)化為實(shí)踐主體的任務(wù)。新儒家要么把心性的主體改造為意志的主體,要么陷入理性和“覺知”的二元結(jié)構(gòu),難以真正解決思想的客觀性問題。在批判改良派和革命派分離知與行的基礎(chǔ)上,馮契把金岳霖的“得自”經(jīng)驗(yàn)和“還治”經(jīng)驗(yàn)革新為“得自”現(xiàn)實(shí)和“還治”現(xiàn)實(shí),人的能在活動(dòng)指向了感性之“所”,理論和現(xiàn)實(shí)得以統(tǒng)一,主體在掌控知識(shí)中獲得自由感,達(dá)成樂生境界,知識(shí)和智慧融為一體。馮契對(duì)傳統(tǒng)哲學(xué)的創(chuàng)新開啟了知行觀的新局面:把傳統(tǒng)哲學(xué)的“能-所”結(jié)構(gòu)與現(xiàn)代實(shí)證科學(xué)對(duì)接,開啟了中國(guó)傳統(tǒng)哲學(xué)與杜威“探究認(rèn)識(shí)論”對(duì)話的可能;事實(shí)和價(jià)值的深度融合也聯(lián)結(jié)了“成物”和“成己”,推動(dòng)了具體形而上學(xué)的構(gòu)建。與新儒家相比,馮契轉(zhuǎn)化心性主體為實(shí)踐主體的創(chuàng)新在于,在“還治”維度上賦予實(shí)踐以辨驗(yàn)的可能性,在歷史維度上中介知識(shí)和智慧。驗(yàn)證和中介給予傳統(tǒng)哲學(xué)的倫理主體以經(jīng)驗(yàn)性,構(gòu)建出兼具中國(guó)傳統(tǒng)哲學(xué)智慧特征與西方哲學(xué)知識(shí)論取向的哲學(xué)新局面,為中國(guó)傳統(tǒng)哲學(xué)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提供了一條歷史主義路徑。
關(guān)鍵詞:馮契;知行觀;中國(guó)傳統(tǒng)哲學(xué);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
中圖分類號(hào):B26" "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 文章編號(hào):1001-862X(2025)01-0041-008
傳統(tǒng)儒學(xué)的核心是心性論,知行觀與心性論相關(guān)聯(lián),旨在實(shí)現(xiàn)行動(dòng)與心性覺悟的相互滲透。儒學(xué)在宋明時(shí)期達(dá)到高峰之后,此種知行觀面對(duì)著近代科學(xué)觀念漸入的沖擊。以張君勱、熊十力、牟宗三等為代表的新儒家意識(shí)到,心性論的知行觀限定自身為倫理的主體,在一定程度上封閉了“利用厚生”的通道,難以兼容科學(xué)探究指向的外在世界的客觀經(jīng)驗(yàn)。新儒家把道德的主體轉(zhuǎn)化為“認(rèn)識(shí)的主體”“政治的主體”“實(shí)用的主體”,建構(gòu)進(jìn)路“以一種實(shí)踐的優(yōu)位性的哲學(xué)信念滲入其中國(guó)歷史文化的詮釋之中,而強(qiáng)調(diào)一種主體的轉(zhuǎn)化的創(chuàng)造(subject-transformative creation)”[1]。轉(zhuǎn)向?qū)嵺`主體的建構(gòu)路徑旨在以啟蒙的姿態(tài)打通心性之學(xué)與西方科學(xué)的關(guān)聯(lián),然而,在實(shí)踐的具體意涵問題上,新儒家要么以唯識(shí)論的本心作為實(shí)踐主體溝通求善與求真(1),要么以理氣結(jié)合的道體看待實(shí)踐(2),或側(cè)重實(shí)踐主體的意志和直覺維度(3)。此種對(duì)實(shí)踐主體的觀念論建構(gòu)忽視了實(shí)踐的感性經(jīng)驗(yàn)維度,也難以解決思想的客觀性問題,使得心性主體外化的通道難以真正聯(lián)通外在物。近現(xiàn)代哲學(xué)家馮契以馬克思的主體感性活動(dòng)為建構(gòu)起點(diǎn),融通船山的能所論,兼容金岳霖的經(jīng)驗(yàn)分析之學(xué),建構(gòu)了一種中、西、馬融通的新型知行觀,對(duì)于擴(kuò)展中國(guó)傳統(tǒng)的知行觀有著啟發(fā)意義。就馮契研究本身而言,目前的研究關(guān)注其邏輯思維、理想人格、自由學(xué)說、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中國(guó)哲學(xué)化路徑等(4),較少關(guān)注其知行觀及其在當(dāng)代哲學(xué)中的思想效應(yīng)。而知行觀是中國(guó)傳統(tǒng)哲學(xué)的核心問題之一,考察其在近現(xiàn)代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可以窺見中國(guó)傳統(tǒng)哲學(xué)創(chuàng)新的可能路徑。
一、時(shí)代巨變中的近代知行觀及其困境
近代中國(guó)遭遇外敵入侵,清王朝的落后和愚昧使得近代知識(shí)分子思考民族文化如何適應(yīng)時(shí)代巨變,古今之爭(zhēng)便成了時(shí)代的核心問題。這個(gè)時(shí)期的知識(shí)分子都有以西學(xué)革除中學(xué)之弊的使命,中體西用便成為此一時(shí)期思想家的重要論題,西方理性哲學(xué)和非理性哲學(xué)紛紛在中國(guó)登場(chǎng)并與中國(guó)傳統(tǒng)哲學(xué)相結(jié)合,如馮友蘭引入邏輯經(jīng)驗(yàn)主義,李大釗引介馬克思和柏格森的哲學(xué)。在馮契看來,“凡是在中國(guó)近代史上起了積極影響的哲學(xué)家,總是善于把西方先進(jìn)思想與中國(guó)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思想結(jié)合起來,以回答現(xiàn)實(shí)問題和理論問題,從而作出了創(chuàng)造性貢獻(xiàn)”。[2]6其中,影響較大的是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思想,對(duì)二者的批判為馮契“智慧說”的出場(chǎng)提供了思想背景。
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改良派把西方的歐幾里得幾何學(xué)公理演繹方法與傳統(tǒng)哲學(xué)中孟子的“魂御體魄”(5)觀念相結(jié)合,提出“心貴于體”的知行觀。他把“心”比喻為“魂靈”、把身體說成“魄質(zhì)”,“魂靈”主要指人的知覺、印象、記憶、推理等意識(shí)活動(dòng),“魄質(zhì)”主要指人的身體活動(dòng)。對(duì)于二者關(guān)系,康有為的基本判斷是:“心有知者也,體無知者也,物無知而人有知,故人貴于物,知人貴于物,則知心貴于體矣。”[3]康有為對(duì)心貴于體的論證分為本體論、知識(shí)論和認(rèn)識(shí)論三個(gè)主要部分。
從本體論維度來看,他確立了“元”作為宇宙的本源,人在行動(dòng)之前必須認(rèn)識(shí)元。董仲舒提出“人之元乃在乎天地之前”,康有為加以深入闡發(fā),認(rèn)為在天地生成之初就已有了元,元相當(dāng)于道,也是人之神的根本,人的神(靈魂)必須以元為根本才能行事。康有為此種道在心之先的知行觀即可衍生先驗(yàn)主義的知識(shí)論。
從知識(shí)論來看,康有為的知行觀中,知識(shí)體系由“實(shí)理”和“公法”構(gòu)成,并不從行動(dòng)中產(chǎn)生。既然知識(shí)都是從元中產(chǎn)生,那么元生成知識(shí)必定有著一套系統(tǒng)的機(jī)制。康有為引入了歐幾里得幾何學(xué)體系作為元生成知識(shí)的第一套機(jī)制。歐幾里得幾何學(xué)由公理和推論構(gòu)成,“實(shí)理”就相當(dāng)于歐幾里得幾何學(xué)的公理;推論由公理產(chǎn)生,相當(dāng)于人類社會(huì)運(yùn)行的法則,即“公法”。康有為以歐幾里得幾何學(xué)的公理和推論類比人類社會(huì)的“實(shí)理”和“公法”,比如人的平等相當(dāng)于人類社會(huì)的公理,以這種公理為依據(jù),人類社會(huì)確定了法律,法律的基本信條就是公理,那么法律就是由“實(shí)理”推出的“公法”。
從認(rèn)識(shí)論看,人的認(rèn)識(shí)就是對(duì)“實(shí)理”和“公法”的認(rèn)識(shí),并不依賴行動(dòng)。康有為在《師弟門》中說:“地球既生,理即具焉,蓋既有氣質(zhì),即有紋理。人有靈魂,知識(shí)生焉,于是能將理之所在而發(fā)明之,其發(fā)明者日增一日,人立之制度亦因而日美一日。” [4]148-149由此可見,人的認(rèn)識(shí)就是對(duì)理的“發(fā)明”或認(rèn)識(shí)。同時(shí),康有為把知識(shí)認(rèn)定為理的體系,與人的行動(dòng)和活動(dòng)分離開來,人的能動(dòng)性被消解,因此,這種認(rèn)識(shí)的發(fā)生帶有一定的機(jī)械論色彩。康有為把“實(shí)理”和“公法”擬定為先驗(yàn)的、非流俗的、非常識(shí)性的觀念,最終意圖是為變法提供根據(jù)。元和理受環(huán)境的影響,可以外化為有差異性的多種現(xiàn)實(shí)觀念。然而,環(huán)境經(jīng)常灌輸給我們某種流俗的觀念,多次重復(fù)變成了我們的認(rèn)識(shí),這就是一種“常緯”;人要敢于與流俗觀念作斗爭(zhēng),他提出“人之所以異于人者,在勉強(qiáng)學(xué)問而已。夫勉強(qiáng)為學(xué),務(wù)在逆乎常緯”[4]148-149。“逆常緯”才能回歸元或“公理”,為社會(huì)確立新的“公法”。因此,“托古改制”有了認(rèn)識(shí)論的基礎(chǔ)。
改良派的保守性決定了他們的知在行先觀念,他們認(rèn)為當(dāng)時(shí)的民智沒有達(dá)到對(duì)革命積極意義的有效認(rèn)知,不能進(jìn)行革命,“三統(tǒng)”“三世”的政治道統(tǒng)在當(dāng)時(shí)人們的觀念中設(shè)定在先,一時(shí)難以改變。作為革命派的章太炎針對(duì)康有為上述思想作了針鋒相對(duì)的批判,提出了“行在知先”為核心的知行觀。章太炎把進(jìn)化論與唯識(shí)宗的認(rèn)識(shí)論、康德的先驗(yàn)論融合在一起。一方面,進(jìn)化論強(qiáng)調(diào)行動(dòng)或活動(dòng)的優(yōu)先地位,章太炎從中推演出行在知先,并用唯識(shí)宗的“八識(shí)”加以證明;另一方面,在行如何生成知的意義上,章太炎又把康德先驗(yàn)論植入唯識(shí)宗的認(rèn)識(shí)論。由此,康有為的基本論點(diǎn)是,認(rèn)識(shí)是一個(gè)先行而后知的過程,人只有吃了東西才知道食物的味道,只有聽到了東西才知道聲音。除了用自然發(fā)生的過程來論證外,他還引入了唯識(shí)宗的“五級(jí)認(rèn)識(shí)論”加以說明。
第一級(jí)是“作意則行之端矣”[5],行動(dòng)有一個(gè)主體對(duì)外在的“注意”。這種觀點(diǎn)與王陽(yáng)明的“意念發(fā)動(dòng)便是知”有相通之處。第二級(jí)和第三級(jí)分別是“觸”和“受”,即與外物接觸形成感知或感受。章太炎舉了李自成的例子加以佐證,李自成在起義之初并沒有革命的理論,在革命之后才采取了“濟(jì)世救民”的一系列舉措;因此,在不斷的行動(dòng)中,關(guān)于革命的概念、策略、方法才形成。第四級(jí)和第五級(jí)分別是“想”和“思”,由接觸形成的知覺形成對(duì)表象的認(rèn)識(shí),這一認(rèn)識(shí)被“思考”為一種概念,在概念的基礎(chǔ)上形成判斷和推理,再由判斷、推理生成更為抽象的概念,即“大共名”。章太炎非常重視抽象概念,認(rèn)為概念是我們理解萬事萬物的基礎(chǔ)。在《顏學(xué)》篇中,他認(rèn)同荀子對(duì)顏淵的批評(píng),但是也指出顏淵的問題在于忽視了“琴譜”作為一個(gè)抽象的理論具有的重要意義。
在行如何生成知的機(jī)制問題上,章太炎構(gòu)建了一種康德主義的先驗(yàn)論模型。他在《四惑論》中舉了“三飯顆”的例子:在吃飯(行動(dòng))的時(shí)候,人們產(chǎn)生了關(guān)于“飯顆”的印象,通過感性認(rèn)識(shí)上升為理性認(rèn)識(shí),這種簡(jiǎn)單的印象組合為“三飯顆”概念。組合的能力來源于主體有關(guān)于“量”的先驗(yàn)范疇;在科學(xué)認(rèn)知中也是如此,主體對(duì)實(shí)驗(yàn)和經(jīng)驗(yàn)材料的加工,背后一定有因果的“原型觀念”。這些觀念形成的認(rèn)識(shí)只是一種知性的認(rèn)識(shí),主體的先驗(yàn)統(tǒng)覺能把這種知性的認(rèn)識(shí)上升為理性認(rèn)識(shí),形成認(rèn)識(shí)對(duì)象的整體概念。顯然,章太炎的這種認(rèn)識(shí)論有著極強(qiáng)的康德先驗(yàn)論痕跡,不同的是,康德的先驗(yàn)范疇由自我的先驗(yàn)統(tǒng)覺發(fā)動(dòng)而出,而章太炎認(rèn)為這些范疇來自人本身的阿賴耶識(shí),這就帶有唯識(shí)宗的痕跡。章太炎在知識(shí)形成后添加了一個(gè)知在行先的環(huán)節(jié),當(dāng)行生成知后,主體認(rèn)識(shí)到了事物本身的必然性就可以在以后的實(shí)踐中運(yùn)用,進(jìn)而達(dá)到“庖丁解牛”的境界或知行合一的自由之境。但是,在認(rèn)識(shí)的生成維度,章太炎的主要觀點(diǎn)依然是行在知先。
改良派和革命派為倫理主體增添了形式邏輯和實(shí)踐論的維度,但也陷入了思辨哲學(xué)的泥潭,沒有走出先驗(yàn)論的圍城。改良派試圖融合西方科學(xué)思想中作為基礎(chǔ)理論的幾何學(xué)的邏輯,創(chuàng)立中西融合的認(rèn)識(shí)論,但是,“實(shí)理”和“公法”并非從現(xiàn)實(shí)中引出,而是從純粹幾何學(xué)邏輯出發(fā)的推演,帶有極強(qiáng)的思辨性,難以解決概念和對(duì)象的關(guān)系問題。對(duì)此,馮契指出,康有為的問題在于,“用形而上學(xué)的概念去推導(dǎo)和衡量對(duì)象,要求對(duì)象和概念相適應(yīng)”[2]118。也就是說,理和元只是一種科學(xué)理論意義上的核心概念,而現(xiàn)實(shí)是復(fù)雜和豐富的物質(zhì)世界,此種科學(xué)理論的懸設(shè)并不能解釋生活世界。章太炎的改良派知行觀有著類似馬克思實(shí)踐觀的萌芽,然而,在行生成知的問題上,行動(dòng)中認(rèn)識(shí)的歷史發(fā)展過程并不建立在行動(dòng)本身,理性的認(rèn)識(shí)反而由先驗(yàn)形式生成,行和知“兩者只是外在的結(jié)合。他未能以實(shí)踐為基礎(chǔ)來說明感性與理性的統(tǒng)一”[2]224。
二、以“得自”與“還治”為中心的知行觀構(gòu)建
在知和行二者間,康有為偏重知,試圖把知變成一個(gè)公理體系來指導(dǎo)行動(dòng)。章太炎則反其道而行之,把行放在知前,通過行來促進(jìn)知的形成。兩位思想家在處理這一問題上偏向了相反的兩端。不同于改良派用邏輯演繹改造傳統(tǒng)哲學(xué),也不同于革命派用進(jìn)化論與先驗(yàn)哲學(xué)改造唯識(shí)宗的認(rèn)識(shí)論,馮契給出了更為復(fù)雜的思想創(chuàng)新。金岳霖已經(jīng)用羅素的邏輯經(jīng)驗(yàn)主義改造了傳統(tǒng)哲學(xué),構(gòu)建出“得自”經(jīng)驗(yàn)和“還治”經(jīng)驗(yàn)的融合路徑。馮契的新融合路徑在于,對(duì)接馬克思的實(shí)踐本體與王船山的“境”,再把“得自”和“還治”座駕于新的實(shí)踐本體之上,使其歷史化,進(jìn)而創(chuàng)建出帶有歷史辯證法特征的新型知行觀。金岳霖提出的一個(gè)重要知識(shí)論命題是“以經(jīng)驗(yàn)之所得還治經(jīng)驗(yàn)”;馮契的創(chuàng)新在于把“經(jīng)驗(yàn)”范疇置換為“現(xiàn)實(shí)”,使得人的認(rèn)識(shí)過程呈現(xiàn)現(xiàn)實(shí)性。具體而言,認(rèn)識(shí)活動(dòng)主體通過實(shí)踐從現(xiàn)實(shí)中獲得認(rèn)識(shí),又在現(xiàn)實(shí)中發(fā)展和驗(yàn)證認(rèn)識(shí),“得自”和“還治”使得實(shí)踐活動(dòng)成為對(duì)象和主體交互作用的中介,認(rèn)識(shí)過程成為主體不斷與現(xiàn)實(shí)互動(dòng)的過程。
首先,現(xiàn)實(shí)給予實(shí)踐主體以經(jīng)驗(yàn),使得認(rèn)識(shí)“得自”現(xiàn)實(shí)。馮契對(duì)現(xiàn)實(shí)給予認(rèn)識(shí)的發(fā)生過程的認(rèn)知深受康德的影響,認(rèn)為實(shí)踐主體的先驗(yàn)統(tǒng)覺對(duì)經(jīng)驗(yàn)構(gòu)建至關(guān)重要,也體現(xiàn)了馮契深受金岳霖“經(jīng)驗(yàn)之治”的影響。馮契說:“我用判斷把事實(shí)和思想結(jié)合起來的過程,于是,我有了‘覺’。”[6]28也就是說,實(shí)踐主體的統(tǒng)覺把經(jīng)驗(yàn)材料組合成一種認(rèn)識(shí),這種組合的過程不斷“自證”和體現(xiàn)自我意識(shí)本身的能動(dòng)性,經(jīng)驗(yàn)給予和認(rèn)識(shí)建構(gòu)的過程也是實(shí)踐活動(dòng)中客體賦予主體認(rèn)識(shí)的過程。馮契的這一思想受到了毛澤東《實(shí)踐論》的影響,堅(jiān)持著馬克思的實(shí)踐決定認(rèn)識(shí)的論斷。實(shí)踐包括生產(chǎn)勞動(dòng)、階級(jí)斗爭(zhēng)、科學(xué)實(shí)驗(yàn),這是認(rèn)識(shí)的基礎(chǔ)。馮契使用了“能量”隱喻,認(rèn)為實(shí)踐過程就是能量的流動(dòng)過程,經(jīng)驗(yàn)對(duì)象的能量轉(zhuǎn)化為我的能量,能量的流動(dòng)使得經(jīng)驗(yàn)認(rèn)識(shí)形成“為我”的認(rèn)識(shí)。對(duì)此種現(xiàn)實(shí)對(duì)象對(duì)我的賦能過程,馮契給予了高度評(píng)價(jià):以實(shí)踐本體的視角來看,現(xiàn)實(shí)對(duì)主體的給予使得人生活的“歷史就被理解為那些投身于現(xiàn)實(shí)的人們的創(chuàng)造活動(dòng),實(shí)踐推動(dòng)著歷史前進(jìn),推動(dòng)著人的認(rèn)識(shí)不斷前進(jìn)”[6]58。如何理解“能量”的含義,馮契并未展開論述。既然馮契這一觀念來自馬克思的思想,那么可以用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成果加以詮釋。一些學(xué)者認(rèn)為,“馬克思是從精神和肉體的對(duì)立統(tǒng)一中理解人的”[7],那么,主體在對(duì)象化活動(dòng)中通過“得自”和“還治”與外界交換能量,精神和肉體的能動(dòng)性活動(dòng)才是能量交換的載體。
其次,實(shí)踐展開為“能”和“所”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聯(lián)結(jié)“得自”和“還治”。馮契吸納了范鎮(zhèn)的形神論,提出實(shí)踐過程就是形與神的結(jié)合,神必須以身體之形為依托。人之神具有“能”動(dòng)性,這里的“能”來自王夫之的思想。能與所關(guān)聯(lián)表現(xiàn)為主體“能”動(dòng)活動(dòng)作用于對(duì)象之所。馮契的化用在于把 “所”拓展為“境”:“作為認(rèn)識(shí)對(duì)象的 ‘所’是實(shí)有其體的,成為‘境’即對(duì)象,而‘能’就是能作用于客體而表現(xiàn)功效的,是實(shí)有其用的。”[6]61能和所互動(dòng)關(guān)系的引入把知行觀提升到了體用如一的層面。在實(shí)踐活動(dòng)中,客體給予主體經(jīng)驗(yàn)知識(shí),主體并非消極和被動(dòng)的主體,而有著指向“所”的能力,把經(jīng)驗(yàn)認(rèn)識(shí)施加于認(rèn)識(shí)對(duì)象,形成用。“體用如一”意味著認(rèn)識(shí)過程是開放式的循環(huán):從實(shí)踐活動(dòng)中獲得經(jīng)驗(yàn),再“還治”現(xiàn)實(shí)。因?yàn)楝F(xiàn)實(shí)是流動(dòng)的過程,所以認(rèn)識(shí)活動(dòng)和實(shí)踐的對(duì)象化活動(dòng)也是流動(dòng)的。“得自”現(xiàn)實(shí)的認(rèn)識(shí)又“還治”現(xiàn)實(shí),對(duì)客體的經(jīng)驗(yàn)性認(rèn)識(shí)可以通過主體活動(dòng)進(jìn)行驗(yàn)證,驗(yàn)證又確證或修正了主體活動(dòng),如此往復(fù)。
“得自”與“還治”的融合還表現(xiàn)為“思”和“位”在歷史中的交互作用。既然知和行是能所如一的關(guān)系,那么,“能”所在的主體之思與位代表的現(xiàn)實(shí)“情境”也融合在一起。在歷史的流動(dòng)中,思的不斷演進(jìn)與位的不斷變化也契合在一起。歷史具體情境中形成的特定認(rèn)知又在另一歷史情境的流動(dòng)中得到驗(yàn)證、修正和生活。因此,人的認(rèn)知從感性認(rèn)識(shí)上升為理性認(rèn)識(shí),呈現(xiàn)螺旋式上升的態(tài)勢(shì)。這就在歷史層面完成了“得自”和“還治”的呼應(yīng)和流變。馮契也在這一意義上回應(yīng)了不可知論的問題,他指出,對(duì)于感覺的內(nèi)容和外在事物之間的關(guān)系,“不可知論者認(rèn)為不可比較,實(shí)踐證明可以比較,可以達(dá)成一致,感覺能夠把握客觀實(shí)在”[8]。
最后,“得自”和“還治”賦予主體反思和認(rèn)識(shí)更新以可能性,反思提升自我意識(shí)的境界,打通了知識(shí)和智慧。馮契“智慧說”的特色在于行與知不是單一的感性活動(dòng)過程,而是從知識(shí)到智慧的轉(zhuǎn)化過程,轉(zhuǎn)化的可能性在于自我意識(shí)有著從“自在”轉(zhuǎn)換為“自為”的能力。馮契承認(rèn)他的這一思想受到了黑格爾和馬克思的影響。在黑格爾的辯證法看來,自在狀態(tài)的特點(diǎn)是自身的潛在性沒有展開,與他物分離,沒有意識(shí)到自身;而到了自為階段,主體在他物中反思,回到自身的存在。馮契認(rèn)為,人在實(shí)踐過程中獲得認(rèn)識(shí)可以由自在性的認(rèn)識(shí)進(jìn)展到自為性的認(rèn)識(shí);在自為階段,自在之物變成了為我之物,自我在與他物的中介關(guān)系中成為感知到“整全世界”的自我,知和行也在更高的智慧層面得到了統(tǒng)一。對(duì)于知行關(guān)系的自為性關(guān)系,馮契用庖丁解牛的案例作了深入解釋。
“庖丁解牛”展現(xiàn)了知行關(guān)系的三層境界。其一是自由境界,庖丁認(rèn)識(shí)到了牛身體結(jié)構(gòu)的規(guī)律,用規(guī)律來解牛,解的純熟性使得屠牛行為擺脫了外在強(qiáng)制,獲得了駕馭必然之后的自由感。馮契把自由感作為自為階段的根基,他特別強(qiáng)調(diào)“人的自由勞動(dòng)是在人與自然、主體和對(duì)象的交互作用中發(fā)展起來的。人的自由是憑著相應(yīng)的對(duì)象、相應(yīng)的為我之物而發(fā)展起來的。人天生并不自由,但在化自在之物為為我之物的過程中,人由自在而自為,越來越獲得自由”[9]。其二是樂生境界,解牛過程中,庖丁的精神異常飽滿,勞動(dòng)本身也不再是負(fù)擔(dān),而成為庖丁的樂趣,這是一種高維度的生活境界即樂生。其三是美學(xué)境界,庖丁的解牛過程是純熟之知和自由之行高度融合的過程,因而可以展現(xiàn)美,契合音樂和舞蹈的節(jié)拍。
在知行觀的智慧層面,馮契把傳統(tǒng)哲學(xué)的智慧與西方哲學(xué)、馬克思的實(shí)踐論融為一體。“得自”和“還治”的動(dòng)態(tài)歷史過程打通了(西方的)知識(shí)和(中國(guó)傳統(tǒng)的)智慧,其中介的載體是馬克思的對(duì)象化活動(dòng)或?qū)嵺`。馮契引用了馬克思《1844年經(jīng)濟(jì)學(xué)哲學(xué)手稿》中的“蜜蜂隱喻”加以說明。馬克思認(rèn)為,蜜蜂只是運(yùn)用自己的身體來建構(gòu)巢穴,世代遺傳這一本能;而人可以把自我的尺度附著于對(duì)象,使得對(duì)象成為“為我的對(duì)象”,這就為知行境界的提升提供了可能。對(duì)于人的此種對(duì)象化活動(dòng),學(xué)界一般的認(rèn)定是,“主體在改造對(duì)象客體的同時(shí)也改造了主體自身,實(shí)現(xiàn)了主體的目的意圖”[10]。以此來看,既然行動(dòng)本身就是能動(dòng)自我與外界經(jīng)驗(yàn)的互塑,那么在外在經(jīng)驗(yàn)世界中獲得的認(rèn)識(shí)又會(huì)回到對(duì)自我的認(rèn)識(shí)上,實(shí)踐活動(dòng)就把自在和自為聯(lián)系在一起了,也為人在行動(dòng)中獲得自由感、樂生感、藝術(shù)感提供了可能性。
就現(xiàn)實(shí)意義而言,馮契的知行觀不但以“得自”和“還治”聯(lián)結(jié)了人與世界,而且用實(shí)踐融合知識(shí)和智慧,有著很強(qiáng)的現(xiàn)實(shí)和理論意義。從現(xiàn)實(shí)層面來看,后現(xiàn)代思想家對(duì)生活的透視,是“商品世界的交換原則……將主體變成了計(jì)算理性的主體,那么主體也便物化了” [11]。馮契以智慧為導(dǎo)向的知行觀立足現(xiàn)實(shí)實(shí)踐場(chǎng)域,取向自為的境界,直面當(dāng)下生活的異化難題,用自由感、樂生和美給出了人在世俗生活中的超越感,對(duì)克服現(xiàn)代社會(huì)的物象化問題具有積極意義。從理論意義來看,傳統(tǒng)理學(xué)的“概念結(jié)構(gòu)由‘天—理’‘性—理’‘仁—理’三個(gè)層面依次展開”[12],但是,三個(gè)層面與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系依然用邏輯中介“理一分殊”來統(tǒng)合;而馮契以“得自”與“還治”相結(jié)合的知行觀把理與天、性、仁統(tǒng)合于行動(dòng)中,理、主體、現(xiàn)實(shí)生活三者的結(jié)合將更為徹底,可以更為有效地解釋天理和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系。
三、馮契后學(xué)的兩種推進(jìn)路徑
“得自”和“還治”相結(jié)合的知行觀對(duì)以往的知行觀是一種根本性突破。改良派的“公理”和“公法”有形而上學(xué)的痕跡,把理念化的概念運(yùn)用于行動(dòng)的做法帶有機(jī)械論傾向,會(huì)導(dǎo)致主體陷入僵化的行動(dòng)中。革命派注重了在行中形成知識(shí),在“觸”和“覺”中形成感性知識(shí),這保證了知識(shí)“得自”現(xiàn)實(shí);但是,問題在于,在“還治”現(xiàn)實(shí)的過程中,純熟境界的知可以指導(dǎo)行,而非純熟境界的知并不能有效指導(dǎo)行。因此,革命派的“得自”和“還治”依然是分裂的;而改良派只有“還治”,沒有“得自”。對(duì)此,馮契對(duì)知行觀的創(chuàng)新在于,用感性活動(dòng)聯(lián)結(jié)“得自”與“還治”,形成良性循環(huán),進(jìn)一步匯通中西的本體論,打通西方的知識(shí)論與中國(guó)傳統(tǒng)哲學(xué)的智慧。在馮契后學(xué)那里,這一中國(guó)傳統(tǒng)哲學(xué)的創(chuàng)新進(jìn)路拓展為實(shí)驗(yàn)性探究與具體的形而上學(xué)。
第一,“得自”和“還治”的結(jié)合使得知和行在實(shí)踐中互相賦予意義,此種交互作用的機(jī)制延展為以實(shí)驗(yàn)探究為主導(dǎo)的哲學(xué)觀。在馮契那里,“得自”和“還治”是行動(dòng)的兩個(gè)環(huán)節(jié)。那么問題在于,如果“得自”和“還治”以實(shí)踐為核心進(jìn)行聯(lián)結(jié),實(shí)踐如何聯(lián)結(jié)“得自”和“還治”?這一問題在馮契那里并未深入探討。郁振華引入杜威的實(shí)用主義深入思考這一問題,用實(shí)用主義的實(shí)驗(yàn)性探究方法擴(kuò)展馮契的知行觀。
在西方哲學(xué)視域中,知行觀的源頭是亞里士多德提出的三種知識(shí):理論知識(shí)、實(shí)踐知識(shí)和技藝知識(shí),其中技藝知識(shí)是較低層次的知識(shí)。杜威深受實(shí)驗(yàn)科學(xué)的影響,把技藝知識(shí)提升到了與理論知識(shí)和實(shí)踐知識(shí)同樣的高度。技藝其實(shí)就是科學(xué)方法中的實(shí)驗(yàn)方法,遵循三個(gè)基本原則:其一,實(shí)驗(yàn)必然受到一些觀念和問題的指導(dǎo),觀念和問題構(gòu)成了實(shí)驗(yàn)探究的基本論域;其二,實(shí)驗(yàn)行動(dòng)的結(jié)果是一種生成性的活動(dòng),問題和觀念不是不變的,會(huì)隨著實(shí)驗(yàn)行動(dòng)進(jìn)入新情境而發(fā)生改變;其三,實(shí)驗(yàn)過程中出現(xiàn)不斷變動(dòng)的要素修正著研究對(duì)象本身。這三種原則不斷交互、修正,對(duì)此,杜威認(rèn)為:“在指導(dǎo)下的活動(dòng)所得到的結(jié)果,構(gòu)成了一個(gè)新的經(jīng)驗(yàn)情境,而這些情境中對(duì)象之間彼此產(chǎn)生了不同的關(guān)系,并且在指導(dǎo)下從事活動(dòng)的后果形成了具有被認(rèn)知的特性的對(duì)象。”[13]
如果說馮契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哲學(xué)作了本體論層面上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那么其后學(xué)郁振華則進(jìn)一步把西學(xué)最新的實(shí)驗(yàn)性探究方法融入了馮契的知行觀。馮契的知行觀打通知識(shí)和智慧的方法在于發(fā)掘中國(guó)哲學(xué)傳統(tǒng)的知識(shí)論,使之與西方的邏輯性知識(shí)對(duì)接,再與智慧融合。具體而言,馮契融貫西方的邏輯性知識(shí)發(fā)掘了中國(guó)傳統(tǒng)哲學(xué)中墨家的“故、理、類”的邏輯思想。也就是說,中國(guó)古代已有一定的實(shí)證知識(shí)觀的萌芽,有學(xué)者認(rèn)為“中國(guó)古代邏輯的文化實(shí)踐取向主要在于人文社會(huì)知識(shí)的確證” [14]。郁振華進(jìn)一步將知行與知識(shí)和智慧的實(shí)踐性融合機(jī)制深化到實(shí)驗(yàn)性探究過程中,放置“得自”與“還治”的互動(dòng)在更為具體的探究問題場(chǎng)域中。此種創(chuàng)新有著三個(gè)維度的要旨。
其一,知和行處于探究性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中。“訴諸外在行動(dòng),通過變革所考察的事物或事物與我們的關(guān)系來認(rèn)識(shí)事物,是實(shí)驗(yàn)探究的首要特點(diǎn)。”[15]對(duì)事物的考察在人與物的關(guān)系中生成,這不是消極的被動(dòng)的知識(shí)論,而是認(rèn)知在能動(dòng)活動(dòng)中不斷推進(jìn)的知識(shí)論;推動(dòng)環(huán)境變革的實(shí)踐又會(huì)產(chǎn)生新的認(rèn)識(shí),新的認(rèn)識(shí)再施于實(shí)踐。其二,知行關(guān)系中行是可以生成知識(shí)的操作。在實(shí)驗(yàn)性探究中,行動(dòng)就是操作,這是知識(shí)成立的前提。“杜威在承認(rèn)符號(hào)操作和物理操作的差異的前提下,強(qiáng)調(diào)了后者的根源性,以此對(duì)實(shí)驗(yàn)探究的實(shí)踐/行動(dòng)品格作了有力的論證。”[15]其三,知識(shí)在實(shí)驗(yàn)性行動(dòng)的探究中被建構(gòu)出來,探究過程帶有康德式建構(gòu)主義意味。在康德那里,先驗(yàn)范疇在先驗(yàn)統(tǒng)覺作用下可以建構(gòu)經(jīng)驗(yàn)材料,范疇具有絕對(duì)性和固定性,同時(shí)又具有構(gòu)成性,是構(gòu)建知識(shí)、形成經(jīng)驗(yàn)的重要前提。同樣,實(shí)驗(yàn)性探究過程建立在一定的懸設(shè)之上,可以變動(dòng)的假設(shè)條件相當(dāng)于康德的先驗(yàn)范疇,對(duì)經(jīng)驗(yàn)具有一定的構(gòu)成作用。不同之處在于,郁振華所說的這種假設(shè)可以驗(yàn)證,也可以被推翻和重建,然而康德的范疇是固定不變的。
顯然,實(shí)驗(yàn)性探究方法的介入可以解決馮契的知行觀尚未解決的問題,即“得自”和“還治”的螺旋上升如何可能。“得自”和“還治”只是主體在探究性實(shí)踐中的一個(gè)環(huán)節(jié),這個(gè)環(huán)節(jié)的認(rèn)識(shí)要進(jìn)入下一環(huán)節(jié),下一個(gè)環(huán)節(jié)的實(shí)踐會(huì)更為深入地建構(gòu)出認(rèn)識(shí)的對(duì)象,以此“還治”向“得自”的逆向螺旋式上升過渡成為可能。“得自”現(xiàn)實(shí)的認(rèn)識(shí)并非都有效,有效性檢驗(yàn)本身使得“得自”在“還治”維度上發(fā)生改變,這種逆向的過渡使得認(rèn)識(shí)具有上升的可能性。如此,行中的主客關(guān)系是過程性關(guān)系,知識(shí)在人與物的“打交道”中形成和改變。
第二,“得自”和“還治”的融通使得主客之間的深度結(jié)合成為可能,開啟了一種具體形而上學(xué)論域。馮契的“得自”和“還治”其實(shí)是行動(dòng)與經(jīng)驗(yàn)的無限上升循環(huán),這種循環(huán)過程中蘊(yùn)含著四種認(rèn)識(shí)界分:本然界、事實(shí)界、可能界和價(jià)值界。本然界是人類活動(dòng)未參與的自在自然界。在人類的活動(dòng)參與之后,在世界中形成的認(rèn)識(shí)有自我,這種認(rèn)識(shí)便是“事實(shí)”,由此,人類進(jìn)入了事實(shí)界,實(shí)踐過程中人類的知性認(rèn)識(shí)上升為辯證的認(rèn)識(shí),不斷把握世界的必然性。事實(shí)界有著人的活動(dòng)的參與,活動(dòng)帶有人的欲望和需要,這就決定了人的行動(dòng)指向的世界是可能世界,所以事實(shí)界本身就是可能界。可能性的行動(dòng)除了改造世界之外,還帶有副產(chǎn)品,即產(chǎn)生了人的價(jià)值,這種價(jià)值包含行動(dòng)的自由感和德性,從而形成價(jià)值界。
馮契關(guān)于“四界”的觀點(diǎn)是對(duì)傳統(tǒng)知行觀的進(jìn)一步深化,但是也產(chǎn)生了一個(gè)問題:事實(shí)界與價(jià)值界可以通過實(shí)踐活動(dòng)“扭合”在一起,但是融合的機(jī)制只是對(duì)象性活動(dòng)及其效應(yīng),對(duì)象性活動(dòng)貫通價(jià)值界的方式還是黑格爾意義上的“反思”,還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精神性。在楊國(guó)榮那里,進(jìn)一步貫通的中介是“成”和“事”。楊國(guó)榮把海德格爾的存在論與中國(guó)傳統(tǒng)哲學(xué)的“體用不二”內(nèi)涵相結(jié)合,用“成”貫通物和人,在激發(fā)物的潛能的同時(shí),認(rèn)識(shí)和成就自己。“事”不但有著對(duì)象性活動(dòng)的參與,而且關(guān)乎人的“情意”,更能貫通事實(shí)界和價(jià)值界。對(duì)于楊國(guó)榮的具體形而上學(xué)的建構(gòu),郁振華認(rèn)為“金(岳霖)、馮(契)兩位先生基本上沒有在方法論層面上討論建構(gòu)形上學(xué)的這一進(jìn)路。方法論的反思,是后設(shè)的(meta-)、第二序 (second order)的反思。楊國(guó)榮通過將其與抽象形態(tài)的形上學(xué)相對(duì)照,把這一進(jìn)路彰顯出來了”。[16]如果說“得自”和“還治”還是實(shí)踐過程中縱向的歷史序列中的環(huán)節(jié)的話,那么楊國(guó)榮的方法論建構(gòu)就是橫向和縱向相結(jié)合的理論策略:“成物”和“成己”是特定時(shí)間情境中互動(dòng)的要素,也是時(shí)間序列中交互、互生的兩個(gè)要素。
“成物”和“成己”將知行關(guān)系界定為人與世界互相賦予意義的過程。在具體形而上學(xué)論域中,楊國(guó)榮把馮契的“需要”和“價(jià)值”等概念上升為意涵更為豐富的“意義”,再分為“認(rèn)知義”和“價(jià)值義”。具體而言,行動(dòng)本身是主體通過心體賦予外在世界意義的過程,主體的認(rèn)知和價(jià)值外化為現(xiàn)實(shí),在外化過程中,主體通過反思返回自身。這種返回類似黑格爾的在肯定和否定中螺旋上升的“自我持存式辯證法”[17]。返回或上升過程中,主體發(fā)生了肯定和否定并存的揚(yáng)棄性精神活動(dòng)。揚(yáng)棄的過程中,世界向人敞開,賦予主體新的意義。在不斷的行動(dòng)中,達(dá)成了人與世界的統(tǒng)一。
“成物”和“成己”融通了事實(shí)和價(jià)值,由“事”聯(lián)結(jié)在一起。馮契繼承了康德關(guān)于“經(jīng)驗(yàn)” “所予”被主體“統(tǒng)覺”構(gòu)建的論斷,楊國(guó)榮的推進(jìn)在于把“所予”認(rèn)定為事實(shí)的起點(diǎn)并與價(jià)值再融合。“所予”意味著世界并沒有宗教所認(rèn)可的“彼岸”,也沒有嚴(yán)格的主客二分,生活世界只有一個(gè)世界,“所予”代表的事實(shí)界與價(jià)值界本身就是統(tǒng)一的。那么,價(jià)值界和事實(shí)界如何聯(lián)結(jié)?楊國(guó)榮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用“事”連接起來,“事”是人行動(dòng)的“事”,是動(dòng)詞。“事”之所以具有聯(lián)結(jié)價(jià)值和事實(shí)的功能,是因?yàn)椤啊隆c存在和生成的聯(lián)系展開于更為內(nèi)在和深沉的層面。在現(xiàn)實(shí)的世界中,事物既呈現(xiàn)為實(shí)際的存在,又處于生成的過程之中,兩者的這種關(guān)聯(lián),乃是通過‘事’而建立起來”[18]。
“事”的哲學(xué)是一種新型的具體形而上學(xué),把馮契以實(shí)踐為本體的創(chuàng)新提升到更為具體的“事”,將馮契的知行觀提升到生成論的高度。“事”作為不斷生成中的活動(dòng),不斷形成和確認(rèn)認(rèn)識(shí),認(rèn)識(shí)回溯的過程也是人的意義生成過程,這是知行關(guān)系第一層級(jí)的內(nèi)在互動(dòng)關(guān)系。“事”的不斷進(jìn)展使得人與世界的意義關(guān)系不斷升華,人行動(dòng)的自由感由此生成,同時(shí)人的德性也在處理人與人之間關(guān)系的“事”中得到形成,這是知行觀的第二層內(nèi)在互動(dòng)。兩層互動(dòng)內(nèi)在地融合了人與物,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人的異化問題,從本體論的高度深度解決了人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意義問題,可以從深層解決“當(dāng)代人面對(duì)的抽象虛無主義困境”[19]。
四、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哲學(xué)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的方法啟示
關(guān)于中國(guó)傳統(tǒng)哲學(xué)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學(xué)界的一般共識(shí)是,“由于‘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在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社會(huì)制度、意識(shí)形態(tài)等多方面存在差異,發(fā)端、生成于‘傳統(tǒng)社會(huì)’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迫切需要結(jié)合時(shí)代所需對(duì)其進(jìn)行新的詮釋和解讀”[20]。近代以來,學(xué)術(shù)界對(duì)這一“新詮釋”或轉(zhuǎn)化作了多次嘗試。改良派以知先行后割裂認(rèn)知和行動(dòng)的主體,革命派雖然強(qiáng)調(diào)行動(dòng)在先,但是在行如何生成知的問題上陷入了康德主義式先驗(yàn)論。因此,在知行問題上,先前的研究要么分裂主體為二元結(jié)構(gòu),要么陷入先驗(yàn)論。而馮契的知行觀以感性活動(dòng)貫通知和行,避免了二元論陷阱,并用“得自”和“還治”的歷史過程深度融合知和行,較好地解決了行動(dòng)和認(rèn)知的客觀性問題。進(jìn)一步來說,馮契知行觀的意義還在于給出儒家哲學(xué)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的一條較為有效的路徑。如前所述,新儒家的一個(gè)重要任務(wù)是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倫理主體,以與邏輯性科學(xué)知識(shí)相融合。不管是“新理學(xué)”以“正”(理性)“負(fù)”(神秘感性)方法通達(dá)“理”,還是新唯識(shí)論的“性修不二”,都把倫理的主體轉(zhuǎn)化為意志的主體,難以真正通達(dá)外在世界的經(jīng)驗(yàn)知識(shí)。馮契的實(shí)踐性主體可以規(guī)避以上轉(zhuǎn)化方法的問題,達(dá)成一種更為有效的轉(zhuǎn)型。
馮契及其后學(xué)從本體論和方法論兩個(gè)維度給出了中國(guó)傳統(tǒng)哲學(xué)轉(zhuǎn)型的可能路徑。
其一,從傳統(tǒng)哲學(xué)轉(zhuǎn)型的本體論來看,傳統(tǒng)的心性或倫理主體面臨西方知識(shí)論的挑戰(zhàn),馮契將能和所“扭合”在行動(dòng)中,中國(guó)傳統(tǒng)的心性主體和西方知識(shí)主體更能兼容和融合為一。心性主體更傾向于覺知和體認(rèn),西方哲學(xué)知識(shí)主體側(cè)重經(jīng)驗(yàn)建構(gòu)。能指向所彰顯了主體的能動(dòng)性,對(duì)象性活動(dòng)的對(duì)象化聯(lián)結(jié)著主體和經(jīng)驗(yàn)對(duì)象,為覺知和客觀經(jīng)驗(yàn)的融合提供載體;實(shí)驗(yàn)性探究和“事”的學(xué)說則從探究方法與“情意”的高度將心性主體和知識(shí)主體從機(jī)制層面結(jié)合起來。另外,實(shí)踐中的“思”和“位”賦予效驗(yàn)客觀知識(shí)和倫理覺知以可能性,使得轉(zhuǎn)化路徑更具經(jīng)驗(yàn)有效性。“思”和“位”分別涉及了實(shí)踐的主體向度和客體向度,在行動(dòng)的過程中,“得自”現(xiàn)實(shí)的認(rèn)識(shí)可以在“還治”中得到驗(yàn)證和演進(jìn),其思想效果超越了單純的倫理主體,成為更具經(jīng)驗(yàn)有效性的歷史主體。
其二,從傳統(tǒng)哲學(xué)轉(zhuǎn)型的方法論來看,馮契之所以能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哲學(xué)作出影響后世的創(chuàng)新,原因在于他深諳時(shí)代精神的精華。當(dāng)時(shí)時(shí)代的哲學(xué)精華是毛澤東的實(shí)踐唯物主義,馮契對(duì)毛澤東《實(shí)踐論》等著作心悅誠(chéng)服,堅(jiān)定“沿著實(shí)踐唯物主義辯證法的道路前進(jìn),吸取各種哲學(xué)派別的合理因素”[6]10,以馬克思主義的實(shí)踐觀對(duì)勘王船山的“境”,吸納金岳霖的實(shí)證知識(shí)論,深入開掘墨家的“理”“故”“類”,打通知識(shí)和智慧。其后學(xué)也有融貫中西的學(xué)術(shù)自覺,他們沿著馮契的研究路徑,吸納杜威的實(shí)驗(yàn)性探究方法,揚(yáng)棄海德格爾的存在論方法,開拓出具有中國(guó)氣派的智慧論。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是“文化主體性的時(shí)代展現(xiàn)和創(chuàng)造文明新形態(tài)實(shí)踐的智慧展示”[21]。馮契的創(chuàng)新從主體入手,以實(shí)踐為載體,“中和”傳統(tǒng)哲學(xué)范疇,“得自”和“還治”的策略融通了中國(guó)傳統(tǒng)哲學(xué)與帶有實(shí)證和形而上學(xué)傾向的西方哲學(xué),或許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的相關(guān)研究有所啟示。
注釋:
(1)熊十力與張東蓀的書信來往表明,熊十力面對(duì)中學(xué)的求善與西學(xué)的求真問題,選擇了反己自修的方法進(jìn)行融合:“一切知識(shí)皆是稱體起用,所謂左右逢源是也。”(熊十力:《熊十力全集(4)》,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頁(yè))“自修”和“稱體”的核心方法就是修煉本心。
(2)在馮友蘭看來,理是萬物的本源,理表現(xiàn)為陰陽(yáng)二分,其體為無極,其用為太極,體用結(jié)合為道體,實(shí)踐的主體可以逐步趨向道體。(馮友蘭:《三松堂全集(4)》,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頁(yè))
(3)梁漱溟引入了柏格森的意志論,認(rèn)為生命體驗(yàn)有著綿延的歷史維度,認(rèn)識(shí)生命需要從直覺出發(fā)。這種認(rèn)識(shí)論雖然看到了認(rèn)識(shí)的歷史過程性,但也消解了實(shí)踐主體的物質(zhì)性。(梁漱溟:《梁漱溟全集(1)》,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06頁(yè))
(4)晉榮東多從馮契對(duì)墨家邏輯思想的推進(jìn)視角研究馮契的思想(晉榮東:《從歷史研究到理論創(chuàng)造——論馮契對(duì)后期墨家“三物”論說的創(chuàng)造性詮釋》,《哲學(xué)分析》2021年第4期,第51-68頁(yè)),王向清的系列研究側(cè)重馮契學(xué)說對(duì)馬克思主義價(jià)值觀、理想觀等維度的推進(jìn)(王向清、王思:《馮契對(duì)馬克思主義價(jià)值理論的開拓性探索》,《倫理學(xué)研究》2023年第5期,第47-54頁(yè)),也有學(xué)者通過對(duì)臧宏的訪談深度詮釋馮契的自由觀(韓旭、臧宏:《馮契人學(xué)自由觀研究——臧宏教授訪談錄》,《思想與文化》2020年第1期,第353-367頁(yè)),有些學(xué)者從理想人格與現(xiàn)代性關(guān)系來凸顯馮契理想人格思想的革命性意義(賀曦:《理想人格的現(xiàn)代訴求——試論馮友蘭與馮契的理想人格學(xué)說》,《天府新論》2011年第3期,第26-30頁(yè))。
(5)《孟子·告子上》認(rèn)為“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也就是說要先把心立起來,其他部分就不會(huì)陷入迷途。康有為從這一思想引出的是“魂御體魄”論。
參考文獻(xiàn):
[1]林安梧.儒學(xué)革命:從《新儒學(xué)》到《后儒學(xué)》[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1:41.
[2]馮契.馮契文集:中國(guó)近代哲學(xué)的革命進(jìn)程(第七卷)[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6.
[3]康有為.康有為全集(第二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392 .
[4]康有為.康有為全集(第一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460.
[6]馮契.馮契文集:認(rèn)識(shí)世界和認(rèn)識(shí)自己(第一卷)[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6.
[7]王曉升,趙亭亭.馬克思道德觀基礎(chǔ)新論——精神和肉體關(guān)系視角下的馬克思“道德論”與“反道德論”[J].廈門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3 (6):1-11.
[8]馮契.馮契文集:邏輯思維的辯證法(第二卷)[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6:38 .
[9]馮契.馮契文集:人的自由和真善美(第三卷)[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6:8 .
[10]林默彪.馬克思?xì)v史觀的總體性思想:一種隱性的歷史分析框架[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4(8):42-58.
[11]李乾坤.對(duì)主體的探尋:國(guó)外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的一個(gè)核心問題[J].內(nèi)蒙古社會(huì)科學(xué),2023(3): 74-81.
[12]田寶祥.“天—理”“性—理”與“仁—理”——從《四書章句集注》看朱子理學(xué)的概念結(jié)構(gòu)[J].江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3(2):106-116.
[13][美]約翰·杜威.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第四卷)[M].傅統(tǒng)先,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5:71.
[14]張學(xué)立,張存建.中國(guó)古代邏輯的文化實(shí)踐取向及當(dāng)代價(jià)值——知識(shí)論視角的證明[J].江淮論壇,2023(4):33-40.
[15]郁振華.沉思傳統(tǒng)與實(shí)踐轉(zhuǎn)向——以《確定性的追求》為中心的探索[J].哲學(xué)研究, 2017(7):107-115.
[16]郁振華.具體的形上學(xué):金-馮學(xué)脈的新開展[J].哲學(xué)動(dòng)態(tài),2013(5):36-45.
[17]代利剛.論赫爾穆特·萊希爾特對(duì)歷史辯證法的新黑格爾式闡釋[J].江淮論壇,2023(1):73-80.
[18]楊國(guó)榮.存在與生成:以“事”觀之 [J].哲學(xué)研究,2019(4):42-51.
[19]代利剛.加速社會(huì)中的傳播媒介與虛無主義:解蔽及超越[J].蘇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3(4):22-30.
[20]陸衛(wèi)明.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與科學(xué)社會(huì)主義價(jià)值觀主張高度契合的邏輯向度[J].探索,2024(3):127-141.
[21]吳滿意,楊榮所.深刻把握“兩個(gè)結(jié)合”的多重意蘊(yùn)[J].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xué)與研究,2024(2):9-15.
(責(zé)任編輯 吳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