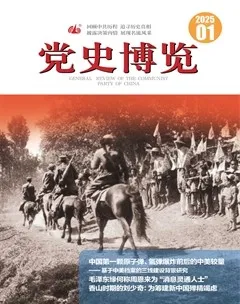中央印刷廠的榮與辱
中央印刷廠,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印刷局直屬國有企業(yè),也是中央政府規(guī)模最大、收入較高的印刷廠之一。自成立以后,它既為宣傳黨和蘇維埃政策、增加政府稅收、支援革命戰(zhàn)爭作出了突出貢獻(xiàn),又為中央蘇區(qū)的干部群眾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斗爭提供了反面教材,教訓(xùn)深刻,令人警醒。
沿革:中央印刷廠的光輝歷程
中央印刷廠,全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印刷廠。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瑞金葉坪成立后,中央印刷廠也在葉坪下陂塢村正式成立。
據(jù)曾在中央印刷廠工作過的鐘久昌、鐘明星、朱先林及知情人朱炳生、肖易生等老人回憶,中央印刷廠的創(chuàng)辦,經(jīng)歷了一個艱辛的歷程。中央印刷廠最早是在興國縣的古龍岡創(chuàng)辦的,后搬遷到寧都縣的青塘村。1931年農(nóng)歷八月十六日(公歷9月27日),又搬遷至瑞金縣葉坪下陂塢村。1933年7月,為了防備敵機空襲,中央印刷廠又遷入沙洲壩臘犁督下村。1934年七八月間,原駐在沙洲壩的中央機關(guān)被國民黨特務(wù)發(fā)現(xiàn),為安全起見,中央政府決定,所有機關(guān)全部轉(zhuǎn)移至較為隱蔽的瑞金云石山一帶,分散駐在附近各個村莊,中央印刷廠也隨機關(guān)搬至云石山沿壩新屋家村。中央主力紅軍長征時,中央印刷廠一部分工作人員隨軍長征,留下的人員和印刷設(shè)備便轉(zhuǎn)移到于都縣桐樹坪村。1934年11月后,中央蘇區(qū)的全部縣城陷入敵手,中央印刷廠被迫停止工作。1935年1月,全廠工作人員和工人奉命掩埋印刷設(shè)備,并被編入地方游擊隊,開始分散開展游擊戰(zhàn)爭。
當(dāng)時,由于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qū)實行軍事“圍剿”和經(jīng)濟封鎖,根據(jù)地經(jīng)濟建設(shè)困境重重,直至1934年春,全蘇區(qū)的國家工礦企業(yè)僅有32家。其中較大的國有印刷企業(yè),主要有中央印刷廠、《青年實話》印刷所、中央教育部印刷所、中央財政部印刷所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印刷所等,規(guī)模最大的印刷廠,當(dāng)數(shù)中央印刷廠。該廠由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出資,廠址位于葉坪下陂塢村一棟謝氏民房里。全廠有工人100多人,最多時達(dá)200人左右;有鉛印機器5部,設(shè)備雖然陳舊但較齊全;分工也較細(xì),下設(shè)鉛印、石印、排字、編輯、刻字、裁紙、裝訂、鑄字等8個生產(chǎn)部門,另有總務(wù)、材料和財會等3個行政管理處室,還成立了黨、團支部和工會組織。“一蘇”大會后,該廠的主要任務(wù),就是承擔(dān)中共蘇區(qū)中央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全總蘇區(qū)中央執(zhí)行局、少共中央局聯(lián)合機關(guān)報《紅色中華》,中共蘇區(qū)中央局機關(guān)刊物《斗爭》,全總蘇區(qū)中央執(zhí)行局機關(guān)刊物《蘇區(qū)工人》等報刊,以及中央重要文告及部分重要革命圖書、傳單,蘇維埃紙幣、公債券、米谷票、郵票等印刷任務(wù)。
由于戰(zhàn)爭環(huán)境殘酷,中央印刷廠的負(fù)責(zé)人調(diào)整頻繁。1931年11月剛成立時,中央印刷廠由陳祥生任廠長;同年底,陳祥生奉調(diào)中央造幣廠后,由原副廠長楊其鑫接任廠長。1934年春,楊其鑫被調(diào)離,印刷廠改由古遠(yuǎn)來繼任廠長。同年10月,印刷廠部分人員隨軍長征后,則先后由鄒武、朱榮生等接任廠長。以上這些中央印刷廠的掌門人,在硝煙戰(zhàn)火中,帶領(lǐng)全廠干部職工,克服各種難以想象的困難,圓滿完成了各種印刷任務(wù),踴躍參加蘇維埃政府組織的各種活動,為革命作出了積極貢獻(xiàn),成為中央蘇區(qū)的“明星企業(yè)”,受到黨和蘇維埃政府的嘉獎。楊其鑫、朱榮生等人,還曾在“二蘇”大會上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出版局局長張人亞,也被選為中央工農(nóng)檢察委員會委員,后因公殉職于“瑞金赴長汀路上”,其事跡曾被《紅色中華》登報表揚。
紅榜:中央印刷廠工人勞動熱情空前高漲
中央印刷廠工人為適應(yīng)戰(zhàn)爭的需要,以火一般的工作熱情,克服一切難以想象的艱難險阻,千方百計努力增加生產(chǎn)。據(jù)《紅色中華》報道,中央印刷廠“所定的生產(chǎn)計劃,全廠各部現(xiàn)在都超過了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甚至有個別部門的同志,超過了百分之四十以上。特別是裝訂部,在最近為要適應(yīng)戰(zhàn)爭環(huán)境的需要,該部工友自動起來每天多做一小時的義務(wù)工,并定出了一月的沖鋒計劃”。同時,中央印刷廠還經(jīng)常舉辦各種勞動競賽,經(jīng)過大家評比后,選出模范工人,但當(dāng)選模范工人不發(fā)獎金,只獎帽子或衣服等日常生活用品,并且繡上“模范工人”字樣,以資鼓勵。由于中央印刷廠工人的勞動熱情十分高漲,《紅色中華》曾以《中央印刷廠工友的積極》為題,表揚“中央印刷廠的工友平常對于參加革命戰(zhàn)爭,提高生產(chǎn)非常積極”,“每天提前上班,想方設(shè)法增產(chǎn)節(jié)約”,受到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央印刷局的充分肯定。
為了爭創(chuàng)一流的工作,在條件艱苦、設(shè)備簡陋的情況下,中央印刷廠工人積極響應(yīng)中央人民委員會關(guān)于開展節(jié)省運動的號召,以實際行動支援前方戰(zhàn)事,其事跡多次被《紅色中華》報道。如1931年報道該廠曾組織了一個工人消費合作社,工人們表示“愿將紅利里面提出百分之十的獎勵金”,“都拿來幫助紅軍戰(zhàn)費”。1932年1月,中央印刷局的印刷工人(指中央印刷局直屬的中央印刷廠工人)決定,“因為節(jié)省經(jīng)濟起見,愿將原有中央政府規(guī)定工資十八元的減為十六元,十四元減為十二元”。“二蘇”大會期間,該廠工人“每人募捐的工資來慰勞二蘇大會代表”。1934年3月16日,中央印刷廠與中央財政部、糧食部、國家銀行等中央機關(guān)廠企11個工會,在全國總工會的指導(dǎo)推動下,“互派全權(quán)代表”,聯(lián)合簽訂了《實行節(jié)省運動的革命競賽條約》,主要以節(jié)省工資津貼幫助戰(zhàn)費、每人每天節(jié)省二兩米幫助紅軍給養(yǎng)、每人每天節(jié)省一個銅圓幫助戰(zhàn)費、節(jié)省辦公費、種菜園、養(yǎng)豬、衛(wèi)生、儲蓄等八方面為競賽內(nèi)容,取得了豐碩成果。

與此同時,為支援革命戰(zhàn)爭和蘇維埃經(jīng)濟建設(shè),中央印刷廠工人還積極購買革命公債和捐資捐物。據(jù)《紅色中華》報道,1932年6月28日,“中央印刷局工人自動提議最低限度是每個工人拿出半月的工資來購買公債票,甚至有的愿將全月的工資全數(shù)購買。此外,中央政府工作人員及印刷局工人,又決定每日抽出伙食費一分,幫助革命戰(zhàn)爭”。1933年4月,“中央印刷廠工友每日在未到上工前半點多鐘就上工,八小時內(nèi)增加百分之五的生產(chǎn)等,在四月份內(nèi)工友們更自動節(jié)省了大洋四十五元三角,來幫助革命戰(zhàn)費”。1934年7月,“中央印刷廠工友自接到中央組織局及中央國民經(jīng)濟部募集被毯號召后,即在各種會議上討論這一問題,結(jié)果在十一日早晨的一個工人大會上,一聲號召,就募集了四十五床(被毯),并正在繼續(xù)動員,為超過五十床被毯而斗爭”。此外,“他們還附帶的募集軍帽、干糧袋、繃帶、衣服等等的東西”。《紅色中華》表揚稱:“這種種的光榮的例子,是值得登在紅板(《紅色中華》設(shè)置的《紅板》欄目,專門刊登表揚先進(jìn)事跡的專欄)上的。”
檢查:中央印刷廠存在“不可容忍”的浪費行為
與工人們火熱工作熱情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央印刷廠機關(guān)少數(shù)人員竟不同程度地存在鋪張浪費的現(xiàn)象,甚至還有極少數(shù)領(lǐng)導(dǎo)干部利用手中職權(quán),揮霍公款,貪贓枉法,嚴(yán)重?fù)p害黨和蘇維埃政府形象,也影響了中央蘇區(qū)正在如火如荼開展的節(jié)省運動。
1934年2月下旬,為了督促中央機關(guān)開展節(jié)省運動,中央國民經(jīng)濟部部長吳亮平率隊檢查了中央印刷廠的工作,發(fā)現(xiàn)了一些“不可容忍”的浪費行為,主要存在八方面問題:“(一)印一期《紅色中華》實際只需要油墨十二磅,而任意浪費報賬二十四磅半。(二)煤炭每天用五百斤,只燒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作為廢物。(三)印每期《紅色中華》,實際只需要油墨三斤半,而浪費至五斤半。(四)每期《紅色中華》排字只需七工半,而浪費人工報賬十二工半。(五)最熟練的,工資最大的工人(如在排字部鉛印部)沒有做實際的生產(chǎn)工作。(六)以一百另六人的生產(chǎn)工人,雜務(wù)人員有二十四人,工資二百三十元,甚至加油專用一人(而油燈則經(jīng)常無油),工資六元半,有三人給工作人員買魚肉等物,工資每人每月十一元。(七)工廠用的木炭,任私人拿來烤火。每做一個圍裙,要多費一尺以上的布等。(八)照(中革)軍委印刷所價格計算,每期全張報紙(二萬份算)除營業(yè)管理費與利益外,只需一百三十四元三角;而中央印刷廠,因種種浪費,所以每期全張《紅色中華》(二萬份算)需一百六十四元六角一分,相差至三十元二角一分之巨。”如此浪費,真是“不可容忍”。

針對如此情況,中央國民經(jīng)濟部對中央印刷廠的嚴(yán)重浪費行為及古遠(yuǎn)來廠長等領(lǐng)導(dǎo)干部的官僚主義作風(fēng)進(jìn)行了嚴(yán)厲批評,并作出了處理決定:(一)前廠長楊其鑫同志及現(xiàn)廠長古遠(yuǎn)來同志,對于生產(chǎn)采取不可容許的官僚主義的態(tài)度,國民經(jīng)濟部特給他們二人以嚴(yán)重警告。(二)責(zé)成該廠廠長立即規(guī)定具體的確實的生產(chǎn)計劃,在提高工人勞動熱忱的基礎(chǔ)上來完成生產(chǎn)計劃。(三)責(zé)成該廠廠長立刻裁減不必要的人員,消滅上述不可容許的浪費現(xiàn)象,減低生產(chǎn)成本費。(四)廠長應(yīng)對蘇維埃政府負(fù)絕對責(zé)任,應(yīng)該立即健全工廠委員會的組織,組織生產(chǎn)討論會,經(jīng)常討論改良生產(chǎn)的工作。(五)組織審查委員會,徹底審查中央印刷廠的賬目。(六)根據(jù)這一決定,在中央印刷廠開展嚴(yán)厲的反浪費反貪污反官僚主義的斗爭,發(fā)揚工人群眾的積極性,為著革命戰(zhàn)爭來最大限度地提高蘇維埃的生產(chǎn)。
根據(jù)以上處理決定,中央國民經(jīng)濟部迅速在中央印刷廠組織掀起了反貪污、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的斗爭,并將檢查情況及時報告了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和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等。1934年3月3日出版的《紅色中華》第157期第3版,還全文刊登了部長吳亮平、副部長嚴(yán)樸署名的《國民經(jīng)濟人民委員部關(guān)于中央印刷廠工作的決定》,在中央蘇區(qū)引起了強烈反響。
審計:中央印刷廠“未有盡到蘇維埃國家企業(yè)機關(guān)應(yīng)有的作用”
1934年2月,中央審計委員會主任阮嘯仙,在中央國民經(jīng)濟部檢查中央印刷廠等工礦企業(yè)期間,率隊對中央印刷廠和中央造幣廠、郵政總局、貿(mào)易總局、糧食調(diào)劑總局等5家有代表性的國家企業(yè)進(jìn)行了審計,重點審查了他們的財務(wù)收支及生產(chǎn)管理經(jīng)營狀況。
阮嘯仙率領(lǐng)幾個審計人員,首先進(jìn)駐中央印刷廠。在印刷廠廠部,阮嘯仙召集廠領(lǐng)導(dǎo)、黨團支部及有關(guān)負(fù)責(zé)人開會,了解印刷廠的經(jīng)濟收支及生產(chǎn)管理情況。在聽完廠長古遠(yuǎn)來的匯報后,阮嘯仙開門見山,就有關(guān)問題進(jìn)行詢問。但是古遠(yuǎn)來一問三不知,財務(wù)收支不清,生產(chǎn)管理無序,阮嘯仙深感問題的嚴(yán)重。經(jīng)過審查,阮嘯仙發(fā)現(xiàn),印刷廠對于中央國民經(jīng)濟部指出的問題充耳不聞,同時還發(fā)現(xiàn)印刷廠財務(wù)賬目不符。經(jīng)突擊隊的努力和群眾的反映,發(fā)現(xiàn)該廠會計員楊其茲有重大嫌疑。對于楊其茲的問題,開始查了很久查不出來,后來經(jīng)過走訪群眾,并發(fā)動中央印刷廠工友與楊其茲面對面核對賬目,終于發(fā)現(xiàn)楊其茲“付賬與清算的數(shù)目不對,主要是多開工人的工資,還有工人借了公家的錢,扣還后不上賬”,這樣,他的貪污賬目就完全檢查出來了。經(jīng)反復(fù)核對,僅多開工人工資和扣錢不入賬這兩項,楊其茲就涉嫌貪污100多元,令人觸目驚心。
從對中央印刷廠等國家企業(yè)的審計情況中可以看出,蘇區(qū)企業(yè)管理中存在嚴(yán)重問題。鑒于此,由阮嘯仙牽頭組織起草的審計報告——《中央審計委員會審查國家企業(yè)會計的初步結(jié)論》,就中央印刷廠等企業(yè)在經(jīng)濟收支及經(jīng)營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公開進(jìn)行了披露。其中稱,中央印刷廠“每月有7000元以上的營業(yè)收入,是一個大的印刷機關(guān)。但還說不上有生產(chǎn)計劃和完善的管理,還未有盡到蘇維埃國家企業(yè)機關(guān)應(yīng)有的作用”。主要體現(xiàn)在三方面:一是“他們有支出預(yù)算,無收入預(yù)算。問他們過去幾月賺錢或蝕本,成本費如何?他們可以答不知道。只知道收來的錢都用光了,而且每月的開支,似乎還向國家領(lǐng)過錢,但沒繳過錢給國家。——廠長古遠(yuǎn)來同志這樣說的”。二是不注重生產(chǎn)經(jīng)營與管理,“該廠印刷物的估價,是把原料、工資、管理費及例假雙工資等算入,另加百分之十的純利”,并引用了中央國民經(jīng)濟部的檢查成果,認(rèn)為“這是說印刷廠得的利益當(dāng)更多(國民經(jīng)濟部說這是浪費,其實并未有用到這么多,不過向紅色中華報社卻收了這么個數(shù)目,應(yīng)該是增加了印刷廠的純利)。但這些利益哪里去了?他們也可以回答不知道”。三是認(rèn)為中央印刷廠存在貪污行為,“這里面當(dāng)然包含著很大的不僅是浪費而是貪污。他們的賬簿極不完全(現(xiàn)正在清查中),用錢沒有標(biāo)準(zhǔn),如工人借款,有時竟達(dá)到七八百元。負(fù)責(zé)人不了解整個生產(chǎn)情形及每個生產(chǎn)品的成本,因而不知道哪些是浪費,哪些是多余,所謂生產(chǎn)計劃、勞動紀(jì)律、節(jié)省運動,都提不出具體辦法來”。
難能可貴的是,審計報告一針見血地剖析了中央印刷廠等國家企業(yè)存在問題的共同原因:“上列諸廠局,一般的缺點是不明了本身在蘇維埃經(jīng)濟上的性質(zhì)和作用,不知道也不考察產(chǎn)品的成本,不知計算盈虧,有錢就用,沒錢就向國家主管機關(guān)要。毫無疑問的,我們蘇維埃的國家企業(yè)是簇新的發(fā)展的形勢,但因上述的缺點,還未能得到盡可能應(yīng)有的進(jìn)步。這是一。”第二,“各廠局都曾做過檢舉貪污浪費和反官僚主義運動,而因為沒有從斗爭中去抓住各廠局的特殊性質(zhì)與缺點,來從積極方面整理賬簿,建立會計制度和管理法制,以致貪污浪費現(xiàn)象無法肅清,官僚主義的領(lǐng)導(dǎo)方式,未能徹底轉(zhuǎn)變,廠長局長不了解實際情形,提不出具體的辦法,反使節(jié)省運動和提高勞動紀(jì)律,變成空喊。同時上級機關(guān),沒有經(jīng)常的檢查和具體的指導(dǎo),也應(yīng)負(fù)相當(dāng)?shù)呢?zé)任”。
最后,審計報告得出兩大結(jié)論,呼吁中央印刷廠等國家企業(yè)應(yīng)建立健全會計制度、反對官僚主義的領(lǐng)導(dǎo)方式。“一是,各廠局長,則對于原料、生產(chǎn)、營業(yè)、辦公費的節(jié)省,尚待考慮,而對工人節(jié)省是有把握。這里,恰恰與領(lǐng)導(dǎo)者的作風(fēng)相反。這就是告訴我們,反對官僚主義的作風(fēng),把各廠局來徹底整理,我們倚靠著群眾的勞動熱忱,是不難得到應(yīng)有成績的!二是,在大多數(shù)工人的革命競賽與沖鋒突擊來提高生產(chǎn)情勢底下,各廠局長一般的不僅不能領(lǐng)導(dǎo)這一勞動熱情,反而容忍不可避免地混進(jìn)蘇維埃經(jīng)濟機關(guān)來的害蟲,以破壞勞動紀(jì)律。有些領(lǐng)導(dǎo)者諉為工會的事,工人自己的事,似乎表示這是重視工人,重視無產(chǎn)階級的領(lǐng)導(dǎo)?這里,又恰恰相反,這正是向工人向無產(chǎn)階級領(lǐng)導(dǎo)開玩笑。”
中央審計委員會的審計報告,有理有據(jù),令人信服,特別是1934年3月31日出版的《紅色中華》第169期全文發(fā)表后,更是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guān)注。時任全國總工會蘇區(qū)執(zhí)行局局長的劉少奇,針對審計報告提出的問題,為規(guī)范國家企業(yè)經(jīng)營管理,親自主持制定了《蘇維埃國有工廠管理條例》《蘇維埃國家企業(yè)工人工會工廠委員會暫時的組織與工作條例》等內(nèi)部法規(guī),并撰寫了題為《論國家工廠的管理》一文發(fā)表在《斗爭》第53期。這些法規(guī)和文章,因與審計報告所提意見遙相呼應(yīng),措施針對性強,很快引起了蘇維埃中央政府的重視,中央印刷廠等國家企業(yè)存在的問題得到了較快解決。
警示:“只有加緊地反對腐化官僚主義,才能更有力地徹底消滅貪污現(xiàn)象”
中央印刷廠存在的貪污和浪費問題,引起了中央工農(nóng)檢察委員會的高度重視。1933年12月下旬始,為了檢查和落實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等簽署發(fā)布的第26號訓(xùn)令——《關(guān)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中央工農(nóng)檢察委員會在中央機關(guān)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公開檢舉貪污浪費分子的熱潮,對群眾舉報、反映強烈的中央互濟總會、中央印刷廠、中央造幣廠和中革軍委印刷所等有關(guān)人員涉嫌貪污案件進(jìn)行了立案調(diào)查,查實中央印刷廠會計員楊其茲“貪污一百七十元三角三分二厘”,中央造幣廠會計科長凌全香“吞污二百十七元六毛七分八厘”,中革軍委印刷所會計路克勤“已查出四十余元,還有七、八、九三個月的賬還未查”,并于1934年2月15日出具了《中央工農(nóng)檢察委員會公布檢舉中央各機關(guān)的貪污案件的結(jié)論》(以下簡稱《結(jié)論》),分兩次刊發(fā)在《紅色中華》第152期第3版和第153期第3版。
中央工農(nóng)檢察委員會在《結(jié)論》的第二部分,即關(guān)于“中央印刷廠、造幣廠與軍委印刷所之貪污檢舉”中,首先分析了以上三個單位人員貪污的方式及查處的簡要過程。《結(jié)論》稱:“這三個工廠貪污的人都是會計科長,貪污的方式大體相同,主要是以少報多,多開工人的賬。”在談及中央印刷廠貪污案件的查處過程時,《結(jié)論》稱:“中央印刷廠楊其茲的賬目,開始查了很久查不出,因為他的貪污不是公開的,所以單純算賬就查不出,后來我們發(fā)動了工會與少共的輕騎隊,特別是該廠的輕騎隊與全體工友,參加了審查委員會,就發(fā)覺他的付賬與清算的數(shù)目不對,主要是多開工人的工資,還有工人借了公家的錢,扣還后不上賬。于是由全體工友對數(shù)與清查他的貪污賬目就完全檢查出來了。”
接著,中央工農(nóng)檢察委員會在《結(jié)論》中認(rèn)真剖析了中央印刷廠等“三個貪污案件”發(fā)生的主要根源。《結(jié)論》認(rèn)為,“至于這三個貪污案件之釀成,由于該廠過去的廠長總務(wù)處長之官僚主義的領(lǐng)導(dǎo)”。《結(jié)論》中舉例說,“他們從來不檢查會計科的工作與生活,也不查賬,由他隨便報賬,使這些貪污分子,可以自由地造假賬貪公款”。“(中央)印刷廠總務(wù)處長(會計科歸他管)從不問事,工作消極。”基于此,該《結(jié)論》總結(jié)道,“所以反貪污浪費,就必須反對官僚主義,因為官僚主義總是包庇貪污腐化的”。

任人唯親、敷衍塞責(zé),也是中央印刷廠等“三個貪污案件”發(fā)生的另一重要原因。“(中央)造幣廠與(中央)印刷廠之貪污數(shù)目有百余元與二百余元之多,經(jīng)過的時間很長,這不單因為官僚主義的領(lǐng)導(dǎo),而且,還由于過去兩個廠的廠長,離開階級立場,站在親屬觀點上引用自己的親戚來管理經(jīng)濟,而又不檢查工作。”該《結(jié)論》舉例說:“(中央)印刷廠之楊其茲,系前廠長楊其鑫之兄,是楊當(dāng)廠長時引用的,——后來查田查出他是地主又是從前教老書先生。(中央)造幣廠之凌全香,系前廠長陳祥生之老婆的哥哥,陳當(dāng)廠長時引用的,查田時,查出他是富農(nóng),曾發(fā)生錢不對數(shù),陳不僅不去檢查他的賬目,還替他掩蓋,后來洛江區(qū)寫信來說他是富農(nóng)。陳祥生不但不立即警覺起來,反而替他隱瞞成分,在黨證上□(原件字跡模糊不清)寫貧農(nóng)。因為官僚式的廠長楊其鑫與陳祥生二人離開階級立場引用親人,特別是陳祥生公開庇護(hù)階級異己分子與貪污行為,所以那兩個混賬東西,就更加大膽無忌了。”
基于此,中央工農(nóng)檢察委員會在該《結(jié)論》的最后,給中央蘇區(qū)廣大黨員和干部提出了三方面的警示:第一,“由這三個貪污的檢舉,證明反對生活腐化,特別是反官僚主義是與反貪污斗爭不可分離的,只有加緊地反對腐化反對官僚主義,才能更有力地徹底消滅貪污現(xiàn)象”。第二,“關(guān)于用親戚尤其是階級異己分子,這完全是封建的官僚機關(guān)的惡習(xí)。蘇維埃機關(guān)絕不允許有這種惡現(xiàn)象,我們應(yīng)該加以無情的打擊”。第三,“對于工廠的工賬,我們提議應(yīng)當(dāng)每月向工人公布,或是由工人與工會派代表來審查,每月不要有了結(jié)算就放心,而且工廠負(fù)責(zé)者與該廠上級機關(guān)應(yīng)當(dāng)詳細(xì)審查決算”。
在社會各界的廣泛關(guān)注下,中央印刷廠等三個國家企業(yè)的相關(guān)責(zé)任人,均受到相應(yīng)的懲戒。其中,中央印刷廠會計員楊其茲與中革軍委印刷所會計路克勤、中央造幣廠會計科長凌全香三人,因貪污被移“送法庭裁判”,受到蘇維埃最高法庭的公審判決。中央印刷廠前廠長陳祥生、楊其鑫及現(xiàn)任廠長古遠(yuǎn)來因官僚主義作風(fēng)被給予嚴(yán)重警告處分;中央印刷廠總務(wù)處長被撤銷職務(wù),其他相關(guān)責(zé)任人也受到應(yīng)有的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