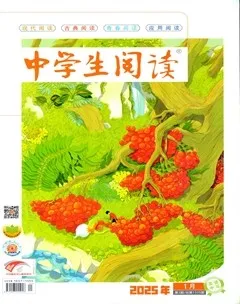黑魚
2025-01-18 00:00:00韋如輝
中學生閱讀·高中·讀寫
2025年1期
老話說,不打不相識。此話不虛,母親跟韓桂枝就是這樣。
時間要回到多年前,我還小,剛記事。
夜里,下了大雪。雪還沒有成團往下掉的時候,家里的電話機突然響了。母親的一只腳才伸到被窩里:“哎呀,這是誰呀?”母親慌忙把那只腳從被窩里抽出來,趿拉著棉鞋,來到電話機前,伸出手又蜷回來,好像面前是一塊燒紅的鐵塊。上一次,也是夜里,電話機響了——父親從工地的腳手架上掉了下來。
姨姥明天要從武漢來。母親長舒了一口氣,打開門,成團的雪從天上沒頭沒臉地砸下來。
姥娘走得早,母親是姨姥一手帶大的。自從母親成了家,遠嫁到武漢的姨姥,還是第一次要來。
母親抬頭看天,低頭看地,眼里除了白還是白。母親陷入無限的為難之中,老人家現在來,自己該拿什么招待她?
此時,姨姥喝黑魚湯的畫面,從母親記憶深處浮出來。姨姥雙手捧著粗瓷大碗,仰起腦袋,瞇著眼睛,讓最后一口湯滑進咽喉里,吐出一口氣,一絲笑意從她眼角的魚尾紋里蕩漾開來。
一大早,雪停了,樹上的雪團冷不丁掉下來。母親深一腳淺一腳往農貿市場趕。她要趕個早市,買一條黑魚。
魚行老板跟母親相熟。母親說:“留一條黑魚。”老板叼著煙,煙火快燒到嘴角,一溜煙灰固執地掛著。“來得巧,今天就一條,河里結了冰。”說這話時,煙灰倏然落下,落到面前的塑料盆里,一條黑魚在水里似動非動。母親又說:“留著啊!”轉身往前走。她要到前面的商店,買些煎煮黑魚湯的作料。
回來時,魚行老板的面前站著一個裹軍大衣的人,正接過一個黑色的塑料袋子,袋子左右晃動,呼啦呼啦響。……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