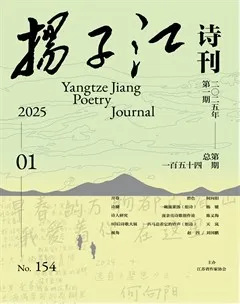“讓我們聽見大地的鼓聲”
當代詩人的風格追求越來越顯出多樣化趨勢,有的追求深邃悠遠,有的追求寧靜淡泊,有的追求慷慨壯闊。劉立云反復抒寫慷慨壯闊,希望詩歌與生命互相清潔,無論是對日常生活多側(cè)面的切入,還是對軍營人事的歌詠,都呈現(xiàn)出一種升騰之勢、怒放之態(tài),正如他一首詩的題目《升騰或者怒放》,也如他在不同詩篇中表達的,希望用自己的靈魂敲響大地,希望人們都能聽見大地的鼓聲。這應(yīng)該是理解劉立云的一個重要角度,或者說是理解當代軍旅詩歌必不可少的角度。其實也只有從這個角度,才能更準確地認識劉立云的特殊情懷和特殊的言說方式:豪放抒情與現(xiàn)代文明進程互為觀照,所形成的獨特的“詩歌政治”;以詞的鋒刃錘煉詩藝,測試生命意志能達致的高度;浸潤家國情懷的抒寫別具只眼,努力發(fā)現(xiàn)世界的真相。
植根大地的“詩歌政治”
有研究者曾就政治抒情詩的品格作過分析:“政治內(nèi)容、政治思想,并不是非要通過某些政治話語直接表現(xiàn)出來,而是通過形式意味、風格力量等藝術(shù)創(chuàng)造原則,通過對生活世界批判的甚至是否定性的內(nèi)在特征表現(xiàn)出來,從而構(gòu)成與現(xiàn)實的關(guān)系,達成一種特別的‘詩歌政治’。”①詩歌政治就是一種公共性的表達,包含個體體驗,更貼合與歷史潮流共振的公共經(jīng)驗。劉立云的抒情在高音部和低音部之間滑動,構(gòu)成“肯定”的言說方式,這種“肯定”出于內(nèi)心,緣于現(xiàn)實或者歷史中一陣陣“大風的聲音”,他在傾聽時感覺自己“緩緩握住的/是生命的一個寓言,大地的一陣心跳”(《紅色寓言》)。寓言意識,大地情懷,就是他的詩歌政治。
他哪怕是寫目盲或失腿的殘疾軍人,也富有生命的熱度和生活的溫馨感,即使憂郁也不失寧靜,始于低音漸向高音而終歸余音裊裊的深沉。戰(zhàn)爭幸存者之所以為幸存者,不僅因為僥幸存活,更因為感受到生的幸福,雖然看不見,但是依偎在愛人胸前仿佛“偎依在黃金麥地”,“輪椅”和“麥地”二者之間的特殊關(guān)聯(lián)因“炮彈落下的瞬間”而明晰,甚至形成了因果關(guān)系,沒有輪椅象征的犧牲也就不會有偎依的幸福,美好因為殘缺反得完整。再如老兵雖然失去了腿,但在市聲躁動中歡悅地看眾人“從暖色的光斑里/匆匆移動”“激動得熱淚盈眶”,又常常記起自己健康的過往,“那條空空蕩蕩的褲管里,/依然奇癢而難忍”(《一個傷病對腿的懷念》),對于生活的熱愛之情宛然可見,“奇癢”的感受是肢體的更是心靈的,是新鮮而美好的生命體驗,一掃陰霾而反襯出勃勃生機。他書寫戰(zhàn)爭的系列詩篇也大多類此,前面都是鼓點輕擊甚至重槌猛擊的節(jié)奏,最后收束于弓弦輕拉的旋律。這就是他的抒情方式,起于高處而輾轉(zhuǎn)抑揚,如大地鼓聲,余音若有所思,是為回聲。
劉立云那些與戰(zhàn)爭相關(guān)的詩篇,基本不用標點,有著特殊的斷連效果。分行顯出時間的流逝,傳遞或疾或徐的節(jié)奏;無標點則暗示每一刻都可能形成空白斷裂,形成空白和斷裂兩端的冷峻對峙,空白處正是記憶深沉而生命感受幽微難言處。就像《流彈意識》中,攜手并進的戰(zhàn)友,“你因站在我的左邊墳頭上已開滿鮮花/我因站在你的右邊如今依然在太陽下行走”,陽光因為生命而讓人產(chǎn)生“溫暖”的感覺,更因為生與死的對視而揭示出悲情或冷酷的一面;咫尺之間,生死兩途,懷念就成為生活延續(xù)的方式。高音區(qū)抒情往往顯出呼告情勢,而低音區(qū)抒情則多流露為婉轉(zhuǎn)不盡的意緒,這種滑動恰體現(xiàn)出“當初”的急促節(jié)奏與“當下”的悠長況味反復切換。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憶當初”起到喚醒作用,情感開始升騰,“看當下”則胸臆淋漓,呈怒放之勢,歷史的回聲與當下的鼓聲反復激蕩。
劉立云言志的獨特之處,還在于其諸多詩篇形成的個人編年,從新兵入伍到南疆見聞,從國內(nèi)軍營到國際戰(zhàn)場,從士兵角色體認到軍人身份洞察的歷時變化和地理切換,構(gòu)成了一部從軍史。《生命最美的部分》組詩以列兵為開端,將哨所、門崗、南疆、高原等空間點連綴起來,視野宏闊,主題明晰。敘事是樸實的抒情,當詩人把生活經(jīng)歷按照編年或者地理志形式譜寫出來,就是在紀念那些不可遺忘的瞬間體驗或者過程體驗,也就意味著以心理感受和記憶建構(gòu)自己的時間之軸和精神高地。反復記述從軍歷程和心路,構(gòu)成一部規(guī)模宏大的從軍征;從更高的層面看,像劉立云這樣的軍旅詩人都因為其工作環(huán)境的明晰變化而形成不同的個人編年,也是當代軍旅詩歌的典型特征之一。這樣的經(jīng)歷使他自覺遠離“將詩歌導入一個狹隘的、孤芳自賞的小天地”,不僅源于對慘烈而壯闊歷史的體認,更出于對詩歌意義和價值的體認。
詩人反復編選的詩篇,就是他不斷想呈現(xiàn)的聲音,自然反映了他念茲在茲的感受或者追求。《內(nèi)心呈現(xiàn):劍》《烤藍》《高地》《河流的第三條岸》對于劉立云來說就是如此。前幾首具有鮮明的軍旅背景,而《河流的第三條岸》雖然只著眼于黑龍江,卻可以看作當代邊塞詩的一個特殊范本。“他們那邊叫阿穆爾河,我們這邊叫黑龍江”,一物而兩名,兩個短句并列卻不分行,顯出平行對視而又隱然隔離的態(tài)勢,國與國的現(xiàn)實關(guān)聯(lián)與歷史關(guān)聯(lián)豁然而出,對于軍人身份的作者來說就更加微妙。從江心古城島眺望雅克蘇,河流能“看到我內(nèi)心凄楚”,蘊含了復雜的歷史況味。黑色水流被比喻成一方水墨:“它留下的白/有如鐵被磨亮之后,隱居在自己的光芒中。”這里的留白是江水偶爾泛起的浪花,是國土往復競奪的象征,是界河暗示的戍守歲月,是前人給后人留下的拷問,所以水與鐵形成黑與白的另一重象征,象征歲月之逝如斯夫,其中的鐵血意味始終難掩。鐵被磨亮暗示著鋒刃如霜,以其不用而顯出鎮(zhèn)國長安的大用。
劉立云首先是從戰(zhàn)爭與民族生存的層面思考,然后從國家博弈的層面思索,這是其詩歌政治的重要內(nèi)涵。這與他對戰(zhàn)爭的態(tài)度有關(guān):“面對當下這個瞬息萬變的大時代,如果我們的詩歌甘于沉默,或者只滿足于抒發(fā)內(nèi)心的孤傲和小情調(diào),可能難逃蒼白的命運。”①他不僅關(guān)注現(xiàn)代中國軍旅詩歌,還廣泛關(guān)注現(xiàn)代世界各國著名詩人書寫戰(zhàn)爭的詩篇,而且從地緣政治對弱小民族的生存影響角度展開思考,所以他推崇薩克斯、布羅茨基和阿米亥,強調(diào)他們“從自己的現(xiàn)實境遇去思考人類的命運”,在劉立云看來,詩人對戰(zhàn)爭發(fā)出的聲音,是喚醒人類良知的聲音,“就應(yīng)該是大地的聲音、天空的聲音、生靈和草木的聲音”②。
以詞的鋒刃測試生命的高度
詩人努力捕捉甚至固化那些介于物象與感覺之間的微妙區(qū)域,以涵括現(xiàn)實觀察與歷史回溯以及各種傳統(tǒng)聲音的混響,因而往往擁有“現(xiàn)實/歷史/自我”三者合一的個性化體驗,畢竟詩歌既表達對世界的發(fā)現(xiàn)性認知,又是詩人安置自我靈魂的空間,其“意指”特點和“棲居”色彩是詩人的追求,為了實現(xiàn)這多重感受的疊合充盈,常常要借助靜思默悟得來的合宜詞句,形成自己的語法,對于劉立云來說,就是“以詞的鋒刃測試生命的高度”。
劉立云的詩歌語言多呼告、告白而非獨語,多描摹現(xiàn)實而不是冥想或“虛構(gòu)”,多用明喻、排比形成疊波連浪的氣勢,升騰不已而情感濃烈如花如酒。《歌,或者贊美》首先采取呼告的方式,“唱個歌吧!”抒情從高音區(qū)開始。“雷霆”“大河”“山呼海嘯”譜出極為宏闊的氣象,與士兵齊聲歌唱的場景正相呼應(yīng)。在這類詩歌中,劉立云多用明喻排比的方式,“就像一座山怒吼著,咆哮著/撞向另一座山;就像一群烈馬撒開四蹄/在原野上狂奔,踏起漫天煙塵/就像德沃夏克用重槌和弓弦,用震顫世界的/銅號,喊醒一片沉睡的大陸”。在連續(xù)的比喻之間,有意識采取了跨行策略,形成特殊的“連”,既節(jié)奏分明又連綿不絕,從視覺感受上升到聽覺感受,融會成連續(xù)撞擊而多重疊合的心理體驗,如洪鐘大呂反復震蕩,如同他用以作比的德沃夏克交響曲。實際上,德沃夏克后期轉(zhuǎn)向交響詩,努力打通音樂、繪畫與詩歌的壁壘,以多變的節(jié)奏象征生命感覺的抑揚起伏,“重槌”敲擊出鏗鏘的節(jié)奏,“弓弦”拉出心神震顫的旋律,“銅號”將聲調(diào)再升高一個音節(jié),使人感覺到“被一種力量提升和融化”。
《升騰,或者怒放》的抒情理路與《歌,或者贊美》一樣,先鄭重宣告,而終于呼告,因美國桂冠詩人沃倫《三種黑暗》而發(fā),思考核武器的巨大威力與恐怖后果:“必須剔除這兩個詞里的浪漫部分/抒情部分。因為它們現(xiàn)在是/猛烈的,殘酷的/光芒萬丈。”對于關(guān)鍵詞內(nèi)涵的釋讀重在其“矛盾”,外在形象“光芒萬丈”,其本質(zhì)卻是毀滅性的,這是“蘑菇云”視覺可觀卻令人恐懼的根源,它帶來的是深入每根青草、每片樹葉的“疾病”,解構(gòu)了“光芒萬丈”的浪漫。畢竟這威力巨大的物是人為的,結(jié)尾的呼告也就更加發(fā)人深省:“但是世界啊,人類啊/你究竟要爬得多高,摔得多慘/才能看清我們自己的命運?”既不否認其積極作用,又直面可怕的后果,最后上升為對“我們自己的命運”的審視。以《核殤》作為這組詩的總題,從漢語的詞源學角度來看,“殤”意味著尚未成年,喻示文明可能遭遇的夭折,憂患色彩顯得更濃。
當令人心情沉重的“歷史”退隱到遠處,時間軸一下子變得細膩起來,于是四季和晨昏就被點亮了細節(jié),日常生活的豐富質(zhì)感、細節(jié)使人的心靈擦拭一新。劉立云注目日常的感興之作,柔和而不失闊朗,顯出對語言的別一番體悟和琢磨,雖然背景多為山川曠野,卻不以鄉(xiāng)土抒情為旨歸,而是以“大地”為根基,講述自己對于“萬物”的體會,仍然心儀于一種處處皆在又大而無形的東西,仿佛他的詩歌就是為了使萬物深處那個龐然大物顯形。“早晨我去河邊洗臉/不慎滑倒,木橋上薄薄的一層霜/告訴我河面就要結(jié)冰了,從此一個漫長的季節(jié)/將不再需要渡輪。”(《大地上萬物皆有信使》)瓶水之冰的典故被轉(zhuǎn)化為木橋薄霜,而河邊洗臉的真實情境使得可能枯澀的道理變得親切起來,四季演替瞬間照亮了個人生命史。更為重要的是,“早晨”是一種類似于中樞點的時間設(shè)置,銜接了夜與晝、秋與冬,其過渡性恰顯出世間萬象各有啟示的生生不息的特點。局部的描景狀物不過是詩人興之所至的留痕,其詩語所想達至的,是生命感覺的細膩豐厚,是精神飛揚的超拔高度,是隴南宕昌霧中陡然發(fā)現(xiàn)的神女峰(《給一座山峰命名》),是荒沙敲門的蘭州“憂郁而蒼茫的靈魂”(《鉆石》)。
看見真相的“第三只眼睛”
每個將靈魂融入詩歌的人都覺得自己看到了世界的真相,仿佛生出了與眾不同的眼睛。劉立云就有這樣的自信,甚至說自己眼睛里有“毒”,無需更多,只需要一行詩,“我就能看見你的骨頭”。這可以稱之為審美的“偏執(zhí)”,甚至可以從中窺出隱秘的精神譜系。
《眼睛里有毒》似乎記錄了個人寫作的遭遇,也使人聯(lián)想到七月派詩人阿垅的《無題》,“要開做一枝白色花——/因為我要這樣宣告,我們無罪,然后凋謝”。不過,阿垅的自信緣于那個時代的理想,劉立云的自信緣于南方浴火重生的戰(zhàn)場。“多年前我在垃圾上爬坡/在白天展開的紙張上/獨自看見黑/大師們喝令我退下/我說不!我的雙腳不是用來退下的/我的思想也是/他們又說,那你就站著吧/那就讀著,寫著,寂寞著/等待在某一天莊嚴地凋謝。”回望是常見的書寫姿態(tài),回望聚焦之處顯出書寫者的格局與視野差異,緣于回望立身之處確立的時間軸和詩人的自我面向。劉立云的詩歌喜歡選擇具有臨界色彩的時間點,如凝霜的早晨或者突然到來的生命彌留之際(生與死的過渡),這就使得季節(jié)更替在“更換”與“代替”的層面上意味深長,并且使得詩歌具有了通過時間探索生命甚或意義的傾向,以這種臨界點展開其時間軸,向前追溯便是再次觸摸自我,必然指向消失或新生、放棄等命題,因為其中蘊含著事物變化的源泉,更蘊含著復雜的情感秘密。
“在垃圾上爬坡”意味著徒勞的寫作嘗試,“獨自看見”卻被“大師”喝令退下,折射出可笑又可怕的權(quán)威存在,反襯出“獨自看見”固然難,言說“獨自看見”更加艱難;正是因為這種堅持,才有了后來一句可見骨頭的自信。在劉立云的詩中,“南方”有著極為特殊的意義,絕非一般人吟詠引用的詩意江南,而是一段戰(zhàn)火歲月,“那年我從南方歸來/見過碑石輝煌/當著青草綠樹和盛大的落日/我也發(fā)現(xiàn)我比以前更聰明了”,對生與死最直觀的體察使人“聰明”,畢竟“碑石輝煌”與青草、綠樹、落日構(gòu)成了生命意義的兩極,二元對立思維雖然簡單,卻往往能夠最有效地還原生命的真相。
對自我生存真相的發(fā)現(xiàn)和對世界真相的發(fā)現(xiàn)需要同樣的眼光,劉立云將理性自知的“我”與始終仰望的蓬勃偉岸的“我”融通互文,以個我之力彰顯群體偉力,而又屢屢以微小的個我去審視歷史和現(xiàn)實中群體龐大的力量。是審視也是透視,是仰視也是俯視,多元視角的錯綜不僅形成超現(xiàn)實表達,也使得自我與現(xiàn)實形成了多重互涉關(guān)系。“即使依恃著鋼鐵,即使依恃著/我身后優(yōu)美的山川、河流和草原/我也將在火焰中現(xiàn)身,展開我的軀體/就像在大風中展開我們的旗幟……”(《火焰之門》)當山川河流和草原在我身后,“我”既可以是個體,也可以是群體,當“我”在火焰中現(xiàn)身,就是群體之我了,或者說洋溢著群體力量感的個我,很像戴望舒的詩句:“無形的手掌掠過無限的江山,/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陰暗/……我把全部的力量運在手掌/貼在上面,寄與愛和一切希望。”以“我”的微細感覺去揣想我們的宏大磅礴的力量,不僅凸顯了思辨之我,還確立“我”與時代共鳴時的仰望姿態(tài),就像《我這樣理解人民》所寫:“如果我漠視大地,拒絕做一粒卑微的/沙塵;如果我用自己的喉嚨,發(fā)出/烏鴉的嘶叫;如果我孤傲自負,形單影只/像飄雪一樣健忘,那么我懇請你把我/刪除!就像你在田野里刪除一莖稗草/就像我在電腦中刪除一個病句。”以山川草原作背景和愿意成為大地的一粒卑微沙塵是同樣的精神姿態(tài),前者因為自覺融入偉大而感知偉大,后者因為感知自我微小而感恩偉大。
因為日常會變得平庸、低矮、軟弱、無力,詩人才靠意志或者焦灼的呼喊來凝聚力量,激醒遲鈍的心靈;詩歌就是他每天磨亮的刀子,借此使人的目光抬升到鷹的高度。《阿米亥,阿米亥》和《劍:內(nèi)心呈現(xiàn)》可以看作互文文本,后者是劉立云為自己五十歲生日寫的。阿米亥經(jīng)歷過二戰(zhàn),在和平時期仍然警惕著戰(zhàn)爭幽靈的借尸還魂,“辨認因此變得更加艱難,更加詭異”,所以要每天反躬自問,呼喚和平“請進入我的心”。劉立云有著同樣的認知,只不過采用了更加中國化的表達方式:“我很高興一個懷劍的人/住在我的身體里/我很高興我能成為這個人和這把劍/共同的知己和共同的鞘/我很高興,當我最外面的皮膚/被另一把劍戳穿/那股金子般的血,將濺紅/我身體里的那件白袍”。人與劍成為知己,擁有共同的鞘,意味著精神氣質(zhì)的合一,而詩人期待的最高境界是劍鋒露出,血染“我身體里的白袍”,這固然使人聯(lián)想到白馬少年“捐軀赴國難,誓死忽如歸”的風采,也可以把它看作劉立云詩歌創(chuàng)作的一個隱喻。詩歌既是淬煉他靈魂的火焰之門,也是他吐露豪氣、縱橫大地的劍:“我希望我的詩歌在保持詩歌品質(zhì)的同時,還能發(fā)出火焰的光芒,劍的光芒。”①
以群體記憶喚醒自我,鐫刻成為自我生命不可割舍的一部分,而不是將自我融化在“大我”之中,這是優(yōu)秀詩人無法擺脫的誘惑。劉立云的策略是以傾聽或觀看的方式,在傾聽或觀看的過程中覺醒自我,從而覺醒自我與歷史與現(xiàn)實的深刻關(guān)聯(lián),而不是郭小川、賀敬之那種以呼告的方式將自我投入集體的“大我”。比較典型的是《蒼茫二重奏》中的那首《窗外拉二胡的》:“他一曲/接一曲,在熱情洋溢地拉/孜孜不倦地拉,總是把我的思緒帶走”。引發(fā)抒情主體感觸的,是外部存在的抒情,似乎在暗示情感的喚起需要外部媒介,而且是能夠順利共鳴的外部媒介,或者說這種抒情理路暗示著引起崇高情感的外部世界本就存在著崇高的情感。這個業(yè)余琴手拉的都是我“記憶里的歌”,如《紅太陽照邊疆》《我為祖國站崗》《我愛五指山》等,“而這些歌,哦這些歌/都刻在我年輪的吃水線上,/融化在/我的血液里”。詩人把“我”和“他”置為抒情的前景,而把一個數(shù)量龐大、身份迥異因而顯出復雜歷史縱深的“唱歌人”設(shè)為背景,使“我”與“他”的對話成為歷史的深沉回聲:“每當琴聲響起,我都打開窗,喊他/鋸木頭的,拉纖的,或者割膠的/吹號的,喂騾子的,炊事班背行軍鍋的/他都昂起頭答應(yīng),并且,一臉燦爛”。很顯然,“我”賦予“他”的身份,縱貫革命戰(zhàn)爭年代和和平建設(shè)時代,兼顧國防戰(zhàn)士和普通勞動者的身份,“他”一臉燦爛的響應(yīng)意味著對這些身份的認同,于是拉琴者與聽者就既具有互相獨立的審視意識,又擁有共同情感。不能不指出的是,二胡在很多現(xiàn)代詩人的筆下,都以發(fā)出悲音為主,比如“巷中樓上有人拉南胡,是一曲似不關(guān)心的幽怨”(林庚《滬之雨夜》)。劉立云筆下二胡的旋律,則陽剛明快,從一系列歌曲的名字就可以知道;“寫詩”與“拉二胡”是同在的行為,因而具有相同的精神質(zhì)地。既可以說是二胡的聲音喚起了自我深處的記憶,也可以說寫作使那種特殊的歌聲再次傳播開來。
有了記憶,個人生命史就有了扎實的基礎(chǔ),而記憶掇取為文字意味著生命中出現(xiàn)了空白,意味著本該清晰流暢的生命史有所缺失,其中隱現(xiàn)的是時間對人的嘲弄。“就這么耐人尋味,當我們回想過去十年/會沒緣由地忘記某一年/怎么也想不起來,該慶幸還是悲傷?”(《十年中的某一年》)詩歌一方面是對日常生活的掙脫,這使得詩人和讀者都能上升到某種高度擁有某種廣度,另一方面是對日常生活的沉潛,使詩人和讀者都能夠觸摸和體驗到某種深度與力度。因此,閱讀劉立云的詩歌,常常會“沒緣由”地想起很多生活細節(jié),又會感到“沒緣由地忘記某一年”的悵惘;能夠感受到金戈鐵馬起秋風的慷慨蒼涼,也能體會到“一根草將帶領(lǐng)一個春天/在來年的這片山谷卷土重來”(《大雨》)的爛漫。
作者單位: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
①殷實:《歷史意識,預(yù)言價值與詩歌的公共性表達——讀朱增泉〈中國船,從南湖起航〉》,《神劍》2021年第4期。
①劉立云:《回望一場戰(zhàn)爭》,《中國詩歌》2017年第8卷。
②劉立云:《火焰的劍為我們劈開大地——外國現(xiàn)代戰(zhàn)爭詩歌閱讀思考》,《詩探索》2011年第2輯。
①劉立云:《劍光閃爍的生活》,《星星》2021年第7期。
白小云,本名蔡麗娟,生于江蘇蘇州,現(xiàn)居江蘇南京。在《人民文學》《鐘山》《詩刊》《十月》《作家》《星星》等刊發(fā)表文學作品,出版小說集、詩集多部。曾獲紫金山文學獎、金陵文學獎、江蘇省新聞出版優(yōu)秀青年稱號等。偶把生命之愛訴諸色彩線條,本組畫作選自其“喵三幅——溺于柔軟愛空無”水彩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