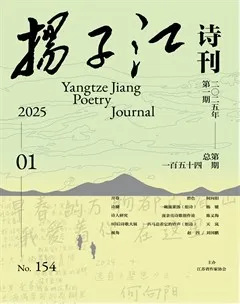“填平精神與物質之間的溝壑”
一
黃梵認為:“詩歌是最靠近人類本性的體裁”(中國作家網訪談《黃梵:掀開詩意的面紗》),這種植根于人類本性的詩之思考,與我前些年談論散文詩的觀點——散文詩有它獨立的精神和氣質所在,這種精神和氣質根植于人類性情的蕭散及詩意棲居的理想欲求——有相似之處。這讓我對其詩歌有了一種親近感。黃梵還看到了人性中的悖論與辯證法之間的美妙契合,因為二者都常常帶來近乎模糊或混沌美學的絕妙體驗,而詩歌帶著它們共同的特點為人類打開了通向終極關懷的甬道:“人性中的悖論和辯證法一樣的謎,都在詩歌中得到了極致體現。……詩歌的多義,不確定,謎一樣的美,也讓它成了詩人走向超越和自由的通道,成為擺脫現實束縛的利器,成為掙脫俗常之美,讓美另成一格的啟示。”這繼而讓我有了一種從根性上認識其詩歌的沖動。
詩歌既然最靠近人類本性,那么表現人性中的悖論就應該成為題中應有之義,比如表現人性道德中的善與惡、美與丑、正義與非正義,情感中的愛與恨、傲慢與謙卑等。不過,一般情況下詩人不會直接訴諸這樣的主題,否則就成為一種主題式的創作,為自己制造局限。通常情況下,這些主題都融合在與詩人有關的生活題材的寫作中。就生活而言,慣用的分類方式是精神與物質兩類。這種二分法直接把精神與物質對立起來,并且將之作為判斷人類人生追求之高下的一種方式。就詩歌寫作本身而言,它是人的一種精神需求,無論創作主體在詩歌中表現精神生活還是物質生活,它都是一種精神層面的東西。但在黃梵看來,由于“很多人沒有發現精神與物質之間的縫隙”,故“有些人的寫作只是精神符號的游戲,有些人的寫作只是物質生活的延伸。”(《我們時代的文學書寫:痛點與期待》,《文藝報》2022年1月24日第6版)前者略可理解為思辨的游戲(創作過于理念化),后者或可理解為將寫作當作記錄生活的流水賬(創作過于物質化)。這樣的寫作方式都是不可取的。黃梵善于從日常中捕捉生活的橫斷面,然后切入自己的精神思考。我理解他所謂“精神與物質之間的縫隙”即生活與精神相交部分的“留白處”,在這個留白處,我們得以見到生活與情感、愿望或意志行動的交融。黃梵的近作一方面保持了此前寫作的特點,同時在“留白”上有了更多更豐盈的嘗試。如《折射》一詩,詩人先從日常中發現的折射現象寫起,然后提煉出新奇的想法:“你沿著河堤,漫無目的往前走"/"你的直背和彎腰,都在河里有了新的內容"/"直,不再那么挺拔"/"彎,也不再那么扎眼”,這實際上是詩人為自己找到了一個切入問題的新角度。于是他把這當成“一面放松的鏡子”,同時看出了它所擁有的神奇功效:“微波把分明的現實,化為含混的錯覺/你走動時,是你的憂慮"/"在水面和繽紛的錯覺周旋”,如果你生活得渾渾噩噩,錯覺的狀態或許是一種精神享受,然而一個對現實感保持警惕的人,無論如何,他都不會被這樣虛假的幻覺所迷惑,所以詩人在詩歌的結尾將結局挑明:“無論你怎么走"/"這面鏡子,也無法把你的憂慮變短”。這就為我們揭示出一個道理:折射貌似為解決問題提供了一種方法,可在現實生活中它并不奏效。就像是刻舟求劍和掩耳盜鈴,不過是一種錯誤認知,或者自欺欺人的手段。這是黃梵詩歌中非常典型的案例,人行走在現實生活之中,經驗的話語信手拈來,而精神上的出路仍然在空白處留存。他提出問題,但并未解決,或者他亦不能解決,因為像這樣宏觀上抽象、微觀上具體的問題需要更多的人來實踐或想象。
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彭波那齊曾說:“在宇宙中,存在三種活的存在者。有全然永恒的活的存在者,有全然有朽者,還有在此二者之間者。”(《靈魂與自由意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扉頁)如果將此處的“存在者”換作“寫作”,則第一種全然永恒者,可以是對應著“神”一樣存在的宗教典籍或奠定人類歷史根基的宣言、法典等作品;第二種全然有朽者,顯然是對應著“禽獸”一樣存在而又毫無意義的寫作;第三種介于此二者之間者,是對應著“人”的既出入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文學寫作,詩歌的寫作即從屬其中。詩歌既不能失了人間煙火,又不能完全成為沉重的精神重負。前文黃梵所說“精神與物質之間的縫隙”,一看就知并非原始意義上的縫隙,而是指二者在“鉚合”或“銜接”之前呈現出來的那個空白處,這個空白處不是無用的,而是如道家思想里所說的“無之以為用”的那個“無”。這樣理解起來,介于物質與精神之間的詩歌寫作的那個“縫隙”,其寫作意義上的所指就不言自明了,那就是創作既不過于理念化又不過于物質化的中間寫作狀態。所謂執兩用中,然而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如果一個詩人缺少對生活足夠的敏銳,缺少投入與洞見,缺少寫作的靈性與韌性,看似容易的,實際上最難達成。而黃梵在《外國》《石榴》《黃鶴樓》《南唐二陵》《導師》《六十歲》《工作日》等詩篇中都做到了。
二
黃梵“心目中的詩歌,是試圖填平精神與物質之間的溝壑,讓精神與物質成為詩歌的一體兩面。”(《我們時代的文學書寫:痛點與期待》,《文藝報》2022年1月24日第6版)可見他認為,精神與物質對詩歌而言都必不可少,詩歌必須要處理好物質和精神之間的平衡問題,失之偏頗,則詩的精純亦受折損。
不過,黃梵所說的“一體兩面”之表現可以有多層次理解。一方面他所言之“精神與物質”可以是我們常言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另一方面我們還可以結合他的“現代詩教”觀念來看。鑒于從人類本性切入對詩歌認知的緣故,黃梵對“現代詩教”產生了濃厚興趣。他認為現代詩應該與古典詩歌一樣,“不應該只是精英的標配,要像古人那樣,成為常人精神交流的工具之一。”(中國作家網公眾號“有態度”專欄·黃梵訪談)這在很多人看來,是不可想象的事兒。就新詩對生活的功用而言,這無疑像一場充滿浪漫想象的革命。試想,詩歌走進千家萬戶,進入人們的普遍生活,連販夫走卒都熱愛詩歌的那個黃金時代如果又回來了,會是一種什么樣的震撼情景!這必將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又一個轉折點。然而黃梵有他的考量,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很早就從詩歌中獲得了很多教益(《詩歌的教益》,《山花》2001年第10期)。
古代詩教與現代詩教迥然有別,但“通過回溯詩意的源頭,回到詩人的創作經驗,他找到了理解詩意、寫出詩意的便捷之路”,那就是透過“意象帝國”建立起對詩歌王國的支撐。在黃梵看來,意象乃詩歌進行創造的“靈魂”所在。前文所說“詩歌的一體兩面”,黃梵也從意象的角度做過闡述:“具體來說,詩歌意象既尊重現實的客觀,也不忘激發主觀想象的自由;既接受生活經驗的驗證,比如驗證意象表達是否準確等,也接受人的意志想偏離常態生活的冒險。”(《我們時代的文學書寫:痛點與期待》,《文藝報》2022年1月24日第6版)如此,經由意象的關聯,生活經驗與精神冒險在詩歌中達到了一種既矛盾又對立的統一。當然,需要指出的是,黃梵對“意象”這一概念的理解,既有對傳統的繼承,也有對傳統的創造。他把意象有創意地分成兩類:客觀意象和主觀意象。前者即物體或物象,后者為想象的、內心的圖景。(《意象的帝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77頁)后者大抵是黃梵的發明。而且他認為,在新詩的創作中,主觀意象更重要,更受人青睞,“為了確保新詩有足夠的詩意,更多要仰賴主觀意象。”(同上,第87頁)其實,這與現代詩的生成機制有關。黃梵之所以能做出這樣創造性的“發明”,顯然正是看出了新詩創生機制的緣故(有的地方他說成是“新詩的需要”)。黃梵的這一組作品,大多踐行了他以主觀意象經營詩歌的觀念,《石榴》《黃鶴樓》《“起風了……”》《理工科思維》《蘆葦迷宮》《雨后的郊區》等數首,處理得尤其好。當然,這并不是說客觀意象不重要或者不好。只是在新詩寫作的過程中,客觀意象有其局限而已。黃梵此前的詩歌中有一首《繩子》,是把客觀意象和主觀意象結合得非常好的范例。在這首詩中,詩人從“繩子”這一物象入手,不斷地借助形似、意似的物象(如蛇、拉索橋、蟒蛇、牧羊犬、垂下的綠蘿、策展人、琴弦),以及對圖景的各種想象和創設來達到對詩歌的“帝國性”建構,既有“近取譬”,又有“遠取義”,直接喚起了繩子“意象帝國”中眾多成員的美妙互動,同時通過主觀意象的連續催化,確保了詩意的襲取和再生,有一種“兼取并包”的氣勢。從現代詩的特質看,“意象尊重客觀現實”只是初級寫作的一個需求,“主觀想象的自由”和“偏離常態生活的冒險”才是它的最終訴求。因為提倡詩教,需要為一般的寫作者打開進階門徑,黃梵必須對初級技藝也做出強調。
黃梵說:“如果只談個人詩學,我會要求自己寫的詩歌,意象既清晰、準確又難以窮盡,成為從生活體驗走向精神思考的通道。”(中國作家網公眾號“有態度”專欄·黃梵訪談)這已是慘淡經營“意象帝國”之后登堂入室的層面了。他所謂“曲線救國,通過呈現意象迂回地暗示出來”(中國作家網訪談《黃梵:掀開詩意的面紗》),不是一句空話,更不是一句簡單的話,而是對寫作者提出了一個更高的要求——真正擁有現代漢語的“煉金術”。
一提及新詩語言的“煉金術”,很多人就會產生誤解。他們以為,這是要求現代新詩也要像古典詩那樣錘字煉辭、雕章琢句,其實不是。更多的情況下,新詩追求的是意象的原初性創造及其準確性,尤其是黃梵所說“主觀意象”的原初性創造及其準確性。在黃梵那里,主觀意象很大程度上帶有開放性,但這并不意味著人的意緒或情緒可以胡亂拼接。主觀意象獨創性、有效性和合理性的保證,是一首現代新詩成功的關鍵。在談及詩歌《中年》的創作時,他就意識到:“新詩中存在著一些經驗或體驗,它們和最準確的比喻、意象一一對應,一旦被某個詩人發現,其他詩人就再也無法為那種經驗或體驗找到更有表現力的比喻或意象,只能把與那種經驗或體驗相關的其他比喻、意象棄之不用。……我能感覺,無數經驗或體驗對應的準確比喻或意象,構成了一個偉大的倉庫,聰明的詩人應該找到這個倉庫,并去取拿珍貴的庫品。因為這些庫品拿一件就少一件,別人每拿走一件都會迫使你轉向別處,使你想表達的經驗或體驗也少了一種。”(《詩與事》,《詩選刊》2011年第6期)這實際上是在告誡詩人,對于一些經驗或體驗,要盡可能早地去發現與它們一一對應的最準確的意象或比喻,盡量占領言說的先機,因為我們通常所說的“個人經驗”,其實“并不隸屬個人,它既是共同經驗的個人解讀,也是往昔經驗的重新喚醒”(《新詩50條》,《揚子江詩刊》2011年第6期)。這樣,憑借個人的原初性創造或者言說所占據的先機,你就擁有了排斥其他詩人占有這種詩歌話語經驗的權力。
在古典詩學傳統里,客觀意象占據主導地位,意象的選擇與布局異常重要。同樣,在新詩建構的過程中,主觀意象合乎情感或精神的需要也非常重要。但是要做到這一點談何容易?黃梵曾總結說:“我習詩四十年也得承認,就算營造意象的技藝已嫻熟自如,我仍需要一些神秘的時刻,來讓意象抵達化境。……寫出次好的意象,只需要技藝嫻熟,寫出最佳意象,還需要因緣際會。困難不只來自有無天賦,還來自注意力夠不夠、對生活的敏感度夠不夠、生命的體悟到不到位。”(《詩的雜記》,《特區文學》2023年第10期)可見詩歌之路亦是一條修行之路。各種看不見的加持力量,都靠你的修行得來。
三
由于主觀意象本身被理解、被拆解的可能性較多,所以黃梵的“現代詩教”也對“詩意陌生化”做出了強調。他把這當成詩意萬變不離其宗的形式規律,并且認為“這一規律不僅適用詩歌,也適用生活。如果深究這一規律的來處,根子當然在人性深處。它來自人本性中的悖論:既追求安全又追求冒險的訴求。安全訴求對應著詩意中的熟悉,因為面對熟悉的事物,人才會有安全感;冒險訴求對應著詩意中的陌生,因為接觸陌生的事物,恰恰是人冒險希望達成的目標。”(中國作家網訪談《黃梵:掀開詩意的面紗》)這一理解,與上述他對詩歌“一體兩面”的闡釋具有一致性。
當然,不僅是理念上如此,黃梵的詩歌寫作也在認認真真地實踐這一點。比如這一組詩作中的《石榴》《黃鶴樓》《超市》《手機拍照》《導師》《小男孩的歌唱》《在河邊》《睡懶覺》《雨后的郊區》等,在“詩意陌生化”上都處理得非常有智慧。他較早的一些詩篇如《二胡手》就曾得到過“享受了作者精心制作的諸如‘用弦曲支起一道斜坡’這樣充滿陌生感和詩性的文字”的評價。(徐南鵬《詩歌精神的覺醒與擔當:讀黃梵的〈二胡手〉》,《星星·下半月》2009年第7期)我們舉一個例子來看。《雨后的郊區》這首詩,開篇一句是“我對雨后的郊區,心存感激”,一上來就抓住人的好奇心,讓你忍不住讀下去。為什么會“心存感激”呢?因為“雨是勤勉的清潔工,它打理完的山川"/"讓我的呼吸,游刃有余”,這兩行不僅道出了心存感激的原因,還創設了一個非常典型的主觀意象。接下來的第二節,寫到郊區的其他事物——“被霧舉高的鳥聲”(又一個非常新穎的主觀意象)及其行動,鳥聲“尋找云中的太陽”,“急于說出,太陽看不透的秘密”,“和溝里的流水,議論田野清香的來歷”,這一連串的排比都運用了無比新穎的想象。新奇的圖景紛至沓來,以致于“令我腳下的水泥路,也羨慕童年的土路”。注意,水泥路羨慕土路,也是陌生化的處理。接下來的第三節,又寫到郊區的“風”:“風的哮喘病,已被雨治愈"/"它寂靜成了初夏的午睡”,這兩句描寫,主觀意象的創造及其連綴,堪稱經典。接下來的“將軍山如臥佛,枕著朝代的頌歌入定"/"而游客為聽禪語,東奔西走”兩句,也寫得不俗,尤其是前句。詩的末節,以“雨后的水”襯寫詩人的心境:“雨后的水,繼續在林間、水溝奏響"/"我心中的沖動,仍需要這妙不可言的配曲”,這兩句雖然在陌生化上稍微“松弛”了一些,但依然“妙不可言”。
這樣條分縷析地對“詩意陌生化”進行解剖,就是想讓大家看到,主觀意象作為陌生化的一種手法,在詩歌中已經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發揮。除了主觀意象的陌生化,主觀意象的連綴也非常重要。連綴當然不是胡亂拼接,它有許多方面的考慮,一是要順著主觀意象合乎情理的行動向外擴展,二是要與上下文的結構、風格保持協調一致,三是要順著整首詩的義脈或情感方向往前發展。當然,這也還只是其梗概,更多具體而微的磨合仍然需要費心考量。在《意象的帝國》一書的最后一堂課中,黃梵曾例舉寫出整首詩的若干方法,有從音樂性方面著手的,有從象征、隱喻、通感方面著手的,有從結構方面考慮的,不一而足。他還對詩歌的意味有專門研究(《詩歌中的意味》,《南京評論》2007年卷,2008年11月)。黃梵深諳詩歌的創作之道,但即使如此,黃梵也只是在詩歌王國里“編織他的可能世界”(敬文東《“已有無數的橋,可供我節節敗退……”——讀黃梵札記》,《詩探索·理論卷》2009年第1輯)通往繆斯之神的哪一條路都不順暢,詩人們永遠在路上。
作者單位:深圳職業技術大學教育學院
【本文系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2023年度學科共建項目(批準號GD23XZW19)、深圳職業技術大學創意寫作研究中心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