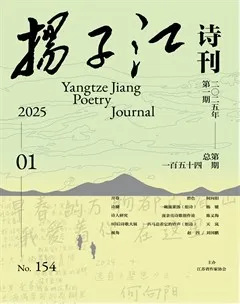凝視:液態(tài)的藍(lán)色詩(shī)學(xué)
與其說(shuō)平靜如鏡,不如說(shuō)微微顫動(dòng)……
既是間歇又是撫慰,液體的琴弓劃過(guò)泡沫的合奏。
——保爾·克洛代爾《旭日中的黑鳥(niǎo)》
經(jīng)過(guò)《青衿》《錦瑟》《剎那》《如初》這四本詩(shī)集的寫(xiě)作和命運(yùn)的淬煉——請(qǐng)注意每本詩(shī)集的名字都由兩個(gè)字構(gòu)成,何向陽(yáng)在詩(shī)歌世界中特有的性格和精神儀軌已清晰地顯現(xiàn)出來(lái)。在南京,她的研討會(huì)上,我就說(shuō)過(guò),她的下一部詩(shī)集或重要作品,書(shū)名或組詩(shī)標(biāo)題肯定還是兩個(gè)字的。果不其然,在北京初秋的午后,我拿到何向陽(yáng)剛剛打印出來(lái)的一沓詩(shī)稿,第一頁(yè)上迎面而來(lái)的就是兩個(gè)醒目的大字《碧色》。
對(duì)于何向陽(yáng)的詩(shī)歌,我是一個(gè)時(shí)間不算短的跟蹤閱讀者,她的詩(shī)集《錦瑟》也由我收入了“中國(guó)好詩(shī)”第二季。何向陽(yáng)的詩(shī)歌寫(xiě)作起步非常早,20世紀(jì)80年代的詩(shī)歌理想主義的光暈至今還在她的心靈深處閃耀。經(jīng)過(guò)時(shí)間并不短的休眠期,她的詩(shī)歌在十多年來(lái)迎來(lái)了近乎火山噴發(fā)的壯麗階段,當(dāng)然也是噴發(fā)和冷凝同步的過(guò)程。尤其是在死亡、疾病的強(qiáng)大精神境遇之下,她的詩(shī)歌從內(nèi)而發(fā),幾乎發(fā)生了重生、再造般的質(zhì)變,這也是我由衷致敬她作為詩(shī)人和生命體的重要理由。在很大程度上,詩(shī)歌成了何向陽(yáng)的特殊生命支撐物,甚至超越身體和物理層面的生命而成為不可替代的精神烏托邦和靈魂共時(shí)體。
何向陽(yáng)的詩(shī)歌越來(lái)越像是秋天深處的大湖,平靜、湛藍(lán)、澄澈,映照著人世的過(guò)往和未來(lái)的矚望,沉淀著人世的悲欣交集和內(nèi)心的愿念執(zhí)守。
一
接下來(lái),我們回到這首剛剛完成的小長(zhǎng)詩(shī)《碧色》。
“碧色”不由自主地讓我想到了遙遠(yuǎn)的云南紅河一隅的“碧色寨”,當(dāng)年我曾沿著滇越鐵路行走了幾十公里,甚至當(dāng)時(shí)還遇上了突然而至的暴雨。顯然,何向陽(yáng)的這首長(zhǎng)詩(shī)與“碧色寨”沒(méi)有任何精神關(guān)聯(lián),而只是她寫(xiě)作履歷和精神譜系上自覺(jué)延伸和深化的結(jié)果。
整首詩(shī)分為5個(gè)部分,每個(gè)部分由4首詩(shī)構(gòu)成。從語(yǔ)言方式、句型來(lái)看,這首詩(shī)仍然延續(xù)了何向陽(yáng)詩(shī)歌的一貫特點(diǎn),詩(shī)行較短、分行頻繁、語(yǔ)言素樸而節(jié)制。
碧色,為中國(guó)傳統(tǒng)色彩,屬于間色,一般是青綠色,有時(shí)也指青白色,“青雜乎白,白似足以掩青色,而卒不能掩,遂成碧色,非正色也。”(陳澧《公孫龍子注》)在何向陽(yáng)這里,藍(lán)或碧色代表了時(shí)間本體和生命歷程本身,“正如踉蹌后面"/"會(huì)是片刻停頓"/"那片藍(lán)"/"在激越后"/"呈現(xiàn)出難言的"/"平靜與"/"溫馨”。
詩(shī)的開(kāi)篇從“藍(lán)”和湖水開(kāi)始,也以它們貫穿始終,從而成為名副其實(shí)的深度意象。這讓我想到太姥山深處有一近乎隱秘的湖泊,每年八月的時(shí)候?yàn)蹊耆~子落在水中而凝聚成碧色,當(dāng)?shù)貗D女用此水來(lái)漚藍(lán)染衣,效果極佳。如果我們轉(zhuǎn)換一下視角和身份,如今是一位佇立湖邊的詩(shī)人,她用語(yǔ)言之水來(lái)漚藍(lán)、染色。無(wú)論是“藍(lán)”還是“碧色”,它們都已經(jīng)成為這一精神轉(zhuǎn)化過(guò)程中不可解的“天意”的一部分,你可以領(lǐng)受,但無(wú)權(quán)將之視為己物。因?yàn)椋谝粚右粚拥臅r(shí)間、空間構(gòu)造中,任何物象都只是短暫的表象聚集物,最終會(huì)渙散于無(wú)形及無(wú)時(shí)無(wú)地。我們所能做的就是說(shuō)出或保留這份“天意”與困惑,讓湖水之藍(lán)之碧色經(jīng)由詩(shī)人之眼成為幽深的淵藪,成為一份見(jiàn)證或幾聲回響也就足夠了。
沒(méi)有一種藍(lán)
能夠準(zhǔn)確說(shuō)出
它的比例
正如這湖水
張開(kāi)澄澈
你能描繪出
來(lái)自過(guò)往的
眼淚
是哪一滴
湖水平靜,而背后的塵世、城市正在沸騰喧囂,于反差中這片不可言說(shuō)的藍(lán)成為龐大而深徹的時(shí)間鏡像和命運(yùn)隱喻。無(wú)論是在一泓具體無(wú)二、真實(shí)不虛的湖水面前,還是在推而廣之的液態(tài)世界那里,詩(shī)人很容易成為多思善感的化身,而只有高度自覺(jué)和嚴(yán)格審視自我的人才能夠勘破表象背后的要旨和奧秘,“燕子并沒(méi)有認(rèn)出"/"眼前的詩(shī)人"/"她生活在倒影中"/"正是那碧色的陷阱"/"讓她無(wú)法停止"/"飛行”。實(shí)際上,詩(shī)人與燕子不存在任何本質(zhì)的不同。在永恒如斯、深迥如謎的宇宙、時(shí)空、碧色湖水面前,人與燕子同樣面對(duì)著各種形式的陷阱而又難以自拔地不自知,似乎只有旁觀者和局外人才能獲得短暫的清醒與啟示。
那么追問(wèn)也就來(lái)了,一代又一代的詩(shī)人為什么總是喜歡站在水邊凝視、沉思、寫(xiě)作?
一旦當(dāng)藍(lán)、碧色和湖水進(jìn)入詩(shī)人的視野,它們也就隨之被賦予了精神勢(shì)能與思想體量,一片水域勢(shì)必轉(zhuǎn)化為精神場(chǎng)域,一片水通過(guò)一滴滴的水完成心理分析。在臨水凝視的過(guò)程之中,詩(shī)人是要將自己融入到所見(jiàn)的物象之中,還是試圖將自己獨(dú)立并區(qū)別于這個(gè)世界?在我看來(lái),詩(shī)人的責(zé)任是既要了解這個(gè)世界,更要化解、和解這個(gè)世界,而這個(gè)世界又不是純?nèi)华?dú)立于主體之外的,主體仍然是這個(gè)世界的一部分。人、事、物、語(yǔ)之間并不存在純?nèi)坏慕缦蓿@完全取決于主體的位置、角度,以及心性、襟懷,詩(shī)人不是要重塑自然并對(duì)外物予以情志的格式化,詩(shī)人最終不一定要與自己和世界和解,因?yàn)樵?shī)正是自我爭(zhēng)辯的產(chǎn)物,“她必將這飛行"/"寫(xiě)入詩(shī)中"/"高樓獨(dú)上"/"湖水涌動(dòng)"/"陽(yáng)光下閃著白光"/"多日對(duì)談"/"她們已彼此了解"/"來(lái)自最深處的"/"澎湃與"/"鎮(zhèn)定”。
的確,水與詩(shī)人之間存在著天然的血緣關(guān)系,由此水與其他自然之物也就區(qū)別開(kāi)來(lái),成為人世中最為親近的靈魂伙伴。千百年來(lái),詩(shī)人幾乎保持了同一個(gè)經(jīng)典化的動(dòng)作,他們往往在水邊站立、凝望或者乘舟而游,他們與水之間建立起寓言般的精神刻度。水的詩(shī)學(xué)或液態(tài)的詩(shī)學(xué)由此生發(fā)并不斷擴(kuò)散。江河湖海等各種形態(tài)的水不只是自然之物,它們還對(duì)應(yīng)了變遷的社會(huì)文化史和人類的集體心理結(jié)構(gòu)。水猶如一個(gè)巨大的明亮鏡面,可以讓人在映照中看清自我,但它又是如此晦暗而充滿不可思議的吸力,那一個(gè)個(gè)浪花或漩渦帶有深不可測(cè)的令人心生畏懼的磁場(chǎng)。
二
此刻,何向陽(yáng)也再次站在了湖岸,凝視再次成為詩(shī)人的標(biāo)示性舉動(dòng),“她長(zhǎng)久長(zhǎng)久地"/"坐在長(zhǎng)廊"/"和靈魂一起"/"研究白皮松的形狀”。凝視是由己及物、由表及里的過(guò)程,甚至在長(zhǎng)時(shí)間的觀看過(guò)程之中事物會(huì)發(fā)生一定程度的變形。對(duì)于凝望水域的詩(shī)人而言,水已經(jīng)不再是液體,而是成為從最深處開(kāi)始的精神打撈過(guò)程。在凝望的過(guò)程之中,詩(shī)人主體也會(huì)發(fā)生分化,在與不在、此刻與往昔、此岸與彼岸、我與非我、靈魂與肉身、消失與重現(xiàn)、對(duì)視與獨(dú)立都時(shí)時(shí)地發(fā)生交匯或齟齬,“我既在這里"/"又不在這里"/"多少次"/"你經(jīng)歷著這樣的"/"靈肉分離”。
這一專屬性的凝視動(dòng)作,在詩(shī)人這里成為必然選擇,甚至?xí)⒛暤膶?duì)象發(fā)生一定的轉(zhuǎn)化和位移,但是凝視所牽涉的心理能量、精神指向是一致的,比如“她長(zhǎng)久長(zhǎng)久地"/"坐在長(zhǎng)廊"/"與靈魂一起"/"等一樹(shù)杏花開(kāi)放”。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反復(fù)出現(xiàn)的“長(zhǎng)廊”。“長(zhǎng)廊”處于一種面向空間、景觀的中介、過(guò)渡位置,它自身構(gòu)成相對(duì)獨(dú)立的觀望空間,繼續(xù)向前則是全然敞開(kāi)的外部空間,如果保持靜坐,它又成為相對(duì)封閉的精神原點(diǎn)式的存在。長(zhǎng)廊之上攀附的紫藤更像是神來(lái)之筆,為駐足、靜坐、觀望和凝視的人提供了一層極其清晰、生動(dòng)的表象景觀。“長(zhǎng)廊”這一特殊的觀望位置使得主體能夠在向外與向內(nèi)之間自由轉(zhuǎn)換,可以使凝視的動(dòng)作保持相對(duì)輕松的狀態(tài)。如果純?nèi)贿~入外部的空間,自我又很容易被那些物象所吸引或稀釋掉。
在很多情勢(shì)之下,詩(shī)歌成為凝視的產(chǎn)物。這一凝視的動(dòng)作和過(guò)程,并非單單指向了外在的可見(jiàn)之物,而是主觀情志對(duì)事物予以選擇之后深刻對(duì)應(yīng)了情感、心理、想象及終極考量的那一精深、幽微的部分。也即凝視是外在與內(nèi)在時(shí)時(shí)平衡的結(jié)果,萬(wàn)物的聲響與自我的呼吸彼此呼應(yīng)或者相互剝離。凝視,往往又指向自我及自我所攜帶的虛無(wú)。凝視不是為了喚醒永恒,而是為了喚醒短暫與消逝,“你卻說(shuō)不必"/"傷懷"/"一枚石子落入"/"湖心"/"這才是事物的本來(lái)"/"‘不斷地逝"/"猶如永久地生’”。這一勸慰指向的不是真理,而是好聽(tīng)的說(shuō)辭,實(shí)則又加深了疑問(wèn)與虛空。詩(shī)人通過(guò)凝視來(lái)接通一種不可言說(shuō)的語(yǔ)言,這不只是詩(shī)歌所達(dá)成的語(yǔ)言,而是超脫于萬(wàn)物之上又來(lái)自于自我的萬(wàn)古之聲。
在《碧色》這首長(zhǎng)詩(shī)中,何向陽(yáng)將以往抒情詩(shī)、女性詩(shī)歌中“我”的第一視角予以強(qiáng)力壓縮,代之以更具有間離、審視效果的“你”與“她”。由此,詩(shī)人既是主體也是客體,既是言說(shuō)者也是被描述者,既是觀望者也是被觀望者,戲劇性的繁復(fù)的精神場(chǎng)景也得以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來(lái)。
在“你”“她”“他”為主導(dǎo)的角色敘說(shuō)中詩(shī)人也意識(shí)到“我”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在全詩(shī)的第三部分——也就是中間部分,敘述主體的視角、重心發(fā)生重大轉(zhuǎn)換,“我”“我們”作為抒情主體的位置再一次被凸顯出來(lái),“我”一次次被“愛(ài)”所驅(qū)動(dòng),其中有渴念、發(fā)現(xiàn)及永恒的困惑,“那天我們散步"/"看一只鳥(niǎo)飛向云天"/"她似乎是從我的詩(shī)篇"/"復(fù)歸樹(shù)林"/"而不是相反"http://"我為這驚異的發(fā)現(xiàn)"/"緊攥你手"/"實(shí)際那手距我"/"尚一尺遙遠(yuǎn)"http://"一只鳥(niǎo)看著我們"/"兩個(gè)不知所措的"/"青年"/"只有她讀懂了"/"一切"http://"而一切的靜止與"/"不安"/"仍然左右于"/"他們中間”。
在何向陽(yáng)一次次的凝視、靜坐、散步之中,一種平靜而又顯豁的聲音從內(nèi)部升起,個(gè)體主體性也經(jīng)由這個(gè)主導(dǎo)性的聲音而轉(zhuǎn)為不斷觀照自我淵藪的鏡像或心象,“難道你沒(méi)聽(tīng)到"/"還是你沒(méi)看見(jiàn)"/"它在漸入黑暗的"/"深夜"/"以絕世的歌喉"/"發(fā)出鯨的"/"叫喊”。
值得注意的是詩(shī)人所發(fā)出的聲音,尤其是女性詩(shī)人所發(fā)出的聲音往往不能排除掉焦慮的成分,這一焦慮既是心理和生命層面的又是詞語(yǔ)和“元詩(shī)”層面的,所以鐘聲、夜鶯在詩(shī)里又獲得了重生,所以孤獨(dú)、回溯的視角也不可避免地在一次次加重,于兩手空空而凝視大湖之際,詩(shī)人要在詞語(yǔ)中建造一座花園或干凈的寺廟就成為必選項(xiàng)。
三
對(duì)于像何向陽(yáng)這樣有高度創(chuàng)作自覺(jué)的詩(shī)人而言,她總是在“詞與物”的掂量中發(fā)出不滿、疑慮或自我懷疑,“大部分時(shí)間"/"她在湖邊散步"/"燕子掠過(guò)湖面的一瞬"/"提示她獨(dú)屬于自己的句子"/"至今尚未寫(xiě)出”。
“獨(dú)屬于自己的句子”無(wú)論是對(duì)個(gè)體寫(xiě)作還是總體性的寫(xiě)作情勢(shì)來(lái)說(shuō),無(wú)疑具有不言自明的難度。“獨(dú)屬于自己”,無(wú)論是現(xiàn)實(shí)生活、精神境遇還是詩(shī)歌寫(xiě)作,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時(shí)刻。
圍繞著長(zhǎng)廊和湖水,以及其間穿插的燕子、天鵝、鴛鴦、鴨子、錦鯉、魚(yú)群、喜鵲、鷗鳥(niǎo)、白鷺、人工草地,詩(shī)人的視覺(jué)和聽(tīng)覺(jué)被一次次放大,它們變得異常精敏、幽細(xì)。與湖水所豢養(yǎng)的這些水禽和植物不同,詩(shī)人要經(jīng)由詞語(yǔ)重新構(gòu)建另一個(gè)空間,“她要在這樣的世界"/"寫(xiě)詩(shī)”。
她要在流動(dòng)的易逝的湖面之上寫(xiě)下凝恒的永不耗散的詩(shī)句,為液態(tài)的世界提供強(qiáng)有力的精神參照。
實(shí)則,長(zhǎng)廊和湖水只是詩(shī)人凝視的一部分或支撐物,而那些花朵、草木、動(dòng)物、場(chǎng)景都成為明心見(jiàn)性的生動(dòng)啟示。何向陽(yáng)在這首長(zhǎng)詩(shī)中似乎一直在尋求一種圓滿,肉身與精神的一致性,自我與本我的一致性,外在與內(nèi)在的一致性,“此生幸運(yùn)"/"花在我在"/"我和‘我’在一起"/"靈魂始終沒(méi)有將"/"肉身拋棄”。這首詩(shī)也就成為自我與自我對(duì)話、磋商、凝視、盤(pán)詰的產(chǎn)物,所有的聲音都可以歸結(jié)為自我的念頭,所有的物象都可以成為心象投射的顯影。
“大部分時(shí)間"/"她在湖邊散步”。在湖水面前,詩(shī)人很容易成為追懷者和自審者,讓一切與時(shí)間、過(guò)往、際遇有關(guān)的經(jīng)驗(yàn)、感受、想象被充分調(diào)動(dòng)起來(lái)。有時(shí)候一切都是沒(méi)有來(lái)由的,猶如生死這般的終極要義,此時(shí)一切語(yǔ)言都是虛空無(wú)力的,這時(shí)候詩(shī)人的責(zé)任就是讓事物自身直接顯示本我和意義,“正如你筆下的"/"這抹顏色"/"我無(wú)法為它的生成"/"與演變"/"講出來(lái)源”。
詩(shī)人只能一次次置身于實(shí)有與虛無(wú)博弈的浩嘆之中。
詩(shī)人凝視湖水,與此同時(shí),詩(shī)人也必將被湖水乃至萬(wàn)物所凝視。這是雙向往復(fù)的凝視,人與湖同時(shí)成為主體和客體,同時(shí)成為中心和參照物。既然凝視是雙向的、平等的,既然詩(shī)人處于這一凝視的法則之下,那么他自身的精神優(yōu)勢(shì)似乎就不那么顯豁了,甚至對(duì)于未知的繁雜世界來(lái)說(shuō),這一精神優(yōu)勢(shì)很容易被時(shí)間和空間同時(shí)擊敗于無(wú)形。所以,詩(shī)人要坦呈自己的限囿,認(rèn)識(shí)自我能力的邊界,這就顯得更為重要了,“讓我接過(guò)你的注視"/"照單全收"/"你贈(zèng)予的波瀾沉浮"/"沒(méi)有什么不能領(lǐng)受"/"所有的天意"/"都已備好”。
四
湖水也是天意的一部分,它對(duì)我們的注視或凝視似乎更為神秘而難解,由此它就形成了巨大的漩渦般的吸力。
大湖所帶給詩(shī)人的更多是精神的牽引和思想的沉淀,而這又往往容易成為凌空蹈虛或自我虛幻的精神閉環(huán)。試圖一次次起飛的詩(shī)人仍要回到地面和人間來(lái)。凝視的悖論在于物與我都處于短暫的此刻狀態(tài),“一閃而過(guò)”成為所有生命體的宿命,所以凝視在產(chǎn)生寧?kù)o、自省的同時(shí)也必然伴隨著焦慮與虛無(wú),最高的理想與現(xiàn)實(shí)的肉體之間的時(shí)時(shí)沖撞則處于這一焦慮與虛無(wú)的中心。如果詩(shī)人不能解決凝視所帶來(lái)的悖論與矛盾,詩(shī)歌也必將產(chǎn)生無(wú)可挽回的頹勢(shì),盡管詩(shī)人的責(zé)任并不是為這個(gè)世界提供答案,而更多的時(shí)候是提出疑問(wèn)。
答案有嗎?
我愛(ài)著的世界
是的""你身后
古人牌匾的字
難道不是一種
預(yù)知""或者
提醒
此時(shí)此刻,也是無(wú)時(shí)無(wú)地。為此,何向陽(yáng)又只能將自己一次次拉拽到滾沸的都市生活場(chǎng)景之中,不能對(duì)日常的摩擦系數(shù)熟視無(wú)睹。
當(dāng)平靜如斯的湖水替換為轟響的高速列車,當(dāng)割草機(jī)的轟鳴、咖啡的香氣及白皮松的枝干在詩(shī)人這里融合成為一種日常化的現(xiàn)實(shí)景觀,詩(shī)人才有可能經(jīng)由細(xì)節(jié)、場(chǎng)景重新激活那些象征性的分子和精神的飛地。
當(dāng)時(shí)間轉(zhuǎn)向凌晨三點(diǎn)的室內(nèi),一個(gè)失眠的人與不知名的夜鳥(niǎo)的啼鳴之間形成了深刻的精神呼應(yīng)。詩(shī)歌同樣是失眠的產(chǎn)物,猶如對(duì)湖水的凝視是另一種形式的失眠一樣。對(duì)于愛(ài)與怨怒,對(duì)于真實(shí)與虛無(wú),對(duì)于失眠與凝視,只有真正的歌者才能夠全然領(lǐng)受。就像扎加耶夫斯基所言:“讓我們愛(ài)上這個(gè)殘缺不全的世界吧!”
但是,詩(shī)人又不甘心停滯于浮土式的表象世界,因?yàn)樯钔鶑?fù)中所缺失的正是面前的這一片看似真實(shí)實(shí)則更接近于夢(mèng)境的湖水,以及無(wú)所不在的虛無(wú)、空落之感。
如露如電,夢(mèng)幻泡影,芥子須彌,萬(wàn)物空相,而我們又沒(méi)有任何選擇,除了肉身能夠證道之外,詞語(yǔ)和詩(shī)歌也是重要法門(mén)之一,“一個(gè)我坐在樹(shù)下"/"春天的花"/"落滿膝頭"/"她步入自己"/"提醒這實(shí)相的"/"虛無(wú)”。
凝視代表了想象的世界、自我的世界。正是經(jīng)由一滴滴的液態(tài)的藍(lán)、碧色,它們喚醒或重構(gòu)了自我世界及內(nèi)部的秘密。詩(shī)人需要在藍(lán)色水域的凝望之中打開(kāi)一道門(mén),即使這道門(mén)通向未知或虛無(wú),即使藍(lán)色的湖水充滿了雜質(zhì)和種種危險(xiǎn),關(guān)鍵所在是這一洞開(kāi)、凝視及深思猝臨的過(guò)程。
是的,在凝視中藍(lán)色的略顯憂郁的液態(tài)詩(shī)學(xué)得以誕生,這是——
誰(shuí)也奪不去的
澄碧
作者單位: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詩(shī)刊》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