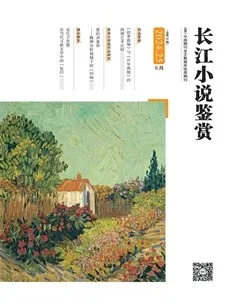愛的多重奏
[摘要]東西是一位高度關注人的生存狀態,書寫人的心靈歷程,表現時代情感的作家。其長篇小說《回響》(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融推理與情感為一體,由一樁兇殺案與女警察冉咚咚情感生活的纏繞,直擊人的心靈與本性,挖掘出時代洪流中各色各樣人物對愛的渴望、冷漠、猶疑、壓抑與堅守。本文從精神分析視域出發對小說《回響》進行解讀,通過對在本我、自我、超我間掙扎的缺愛者冉咚咚,肆意發泄本我欲望的變態追愛者徐山川、易春陽,努力秉持超我原則的守愛者慕達夫等人物形象的分析,探討當今時代復雜多樣的愛情,以及難以捉摸的隱秘人性。
[關鍵詞]東西" "《回響》" "精神分析" "愛與人性
[中圖分類號] I06" " "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25-0093-05
作為與畢飛宇、韓東、朱文等齊名的新生代作家,東西在繼承先鋒小說創新精神的同時,也不斷探索文學與現實人生的關系,注重小說的現實性與可讀性。他的寫作常常透過時代和日常生活的表面,去書寫人物深層的心靈,揭露當代社會中復雜的、難以捉摸的隱秘人性。繼《耳光響亮》《后悔錄》《篡改的命》后,東西創作了他的第四部長篇小說《回響》,小說以其縝密翔實的推理外殼下對當代人的情感拉扯、幽微人性與精神困境的出色書寫,榮獲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引起文壇的廣泛關注。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臧永清對《回響》給予了高度評價:“作者東西首先在藝術形式上進行了探索,他找到了一種‘怎樣寫’的方式,借鑒推理小說的某些形式,以一個案件的發生、偵查及推理作為敘事的內在動力,描繪了廣闊的當代社會生活,將自己對社會人心的敏銳觀察和深入思索藝術地納入嚴絲合縫的情節當中,形成一部邏輯嚴密、情節跌宕、讓人不忍釋卷同時發人深省的精彩紛呈的作品。”[1]
當下學界對于《回響》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三類。一類是基于敘事學的角度,對《回響》的文本美學以及敘事策略進行細致分析。如《論〈回響〉中的詩性隱喻構建》一文指出:“《回響》中的詩性隱喻并不局限于詩性的文學語言中,即在基礎隱喻上延展出來的新奇隱喻之外,還表現在語篇范圍內的敘事結構、人物形象構建和主題構建等范疇內的詩性隱喻上。這些具有篇章性特征的詩性隱喻構建實現了對閾限的突破和義域的跨越。”[2]另一類抓住“情感推理”和“時代精神”的關鍵詞,闡述《回響》映射的“現代都市社會典型心理鏡像”。如林芳毅在《偵探的戲仿與精神的寓言——論〈回響〉》一文中認為:“《回響》看似戲仿偵探小說的形式,實則是現代社會的精神寓言。”主人公“‘心靈偵探’冉咚咚與其說是在破案,不如說借助破案來證實她的直覺,試圖解剖荒誕生活的謎底,探索人性罪惡的根源,揭示出時代隱秘的心靈危機”[3]。第三類深度剖析小說中“各具個性立體鮮活的女性人物形象”[4]。如《東西〈回響〉中的女性群像》指出,《回響》中的女警察冉咚咚除了能力出眾、明察秋毫外,作為家庭中的妻子和母親,她是多疑的、偏執的,《回響》還展現了同樣具有人性矛盾的沈小迎與夏冰清等女性形象。
作為一篇心理分析氣息強烈的小說,《回響》對人的心理、意識及潛意識進行深入開掘,具有明顯的精神分析色彩。但根據現有的研究來看,從這一角度對文本的分析還遠遠不夠。本文基于精神分析理論,圍繞時代中愛與人性的主題,結合《回響》文本中形形色色的交織著愛恨情仇的人物形象,探求其背后潛藏著的當下世界里不同形式的愛與被愛,以及在各種不確定中搖擺的復雜而幽微的人性。
在弗洛伊德看來,“人的心理猶如大海中漂浮的冰山,露出海面的可見的是意識,隱沒在水面之下的大部分則是潛意識,潛意識是意識的基礎,決定著人的大部分行為。”[5]對于《回響》的創作,東西在后記中坦言這是一次更為徹底地有意識地對人物心理的努力開掘。“多年前寫《后悔錄》時,我就有意識地向人物內心開掘,并做過一些努力,但這一次我想做得更徹底。認知別人也許不那么難,而最難的是認知自己。”[6]小說中的人物在各種情感關系的交織中不斷地追問、質疑、迷失,在一次次的推理與被推理中認知自己。謀殺、懷疑、復仇、壓抑、糾結不安等行為和心理的背后,是他們心理深層對愛的記憶與態度。
一、在本我、自我、超我間掙扎的缺愛者——冉咚咚
1.本我的冉咚咚
在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論中,本我是一個人原始的潛意識的本能與欲望,遵循完全的快樂原則,不受道德規范和理性的約束。他認為“個體被我們稱為心理層面的本我,而這種本我不被人知曉,并且是無意識”[7]。在徐山川翻供,案件陷入僵局后,頂著辦案壓力的冉咚咚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不斷地問自己問題,忽然感受到自己深深的孤獨和委屈。“煩的時候沒人說話,累的時候沒有肩膀依靠,遇到困難時沒人分擔,全世界仿佛就她最可憐。”[6]想著想著她竟哭了出來,巨大的孤獨和無助感促使其心理崩潰,開始割腕。孤獨的冉咚咚身邊看似圍繞著關心她的父母、丈夫、女兒和同事,但她真正能感受到的愛卻是匱乏的,這促使她不斷追問慕達夫是否還愛自己,她想要確證屬于自己的愛是否還存在。她幻想的愛是一拍即合、心有靈犀、如影隨形、關懷備至,是一生一世一雙人,為此她的腦海中出現了初戀鄭志多的幻象。本我的冉咚咚害怕被拋棄在滿是孤獨的黑暗里,她渴望愛,期盼愛的光芒照亮她溫暖她,所以當她心靈深處缺失這份愛時,她會下意識地用割腕這種方式來釋放自己巨大的壓力和無助。在自己的感情生活中,冉咚咚自始至終都在不停地懷疑丈夫慕達夫,這份懷疑從她在調查中無意發現慕達夫的開房記錄開始。她不相信丈夫的種種解釋,固執地堅信自己的判斷,并將婚前婚后的慕達夫進行對比,認為對方遠不如之前誠實坦率。隨著女兒逐漸長大,冉咚咚“似乎把愛情給忘了,就像手機調至飛行模式,雖然開著機卻沒有信號”[6]。她不再那么關心慕達夫的一舉一動,對待兩人之間的情感也變得越發麻木,原有的愛正在慢慢歸于平淡,慢慢消散。她越來越不滿足于當下缺愛的婚姻狀態,潛意識中想要去追逐和開啟新的愛情,開始不自覺地注意到周圍新來的年輕同事邵天偉,甚至會在辦案的路上忽然想念起他來,忍不住回憶起兩人過往的點點滴滴。想到邵天偉在自己面前的臉紅,冉咚咚的心里會浮出一絲歡喜。看到邵天偉為自己準備的鮮花和打掃得一塵不染的辦公室,冉咚咚的心情頓時像初戀那般舒暢。最終,本我的冉咚咚毅然決然地選擇與慕達夫離婚,投入邵天偉的懷抱。
2.自我的冉咚咚
弗洛伊德認為,“自我是外部世界以知覺—意識系統為媒介直接影響本我,并導致本我發生改變的部分。”[7]“自我是在本我的沖動與實現本我的環境條件之間的沖突中得到發展一種心理組織,是本我與外界關系的調節者,遵循現實原則。”[5]自我受現實的驅動,一方面牽制著本我,一方面又受制于超我。從小就目睹過父親出軌的冉咚咚帶著不堪的童年陰影長大,冉母出于不傷害女兒的心理,一直選擇對冉咚咚隱瞞他們婚姻的貌合神離。可冉咚咚從開始就十分清楚父母間潛藏的矛盾,小時候的她害怕自己和母親被父親拋棄,長大后這種恐懼依舊扎根于她的心靈深處,她不想重蹈父母無愛的婚姻模式。向丈夫慕達夫提出離婚前的冉咚咚在自我層面中掙扎著,一方面她出于本能奮力追求理想主義的愛情,將自己的感情潔癖帶入婚姻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當發現自己與丈夫慕達夫之間的愛意漸漸消散時,她不自覺地開始放大日常生活中所察覺到的一絲一毫的不對勁,不停地懷疑和質問對方在感情里的純潔性。另一方面,受制于自我內心的情感道德和現實原則,冉咚咚下意識地認為是丈夫慕達夫的出軌造成了雙方婚姻的破裂。她并沒有意識到自己在這段感情里的過錯,也不愿相信是自己精神出軌在先,于是她選擇將責任轉移至對方身上。
3.超我的冉咚咚
“超我代表著人的心理結構中道德和倫理的一面,作為一種外在規范和權威嚴格控制著人的行為,使之符合社會期望的要求,是傳統價值觀和社會理想內化的結果。”[5]在弗洛伊德看來,“自我理想(超我)既是俄狄浦斯情結的延續,也是本我最強有力的沖動和最重要的力比多變化的表現,通過自我理想(超我)的建構,自我已經控制了俄狄浦斯情結,并同時使自己服從于本我。” [7]在偵破案件時,冉咚咚是睿智敏感、能力出眾、明察秋毫的女刑警,擁有維持人間正義的使命感。她在工作中看見了太多人性的惡,每天接觸的案件“不是出軌就是兇殺,不是偷情就是謀財害命,不是貪污就是養小三,不是騙別人就是騙老婆……”[6]這種不堪的現實沖擊和自我心中的道德感驅使冉咚咚產生守夜人心態,她害怕一閉上眼睛就有人作惡,以為只要自己醒著就能防止壞事發生。在審訊背叛家庭、游戲感情的徐山川時,冉咚咚自始至終都懷揣著對其極大的憤怒、厭惡與批判。在問話中,冉咚咚不斷地對徐山川進行道德審判,她一眼看出徐山川與夏冰清簽訂的合同中的不平等與歧視,難以壓制住內心升騰的怒火,質問對方:“你這么做,對得起老婆孩子嗎?”[6]盡管在破案之初冉咚咚并未掌握徐山川強奸的直接證據,但對于案件細枝末節的推理觀察、內心的道德感和對是非曲直的判斷使她不惜制造偽證詐出徐山川妄圖掩蓋的真相。在案件的最后,只有直接殺害夏冰清的患有間歇性精神錯亂的兇手易春陽承認了犯罪行為,這嚴重挑戰冉咚咚的道德底線以及她所理解的正義。于是她仍舊執著地處理案件尋求突破,最終將整場悲劇的始作俑者徐山川繩之以法。破了揪心已久的“大坑案”后,冉咚咚繼續回到自己紛雜的情感生活中。此時的她已經遵從本心與慕達夫離婚,和邵天偉相互表明心意,但面對即將到來的求婚,她的內心開始猶豫開始回避,她的腦海里閃過好幾個念頭:這樣做會不會傷害女兒?是慕達夫先背叛自己還是自己先背叛他?面對已經是前夫的慕達夫對自己一針見血的剖析,冉咚咚發現二人婚姻最終破裂的真相正是自己潛意識的精神出軌。在巨大的道德崩塌與審視下,冉咚咚“心里涌起一股對慕達夫的深深內疚”,這種內省同時引發她內心對慕達夫逐漸強大起來的疚愛,將小說引向一個不確定的結局。
在兇殺案和情感生活的雙向糾纏中,自我的冉咚咚在婚姻感情的淡薄期意識到其中的問題和自己對理想愛情的向往,但那時的她選擇冷漠地維持表面的和諧,并將所有的責任推給對方。本我的冉咚咚出于對工作壓力的掙脫和對童年陰影的逃避,選擇聽從自己內心的聲音,不顧慕達夫的挽留毅然決然地離婚,轉身追求自己憧憬的愛情和幸福。超我的冉咚咚一邊在工作中維持著堅守正義的女警官形象,一邊在發現自己精神出軌在先的真相后因自我道德的審視而生發出對慕達夫強烈的疚愛。縱觀整部小說,從偵破案件到偵破情感和婚姻,冉咚咚都在本我、自我與超我間不斷拉扯、撕裂、掙扎,也在其中不斷成長,不斷認識自己。
二、肆意發泄本我欲望的畸愛者——徐山川、易春陽
不同于在本我、自我、超我間掙扎的冉咚咚,小說中的徐山川和易春陽是釋放本我的典型。
1.以瘋狂占有女性來變態追愛的徐山川
徐山川是整起兇殺案的源頭,也是促使被害人夏冰清墜入深淵的始作俑者。在面試酒店管理員時,徐山川留意到年輕貌美的夏冰清,并故意使計淘汰她,趁其不服返回理論時強奸了她。事后因為害怕對方將自己告上法庭,打破原有的幸福生活,徐山川一方面迅速清理現場,銷毀證據,另一方面假意給予夏冰清結婚承諾,安撫她混亂的情緒。在威逼利誘下,夏冰清一步步踏入徐山川設計好的陷阱之中,成為自己原先最不齒的第三者。除了夏冰清外,徐山川還同時包養了小劉、小尹等多位情人。本我的他欺壓女性,游戲感情,對婚姻道德置若罔聞,以自我的欲望至上,將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多位女性的痛苦之上。在夏冰清的多番糾纏之下,為了維持自己穩定的生活,道貌岸然的徐山川竟萌生了想要假手他人殺掉夏冰清的念頭。在一環又一環的推動下,徐山川間接促成了夏冰清的死亡。在骨子里,徐山川是自卑的,他四肢瘦小,腦袋肥碩,其貌不揚。盡管渴望收獲愛,但他自知頂著這副樣貌和不修邊幅的性格,很難吸引到主動的愛。可是他有著數不盡的財富,于是他便用一捆捆的金錢開路,讓自己的周圍環繞著諸多年輕貌美的女性,以彌補他內心的自卑和空虛。最后,他甚至不惜違反法律,強制占有夏冰清,將其玩弄于股掌之間。變態畸形追愛的徐山川最終難免法律的制裁。
2.謀害他人生命以制造愛的幻象的易春陽
易春陽是直接謀害夏冰清的兇手。在偌大的西江市,他只是一個小小的進城務工者。不同于徐山川的富有,易春陽生活在社會的底層,為了得到一萬塊錢不惜去謀殺一個年輕的生命。易春陽出生于貧苦村莊的農民家庭,不僅感受不到父母的愛,還要在成長過程中遭受來自周圍同學的嘲諷與嫌棄。長期的缺愛竟讓他因為劉青幫他點煙的一個小小舉動感動不已,心甘情愿地加入這場謀殺案中。在現實生活中,易春陽遭受親情與愛情的雙重打擊,于是他躲入自己的精神世界,結合自己在少年和成人時期愛而不得的兩位女性的形象,虛構出美麗善良的謝淺草。想象中的謝淺草大方得體,有涵養并且從不歧視和嫌棄他,愛他甚至超過愛自己。易春陽通過這樣的方式來逃避截然不同的、殘酷的現實,制造一種自己周圍充滿愛的幻象。他極度缺乏愛,又極度渴望愛,所以在與缺了一只右手的吳淺草萌生感情后,他無比珍視并且發了瘋地維護這段感情。當缺失的右手成為感情推進的阻礙時,易春陽本我欲望的釋放從想象走到實施。他不惜觸犯法律的界限,剝奪他人的生命來補足自己渴望的愛。在本我控制下失去理智的易春陽眼里,他需要一只手,一只能給他帶來愛和溫暖的手,不管這只手是誰的,也不管采用怎樣的方式得到這只手。同樣是變態地追求愛,同樣是穿梭在茫茫人海中的自卑心靈,易春陽的境遇卻比徐山川凄慘痛苦得多。徐山川的周圍從不缺乏送上門來的女性,若是真心對待,也能被愛環繞,即便只是物質的虛浮的愛。但自始至終,易春陽都是空有一顆真心,從來都沒有機會感受真正的愛。
從受人嘲諷與漠視的社會底層到坐擁財富眾星捧月的上層,一個是進城出賣苦力勉強生活的農民工易春陽,一個是利用金錢玩弄欺壓各種女性的徐山川。面對自己內心深處的自卑與對愛的渴望,他們都不約而同地任由自己的本能欲望驅使,做出背離道德和法律的瘋狂行為。有人說不是所有的財富都能換來真愛,可捧著一顆真心就一定能迎來真愛嗎?當易春陽將象征著真心的詩集送給他心愛的吳淺草,得到的卻是“我不是不想愛你,是愛不起你”[6]的回答。物欲橫流的現代社會仿佛在人與人之間筑起了一道難以跨越的心墻,人們總是出于各種現實的考量選擇猶疑、冷漠與回避,戴上各色各樣的面具,愛的獲取變得越來越困難。什么是真正的愛?如何正確地獲得真正的愛?人們在不斷的追問和虛無的迷茫與壓抑中爆發。暗藏著畸形人性之惡的徐山川和易春陽所造成的慘案,不僅是現代人內心積蓄的情感危機的顯現,更是快節奏的時代與社會下被壓抑的人的悲劇。
三、努力秉持超我原則的守愛者——慕達夫
在弗洛伊德人格結構模型中,超我要求所有的一切都遵循理想化和道德化, 遵循至善原則和道德原則。作為小說中的男主人公,慕達夫在外是西江大學有名的文學系教授,在內是下得廚房的稱職丈夫和女兒心目中能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條的好父親。面對妻子冉咚咚的猜疑和追問,他始終認真思考和回答。面對作家貝貞的情感誘惑,他雖有微小的觸動,但始終堅持自己對婚姻的底線。面對冉咚咚一直詢問的“你還愛我嗎”,直到小說的結尾,他始終都是給予肯定的回答。他關心冉咚咚的心理狀況,會特意安排她去看心理醫生。他會整理好外出的行李,事無巨細地為兩人未出發的旅行做準備。他為了維系這段岌岌可危的婚姻做出了各種嘗試,不斷地找理由延后離婚的日期,最開始是以女兒喚雨的成長為理由,到后來以冉咚咚割腕的反常心理狀態影響破案為要挾,最后變成卑微的懇求。盡管最后慕達夫并沒能挽留住冉咚咚,但即使是在離婚獲得自由身后,他仍然沒有選擇和貝貞在一起,他依舊愛著冉咚咚,也相信他們有重歸于好的可能。
弗洛姆在《愛的藝術》一書中曾說:“愛情是一項積極的活動。如果我愛,我對所愛之人就抱有積極的態度。而且不限于對他(她)。因為如果我很懶散,而且不使自己處于一種清醒的、開放的和積極的持續狀態,我就不可能對所愛之人抱有積極的態度。愛的能力要求人全力以赴,要求人的清醒狀態和生命力的升華。”[8]在與妻子冉咚咚的婚姻中,慕達夫一面在冉咚咚辦案時細心地照顧好女兒的生活起居,打理整個家庭,免去冉咚咚的后顧之憂,一面耐心地對妻子一而再再而三的懷疑與質問做出合理的解釋。他清醒地剖析冉咚咚的心理,也剖析兩人的婚姻,并積極地為挽救婚姻作出相應的努力。作為堅守道德與愛的守護者,慕達夫傳遞了東西對現代社會愛的希望與憧憬,盡管出于復雜而真實的人性會有搖擺有遲疑,但有人仍舊選擇相信,選擇堅守。這也折射出當今時代的愛最真實最美好的另一面。
四、結語
“當主流世界日趨虛偽、冷漠和麻木的時候,東西讓我們看到,愛與同情,這些現代主流世界業已消失的情感,還保留在這些看不見、聽不到、說不出的邊緣人物的內心世界,還存活于邊緣世界。這是一個巨大的悖論,東西既讓我們看到了現實的殘酷,也讓我們看到了現實的希望。”[9]在《回響》中,無論是掙扎在本我、自我和超我間的冉咚咚,肆意發泄內心欲望的徐山川、易春陽,還是努力秉持愛情婚姻道德原則的慕達夫,他們本質上都渴望一份熱烈真實的愛,只是面對不同的人生處境,他們中有的選擇懷疑愛,有的選擇變態追愛,還有的選擇執著等待,堅持守愛。透過精神分析的視角,我們在小說中不僅看到了現代社會中各色各樣的人物內心深處的愛情觀,也發現了在情感糾葛中的現實人性和現代人所面臨的種種精神困境。盡管在這個快節奏的時代,我們或許都像冉咚咚一樣懷疑過愛,面對愛與被愛時總是猶豫不決,但真正的愛依舊存在,就像小說結尾慕達夫說出那個“愛”字一樣堅定。相信愛,懷揣著希望勇敢地全力以赴地去愛,這是東西對于愛的思考與回應,也是時代在我們情感與心靈間的回響。
參考文獻
[1] 本刊編輯部.東西長篇小說《回響》研討會紀要[J].南方文壇,2023(1).
[2] 林雪皎.論《回響》中的詩性隱喻構建[J].當代作家評論,2023(6).
[3] 林芳毅.偵探的戲仿與精神的寓言——論《回響》[J].小說評論,2022(1).
[4] 莫永俊.東西《回響》中的女性群像[J].文學教育(上),2022(8).
[5] 許燕.人格心理學[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6] 東西.回響[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
[7] 弗洛伊德.自我與本我[M].黃煒,譯.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21.
[8] 弗洛姆.愛的藝術[M]李健鳴,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
[9] 黃偉林.廣西多民族文學的共同發展[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特約編輯" 張"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