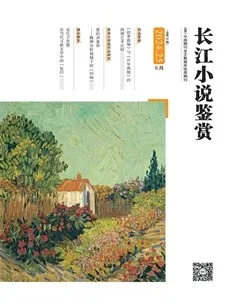彌賽亞時間與日常生活頌歌
[摘要]《我們的小鎮》是美國劇作家桑頓·懷爾德創作于20世紀30年代的劇本,從生活、愛情、死亡等方面展開格洛弗鎮平淡的日常生活畫面。然而,劇作絕不意在展現田園牧歌般的小鎮生活,其真正的主題深埋在對日常生活事無巨細的表現之下:作為一部敘述體戲劇,其中時間和空間隨意切換的敘述話語并不止于一種戲劇表現方式的革新,更是一種全新的解讀生命時間的共時性視角,引領我們走向生命的內在時間,看到彌賽亞時刻降臨的可能性。懷爾德取消情節,淡化戲劇性,采取種種“間離”手段,制造陌生化效果,力圖使讀者的注意力從表層的故事情節轉向深層的日常生活內核。《我們的小鎮》實質上是一首對日常生活的頌歌——千篇一律、平淡無奇的當下生活里才真正埋藏著救贖之地。
[關鍵詞]《我們的小鎮》" 日常生活" "彌賽亞時間" "共時性
[中圖分類號] I06" " "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25-0112-04
一、引入敘述元素 發現共時性狀態
《我們的小鎮》是一部戲劇式的現代寓言[1]。作為20世紀富有代表性的新文本,其最大的創新在于引入大量的敘述元素,以表演組織者(舞臺經理)承擔敘述性話語,從而對時空進行任意切換;以敘述代替動作,從戲劇性戲劇轉向非戲劇性戲劇。
舞臺經理在開篇介紹小鎮概況時,用了一個奇妙的時態:“大概五年之后這里才會有第一輛汽車。”[2]一句話便將三個時間點雜糅起來:處于過去的當下(舞臺經理說話的時刻),處于未來的過去(第一輛汽車出現的時刻),處于未來的更遠的未來(隱含的信息:更遠的以后出現了越來越多汽車),以時空的并置取消時間的歷時性狀態,引入共時性視角。這種共時性視角打破線性時間觀,取消因果關系,在傳統戲劇中按先后順序接連發生的情節變成日常生活畫面的片段式呈現。對此,斯叢狄在《現代戲劇理論》中評論道:《我們的小鎮》是“拒絕戲劇”的“敘事性戲劇”。其中舞臺經理的作用是解除“戲劇性的任務”,使“舞臺敘述替代戲劇情節”,“情節的各個部分不再像在戲劇中相互產生,而是根據一個超越單個時間的普遍性計劃,由敘事性自我來組合成一個整體”[1]。舞臺經理運用敘述元素,通過“面對觀眾介紹環境”和“面對角色進行互動”這兩大作用,傳遞出一種共時性的時空觀念。
首先是舞臺經理引出小鎮背景環境的介紹。對小鎮歷史背景、地理環境、文化氛圍等的敘述,有時以旁白形式穿插在對話與動作中間,但更多是以對話的方式占據主要內容。在歷史學家和報社編輯的介紹中,格洛弗鎮是沉悶無聊的——這是一座沒有任何新意和特色的小鎮。格洛弗鎮以最極致的普遍性成為所有小鎮的代表,這種代表所體現的是一種具體的個性,格洛弗小鎮中發生的一切在其他所有的小鎮發生過;也是一種抽象的共性,一種拆除時間和空間后的共性,這就賦予了小鎮和小鎮中的人和事一種寓言性質,同時也暗示觀眾,這些表層的信息并不是劇作家希望我們關注的重點。除了對話傳遞出的信息,對話的發生方式也十分值得關注:編輯韋伯先生在上臺之前被蘋果割到手、觀眾席的男子在詢問問題時被經理打斷——這兩出插曲目的在于塑造一種真實的日常生活細節,再加上舞臺經理拖沓的話語和對極端真實性不遺余力的渲染,實際是對極端形式的現實主義的一種反諷和解構[1]。觀眾對現實主義戲劇極端真實性的要求,根本目的是更好地沉浸于劇情的體驗之中,相信舞臺上的不是幻覺而是真相。然而懷爾德的這種解構態度意在對這種故事注意力進行拆解,將個性事件化為普遍的共時性視角下的時空。斯叢狄認為,劇作家對格洛弗鎮的介紹,是以“自然主義的意圖”,將“環境作為決定單個人存在的要素”在舞臺上展示,目的在于去除對白的客觀性[3]。盡管斯叢狄對懷爾德是否達到目的持一種否定態度,但不可否認的是,劇中對小鎮的描述絕非作為純粹的客觀背景進行介紹,而是試圖將格洛弗小鎮塑造成一個攜帶人跡的主體空間。小鎮不單單提供了事件發生的客觀場所,更是一個富有主體性的生命角色。
舞臺經理的另一個作用是與角色進行互動。舞臺經理可以肆意調度時空,他不僅可以控制整個舞臺的時空位置,還可以將死者帶回過去的空間。舞臺經理這一角色并不具有任何宗教因素——這種能力并不是神性所賦予的,而是一種理解和認識客觀世界的全新視角的折射:共時性。舞臺經理將生與死,過去、現在、未來并時而置,這種處理之下,生命已然不是因果相連、環環相扣的線性時間,而是以生命沖動和生命直覺構成的綿延。舞臺經理揭示出,所謂的過去、現在、未來,是一種外在于人自身的客觀對應物,而生命的真實狀態,是在混沌的共時性中完成的。在這種共時性中,線性時間沒有了意義,空間也不再區分主體和客體,呈現一種交融的狀態——小鎮與人們彼此相互構成,密不可分。
二、淡化戲劇性情節 重返日常生活現場
懷爾德對故事本身喪失興趣,是《我們的小鎮》淡化戲劇性情節的根本原因。劇中的一切情節僅僅是情節,而不傳遞任何主旨。
為了使得情節作為前景而不指涉真正的主題,懷爾德以這樣的方式消解戲劇性:在最開始就宣布一切人物的未來結局,通過“間離”破壞觀演的沉浸性,讓觀眾把注意力集中在情節背后的主題而不是情節本身上。例如介紹人物時,引出吉布斯醫生和太太后便緊接著宣布他們逝世的日期;報童喬·克羅威爾甫一出場,就立刻告知觀眾他最終的悲劇性結局:年輕有為的生命被戰爭無情地毀滅了。在“高懸的死亡幽靈下,格洛佛小鎮居民的日常生活獲得了一種莊嚴感”[2],如前所述,劇中的共時性視角為平面的日常生活增加了厚度,使其不陷落在感傷劇情的窠臼中。
棄絕故事情節表明懷爾德厭棄以大人物、大事件的古典式戲劇為代表的線性歷史觀下的美學,進而轉向現代主義范式下的日常生活美學——從日常生活中得到救贖。托多羅夫《日常生活的頌歌》中一段對日常生活的表述可進一步闡述這種轉向:
日常生活并不一定是愉悅的——這個道理誰人不知誰人不曉呢?而且,他經常是折磨人的:重復某些機械的動作,被不得不面對的煩惱壓得抬不起頭,僅僅為了維系生存——自己或親人的生存——就已精疲力竭。正是因此,我們才會那么向往夢想、逃避,才想要沉迷于英雄主義神秘主義,而所有這些支柱實際上都不是真實的。不應該拋棄日常生活(蔑視它,或將它扔給別人),而是從內部改變它,令它在意義和美的光照之下獲得重生。[4]
源起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論經歷了“異化”和“抵抗”兩個轉變。“異化”階段的日常生活理論將日常生活視作一種“對象化”“類本質”的生活狀態。以異化為支點,試圖通過日常生活的批判使主體和客體統一起來,從而克服或超越、消除異化的日常生活理論,“將日常生活看作主體和客體辯證的同一場所,批判目的是要恢復日常生活的主體性”。20世紀70年代以后,研究“抵抗”的日常生活理論逐漸興起,取代異化論成為主導范式。以“抵抗”為特征的日常生活理論主張不拋棄日常生活,而是以審美手段超越異化,如托多羅夫所說,“令它在意義和美的光照之下獲得重生”,從而救贖日常生活[5]。作為沉悶乏味日常生活的反面,英雄主義和神秘主義固然不可避免地使我們心生向往,但這絕不是救贖之地——這顯然不是生活的本真面目。只有直面真實,救贖才可能發生。實際上,對日常生活的興趣是一種倫理態度:承認最微不足道的甚至受譴責的行動也具有價值。看到了這一點,才能理解《我們的小鎮》真正的可貴之處——讓故事浮到表層,摒除道德訓誡,不從情節中尋找人為附加的教化意義,而是直面生活本身,還原生活本相。
因此,劇中的一切情節與道具沒有區別,僅僅起到一種工具性的作用,如幾張桌椅構成的布景一樣,作為背景存在著。真正作為主角在其間活動的是連綿不斷的日常生活細節,所貫穿的無意義的時間就是生命的救贖時刻——彌賽亞時間,但劇中人物無一例外地錯過了。這就是懷爾德真正想要向我們傳遞的日常生活美學。在日常生活的反復折疊中,《我們的小鎮》揭示出生命真正的美好存在于一種奇妙的共時性之中。
三、深埋的彌賽亞時間:作為內核和救贖之地
將情節的表層遮蔽去除后,我們將看到文本言說的真正主題——生活。“這部劇所講述的其實是一件大事:那就是生活本身。”[2]舞臺經理曾經點出了題旨:“你知道——巴比倫曾經有兩百萬人口,而我們所知道的全部,只是那些過往的名字,還有幾份關于小麥的契約……可是,每個晚上,那些家庭都會坐下來吃晚飯,父親會干完活回到家里,煙囪里會升起炊煙——就像這里一樣。甚至在希臘和羅馬,我們對那些居民的真實生活的了解,無外乎那些搜集到的打油詩和為當時劇場寫的喜劇。”“所以,我打算把這個劇的劇本放在一份奠基石里,千年以后的人們就會了解一些關于我們的基本情況……這就是當年我們的方式:我們就這樣成長、結婚和死亡。”[2]
《我們的小鎮》一共分為三幕:第一幕的主題是日常生活,第二幕的主題是愛情與婚姻,第三幕的主題是生與死。這部劇的高潮看似是在第三幕發生的,艾米麗穿越生死,回到過去,卻發現所有人對日常生活的真正美好之處無動于衷,直到得出一個悲劇性的宿命結論:我們對生活的美好感受永遠不能和真正生活的時刻同時存在。然而,《我們的小鎮》的核心其實在第一幕,對非對象化、類本質的日常生活的展開。送牛奶的男孩與醫生的交談、媽媽與孩子在早餐時分的對話,都是生活中不能再普通、不能再常見的場景。日常生活現身后,問題就在于:如何從日常生活中看到美呢?托多羅夫在《日常生活的頌歌》中給出了提示。
在托多羅夫看來,日常生活之所以被遮蔽,是因為對于效率的盲目追求。結果導向的生活使一切成為手段,因而我們眼中看到的只是最終目的,而沒有行進的過程本身,自然也就遠離了日常生活:我們的人生被機械的時間切割成段落,以重要的人生節點來標記生命時刻,正如艾米麗一開始選擇回到的場景是婚禮、生育等重要的記憶,其實是一種對人生重要坐標的選擇。隨后在眾亡魂的勸誡下,艾米麗選擇了一個相對而言沒有那么重要的時間點:12歲生日。重返過去后,她驚喜于小鎮舊日的模樣,驚喜于過去記憶的重新體驗,然而,艾米麗的欣喜若狂卻逐漸被失望和悲哀取代。時間不停歇地流逝著,母親專注于種種瑣事,這使艾米麗發現自己沒有辦法與母親完成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對話——“我們甚至沒有真正看一眼對方”。在失望之后,艾米麗動情地說:“再見,再見,世界。再見,格洛弗鎮……媽媽,爸爸。再見,我的鬧鐘……媽媽的太陽花。食物和咖啡。新熨好的衣服,還有熱水澡……睡覺和起床。哦,地球,你太美妙了,以至于無人能認識到你的好。”艾米麗終于意識到,原來生活真正使我們留戀的不是重大事件,而是重復又無聊的日常生活。
艾米麗的覺醒,實則是彌賽亞時刻的降臨。彌賽亞時間觀是本雅明針對線性時間觀提出來的另一種時間概念。在線性時間觀中,時間是斷裂的,記憶和經驗是本質組成部分。但這種歷史主義下的時間,其實并不與我們本真的生命經驗相聯系。本雅明在《歷史哲學論綱》中對歷史主義的線性時間觀進行了批判和重構。歷史主義的時間觀發源于早期基督教,在工業革命后,隨著自然科學的建立,歷史主義者基于線性的時間觀念,構建出一套在客觀上連續不斷進步的歷史進步論。這種進步史觀一方面埋葬過去的苦難,一方面對未來盲目樂觀,并且把救贖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后來者上。然而,這種線性的時間觀只是一種被建構出來的謊言。線性時間是同質的、空洞的、理性的,是外在于人自身的,并不是現實生活的真實狀態。基于對線性時間的否定,本雅明提出了彌賽亞時間。本雅明認識到,世界在本質上是一種整體性存在,人類所追尋的無限的永恒性存在就蘊含在現世和當下的時間中,是一種非斷裂性的救贖時間[6]。
但這種救贖時刻深埋在日常中,它埋得太深以至于無人能夠察覺。生者是如此盲目,在線性時間觀的支配下,我們不是回首過去就是仰望未來,殊不知最珍貴的東西就在當下的此間。吉布斯太太一直有去法國巴黎的心愿,“人這輩子應該在死前有此機會,去個不說英語,也不愛說英語的國家瞧瞧”,但始終沒有實現[2]。然而,這個心愿的真實面目不過是一個不需抵達的路標,而非吉布斯太太切身的渴望。巴黎就這樣作為一個遠方的目的地存在著,但不必向那里行走。吉布斯太太未完成的心愿是一出日常生活中隨處發生的淺淡的悲劇。吉布斯太太這種渴望遠離日常生活、向往異鄉生活經驗的心理,呈現出一種矛盾感:一方面她倦怠了現有的生活,不能從日常生活中得到在世的救贖,然而一方面也沒有充分的動力去遠方尋找救贖。巴黎只需要虛無縹緲地存在著——這就是它的全部意義。但是,在這種線性時間觀念的支配下,人生變成了一串點線相連的高速公路,從一個目的地到另一個目的地,從而使得真正的彌賽亞時間永遠無法降臨。因為生者永遠不曾知曉“人類苦心孤詣找尋的無限的永恒性存在就蘊藏在現實經驗世界和世俗歷史中”[6]。
那么,其中有誰得到救贖了?只有死去的人。艾米麗與舞臺經理的最終對話意味深長。“有沒有人在活著的時候,意識到生命的意義——每一分,每一秒?”“沒有。也許圣人和詩人會——他們能有一些認識。”[2]彌賽亞時刻的降臨,必須深耕于日常生活美學,從最平常的生活中發現偶然性,注意到“立即的、無詩意的、自身缺乏美的存在”。生命的真正意義就在這些平日里不被注意的細節之中。
四、結語
《我們的小鎮》毫無疑問是一首對于日常生活的頌歌。這種歌頌并不停留在表層的情節里,而是深入生活本身,對人的感知能力與生活世界的關系做出全新的思考。在帶有間離目的的敘事化改造下,情節成為不承載任何意義和目的的動作本身,只是單純作為畫面進行展示。在對線性時間的解構中,懷爾德試圖破壞一切在感性層面帶來的刻奇傾向,不遺余力地運用間離效果,希望觀眾的注意力能夠轉入更深的層面:對日常生活進行重新思考。懷爾德想要告訴我們的是:任何一個不被注意的日常生活時刻都是彌賽亞時間降臨的時刻。然而,正如艾米麗悲哀地發現,這個道理生者無法知曉,死者知曉但無可奈何。生活在當下的時刻,意識到此刻的每一瞬間都有救贖可能性的產生。在悖謬帶來的淡淡的悲劇感中,《我們的小鎮》深切地呼吁著人們對當下生活進行觀照,重新發現日常生活的美好和動人之處,從而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救贖。
參考文獻
[1] 但漢松,劉海平.現代寓言的舞臺呈現:重解桑頓·懷爾德的《我們的小鎮》[J].戲劇(中央戲劇學院學報),2011(1).
[2] 懷爾德.我們的小鎮[M].但漢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
[3] 斯叢狄.現代戲劇理論1880-1950[M].王建,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4] 托多羅夫.日常生活頌歌:論十七世紀荷蘭繪畫輕與重文叢[M].曹丹紅,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
[5] 張道建.異化與抵抗:西方“日常生活理論”的兩種路徑[J].湖北社會科學,2018(7).
[6] 郭廣.本雅明對歷史主義線性時間觀的批判與重構[J].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評論,2019(1).
[7] 本雅明.寫作與救贖:本雅明文選[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7.
(特約編輯" 張"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