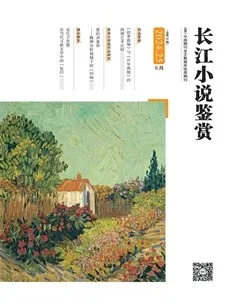尋找“自我”之途:空間批評下的《莫失莫忘》
[摘要]石黑一雄的《莫失莫忘》以克隆人為主角,講述了克隆人為人類捐獻器官直至死亡的悲劇故事。本文旨在運用福柯和列斐伏爾的空間批評理論,特別是列斐伏爾提出的空間“三元一體”概念以及福柯的“全景敞視主義”理論,深入剖析克隆人終其一生追尋自我身份的復雜歷程,以此揭示克隆人在科技高度發展的社會中所面臨的生存困境。小說描述了凱西、露絲和湯米三位主人公成長過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學校、村舍以及畫廊。通過描繪這些空間的地理特征及其對人物成長的影響,展現了三者對自我身份認知的持續變化過程。本文強調了空間批評理論在解析《莫失莫忘》中主人公尋找自我意義之旅中的重要性,綜合分析了克隆人的自我認知過程,同時揭示了空間與人物身份意識構建之間更深層次的內在聯系。
[關鍵詞]石黑一雄" "《莫失莫忘》" "空間批評" "身份意識
[中圖分類號] I06" " "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25-0079-06
一、引言
作為英國當代最成功的小說作家之一,石黑一雄近年來收獲了國際上的廣泛認可與贊譽,其作品已被翻譯成三十多種語言。他的《莫失莫忘》(2005)講述了克隆人被設計為器官捐贈者的故事,小說入圍了布克獎,并于2010年被改編成同名電影。讀者通過主人公凱西·H的視角,回溯了她和朋友露絲、湯米在黑爾舍姆、農舍和康復中心的經歷。黑爾舍姆是一所寄宿學校,在這里,克隆孩子像普通學生一樣接受教育。畢業后,他們被集體轉移至農舍度過近兩年的時光,待到成年之日,他們將在康復中心通過捐贈器官完成自己的“使命”。小說開篇即隱匿了這一殘酷真相,隨著故事的發展,越來越多關于學校的真相和他們的真實身份被揭示出來。
在《莫失莫忘》中,石黑一雄還通過人物角色探討了社會層面的問題。對于這些克隆孩子來說,器官捐贈是他們未來唯一被允許和應該做的事情。像其他孩子一樣,他們享受童年,接受教育。他們仿效人類行為模式,試圖像人類一樣生活。他們渴望身份的認同。但對人類來說,他們只是用來追求健康和長壽的工具。這一殘酷的現實,構筑了小說的悲劇基調。為什么克隆人不能被稱為人類,或者確切的人類是什么,這些問題很難回答。在科學技術的世界里,人類和非人類的問題必須被討論。這部小說是科幻小說和文學作品的結合,反映了未來生活可能的一部分,并提出了基因實驗和人類身份的道德問題。此外,強烈的存在主義主題對社會的激進變革提供了一個值得反思的研究領域。
在理論層面上,亨利·列斐伏爾的《空間的生產》為解讀《莫失莫忘》提供了新的視角。他提出的“空間的生產”概念,涵蓋了兩種含義:“空間中事物的生產”和“空間本身的生產”。列斐伏爾認為,隨著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和城市空間的迅速擴張,人類的生產方式已經從“生產空間中的物”轉向“生產空間本身”[1]。他批判了傳統空間觀的靜態性,強調空間能影響并塑造人類的思想和行為。而米歇爾·福柯的《規訓與懲罰》則進一步補充了空間如何對個體實施控制。這兩者的理論貢獻,為分析《莫失莫忘》中人物身份構建提供了理論依據。
二、不同空間中的身份問題
根據列斐伏爾的說法,“空間從來不是空的:它總是體現著一種意義”[1],因此,對物理空間的研究不僅要關注地理空間的表面描述,還要關注其所承載的象征意義。小說中有三個重要且具有代表性的空間:學校、農舍和畫廊。這三個空間對幾位克隆人的成長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本節將運用空間批評理論,特別是列斐伏爾的“三位一體”理論,探討人物從迷失到自我覺醒,再到最終身份確立的復雜過程。
1.學校
黑爾舍姆是一所寄宿學校,坐落在風景優美但相對與世隔絕的英國鄉村。凱西和她的朋友們在這里度過了看似愉快且與普通人無異的童年。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簡單:黑爾舍姆這所“學校”實則是克隆人的搖籃,看護者們用紀律來營造出烏托邦式的幻覺,讓學生們難以真正意識到自己的真實身份與來源,更無法解答“自己來自哪里以及自己到底是誰”的根本性問題。
1.1 作為空間表征的“監獄”式黑爾舍姆
為了將這些克隆人變成“馴服而有用的身體”,“學校”采用了三種方法:監視、檢查和評價。規訓是福柯權力理論的一個重要術語。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闡述,許多現代機構都是為了規范人類,將人類塑造為“馴服的身體”而設計的[2]。這與列斐伏爾的“空間表征”理念相吻合,即概念化空間的輸出,因為黑爾舍姆作為一所“學校”,人類可以在身體和心理上控制克隆孩子。規訓首先是通過嚴格的監督來實現。黑爾舍姆的布局設計借鑒了英國哲學家杰里米·邊沁所提出的“圓形監獄”(Panopticon)概念,其核心是一座中心控制塔,即學校的主要建筑物。此塔被呈環形排列的監舍所環繞,使得居于中心控制塔內的管理人員能夠輕松觀察到監舍內的所有活動,有效防止了任何逃脫行為。這一設計理念解釋了為何在黑爾舍姆,盡管存在眾多隱蔽角落,克隆孩子卻總是難以逃脫監護人的監視,他們甚至錯誤地認為監護人擁有某種心靈感應的能力。他們由于無法確定自己是否處于被監控狀態,以及何時會受到監控,這種不確定性使得他們心理上始終處于被監視的緊張狀態,從而不敢隨意行事,達到了一種“自我禁錮”的效果。
規訓的第二種手段是檢查,它“整合了權力的儀式、實驗的形式、武力的部署、真理的確立,并顯示了被視為對象的人的征服和客觀化”[2]。為了確保未來器官移植手術的成功率,克隆孩子的健康狀況被視為優先關注的重點。因此,他們需要定期進行體檢,頻率達到每周一次。此外,監護人對于吸煙行為持有極為嚴格的態度。圖書館的藏書中,并未收錄諸如《夏洛克·福爾摩斯》等經典小說,其主要原因是這些作品中的主角頻繁吸煙,而且書籍和雜志中含有的吸煙圖片與插圖已被系統性地清除,以減少不良示范效應[3]。與此同時,“創造力”受到了極度重視,原因在于它成為學校檢驗克隆人是否具有“靈魂”的關鍵途徑。若個人的繪畫、素描、陶藝或詩歌作品得到了認可,甚至榮登“畫廊”,這將被視作極高的榮譽[3]。這種蘊含獎懲機制的審查過程,實則是對他們進行重新塑造與訓練的過程,旨在實現思想和行為上的引導與規范[4]。
第三種規訓手段是評價。首席監護人往往不會采取過于嚴苛的措施,然而,她的每一個舉止都足以令學生們心生畏懼。如果不慎觸怒了她,或是得知她對你的評價有所降低,你會感到深深的失落,并急于尋求改正。這種懲罰方式雖非直接的肉體懲罰,卻能在他們的心靈層面產生深遠的影響。
1.2 空間表征中的身份意識喪失
克隆人的身份喪失,首先明顯地體現在他們的命名上,如Graham K、Reggie D、Arthur H、Alexander J等。這些名字如同流水線產品上的序列號,字母組合成了他們的標識,更有甚者,有些人甚至擁有相同的姓氏,這不禁讓人揣測他們是否屬于同一批“制造”的克隆人。然而,這些孩子從未像正常小孩那樣對自己如何存在于這個世界而感到好奇。在黑爾舍姆的權力結構影響下,他們似乎徹底喪失了自我認知。
此外,黑爾舍姆還會模仿外部社會開展一系列活動,但這些活動的目的是鞏固克隆人的附屬地位。舉例來說,學校設立了一個特殊班級,要求學生扮演各種職業角色,比如服務員、警察等,以便讓他們體驗和學習。然而,這些角色只限于服務行業或維護社會秩序的領域,這種安排無形中強化了他們為社會服務的觀念。學校也會定期進行拍賣活動,但諷刺的是,學生們視為珍寶的藏品不過是外界普通人丟棄的垃圾[3]。按照列斐伏爾的說法,空間“……不僅是權威的控制機器,也是沒有特權的人的防御工具”[1]。在業余時間,他們受到監護者和在這個空間內制定的無形規則的控制。克隆人經常“被告知或不被告知”,因此他們過著一種看似無憂無慮,從不考慮自己身份的生活。正如凱西所說:“我們正處在一個對自己有一點了解的年齡,我們是誰,我們與我們的監護人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但我們不知道這意味著什么。”[3]
2.農舍
農舍,作為學生們離開黑爾舍姆后首個抵達的地方,它不僅承載了他們從學校到外界的過渡,更成為連接黑爾舍姆與外部社會的紐帶。這里匯聚了來自黑爾舍姆的畢業生以及其他地方的年輕人,凱西與幾位密友便是在此度過了他們的青春歲月。對他們而言,這里宛如一個縮影,映射出外部世界的輪廓。正是在這個空間中的實踐經歷,讓幾個主人公開始敏銳地意識自己的身份問題。在這個共同生活的空間里,他們通過日常的點滴交流,逐漸感知到與他人的不同之處,并由此激發了探索“自己是誰”的強烈愿望。
2.1作為空間實踐的半開放性農舍
列斐伏爾在《空間的生產》中指出:“人物的內心世界為空間的實踐想象了各種新的意義和可能性。”[1]精神空間,作為心理與話語的交互場域,承載著邏輯性和形式化的抽象概念。文學作品通過具象化人物的心理狀態和意識形態,使得這些概念得以具象表達。起初,克隆孩子受限于黑爾舍姆灌輸的思想和行為模式,但在農舍里接觸到更多人后,他們逐漸開始“發現”自己。
克隆孩子被人類刻意安置在遠離人類社會、近乎與世隔絕的農舍里。從凱西的敘述來看,這些小屋“(看起來)美麗而舒適,到處都是雜草叢生的草,對我們來說是一種新奇的東西”[5]。隨處可見的雜草表明這些小屋離人類居住區很遠。因為農舍位置偏遠,所以農舍的主人每周只來這里兩到三次[3]。他駕駛的那輛滿是泥濘的貨車也進一步印證了農舍坐落在一個偏遠而崎嶇的地區。更重要的是,除凱弗斯外,再無人類出現在這里,這一點凸顯了農舍的隔離狀態。不同于黑爾舍姆對克隆孩子的嚴格管控,在農舍,他們體驗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可以走出小屋,與外界接觸。然而,由于農舍地處偏僻,與人類社區相距甚遠,克隆孩子若欲外出,必須一大早就離開他們的生活場所,以確保有充足的時間在外逗留。有一次,露絲、凱西、湯米和兩個老兵去諾福克尋找露絲所謂的“可能”,五人于黎明前出發,直至午餐時分才到達目的地。由此可見,克隆孩子是被人類有意安排在遠離人類居住區的農舍。
在農舍中,克隆孩子也被無形地監視著。對他們來說,大部分時間都被束縛在農舍內,鮮少外出。即便他們離開,也必須確保在凱弗斯的登記冊指定的日期和時間前返回[3]。因此,當克隆孩子前往諾福克時,他們必須早早出門,以確保能在日落前歸來,并及時在登記冊上簽到。登記冊記錄了他們出入農舍的時間,這反映出即使身處半開放環境,克隆孩子仍處于某種隱蔽力量的監視之下。不僅如此,克隆孩子之間也會互相監視。凱西的新朋友克麗絲指出,“在農舍后面”不可能進行秘密談話,因為“(每個人)總是在偷聽”[3]。農舍的存在,實質上延伸了黑爾舍姆學校所構建的“圓形監獄”體系。克隆孩子不僅要面對隱形的監控,還要承受同伴的監視。所有的監視手段在某種程度上不斷提醒著克隆孩子所肩負的人類安排下的義務。他們理應留守此地,靜候成為照顧者或捐贈者的召喚。因此,農舍的隱形監控機制也推動了捐贈計劃的實施。
此外,這些簡陋的農舍也迫使克隆孩子不得不服從人類的意志。這些小屋是數年前一個廢棄農場遺留下來的建筑,其中包含一座年代久遠的主屋,以及周邊的谷倉、外屋、馬廄等,共同構成了克隆孩子的居住空間。克隆孩子在農舍中的居住條件非常簡陋。更糟糕的是,除了夏季,整座農舍都非常寒冷。根據凱西的敘述,他們出門的時候即使穿上兩三條牛仔褲,還是覺得很冷。由于這種嚴寒的環境,他們不得不蜷縮在老舊的窗簾下,甚至是地毯下進行取暖。有時天氣過于寒冷,他們只得將所有可用之物堆疊其上以御寒。“雖然農舍里有大型的加熱器,但克隆人必須依靠能帶來煤氣罐的凱弗斯來使加熱器運轉起來。”根據凱西的回憶,“我們一直要求他給我們留下大量的供應,但他總是沮喪地搖著頭,好像我們一定會輕率地用完它們。”[3]只有當天氣變得越來越冷的時候,凱弗斯才會同意給克隆孩子一個裝錢的信封。于是,克隆孩子可以用這筆錢購買煤氣罐,確保加熱器正常工作。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克隆人在農舍中的生活條件惡劣。他們沒有獨立的經濟來源,因而只能仰賴人類援助維生。為了繼續生存,他們必須順從人類的意志。
2.2 空間實踐中的身份意識覺醒
在這個半開放的空間內,階級的劃分并非基于權力地位,而是依據群體間生活方式的差異。當凱西與朋友們初抵農舍時,很快便察覺到他們的習慣與其他人非常不同。為了融入這個群體,克隆孩子便有意識地效仿這些人的行為。露絲觀察到,“這些夫婦在公共場合從不做任何讓人覺得炫耀的事情,而是以一種合理的方式,就像正常家庭中的父母一樣”[3],因此,她改“用指關節的背面輕輕地拍一下伴侶的胳膊,靠近肘部”[6]的親昵方式,代替了在黑爾舍姆習得的親密表達。然而,凱西觀察到,這些人也會通過電視節目學習和復制一些行為模式,他們頻繁引用的口頭禪“上帝幫助我們”源自一部美國電視劇。此外,從夫妻間的非語言交流、同坐沙發的姿勢,到他們爭執與離開房間的方式,無不體現出他們對電視或電影場景的模仿。
凱西逐步意識到她與其他人之間的不同,并開始認識到她的獨特存在意義。她認為露西的行為轉變,是后者試圖掙脫在黑爾舍姆形成的自我形象的嘗試。在經歷了身份認同的危機后,克隆孩子展現出他們正在建立身份認同,并試圖通過放棄過去的身份標識來更好地適應新環境。他們通過模仿他人來確認自己的身份和歸屬,這反映出他們渴望融入外部世界的強烈愿望。在缺乏外部參照的情況下,自我認知難以自發形成,因為自我身份的構建是在與外界互動中逐步形成的。盡管農舍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覺醒自我意識的環境,但他們在不經意間模仿他人的行為,暴露出他們在自主思考和內在行為模式上的欠缺。他們的語言、動作和交流方式均是通過間接學習獲得的。自我認知的缺失驅使克隆孩子踏上了探索身份的征途。大多數克隆孩子相信,既然他們各自是從某個正常人類的原型克隆出來的,那么這些原型一定存在于世界某處。只要找到自己的“原型”,就能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真實存在,甚至有可能預測自己未來的發展方向。然而,當追尋未果后,露絲說出了深埋心底的話:“我們都知道這一點,我們是模仿社會渣滓創造的。吸毒者、妓女、酒鬼、流浪漢……如果你想要找到原型,那就去陰溝里、垃圾桶里找找吧。”
在追尋自己的夢想破滅后,露絲意識到自己出生于“社會底層人口”或“物質底層廢物”中,這讓她陷入絕望。因此,她和同伴們明白了在人類社會中,他們并未得到認可,且社會地位低下。盡管凱西表面上對“原型論”持懷疑態度,但她私下里仍會在色情雜志上尋找自己的“原型”,企圖借此解釋她內心深處涌現的強烈性欲。這正符合了列斐伏爾的空間實踐理論。人類本身是邊界模糊、缺乏完整性的存在。在構建自我身份時,人們需要在與內在“自我”的偏離中尋覓,借由外界的映像來彌補對完整性的想象。然而,當人類將克隆人明確地界定為物品、廢棄物、服務的客體時,克隆人便無法在與人類的相似性中找到歸屬和認同,“仿佛你每天經過的鏡子里,突然映照出的是一件令人不安和陌生的物體”。
3.畫廊
畫廊,作為想象的、象征性的表征空間,是克隆人沒有見過,甚至對其心存疑慮的地方,但這里卻成為他們確立自我身份、寄寓生活憧憬的舞臺。
3.1 作為表征空間的幻想畫廊
在真相大白之前,克隆孩子都認為,感情深厚的情侶或夫妻可以通過將作品提交至畫廊,以此作為證明,從而贏得延期捐贈器官的機會,延長享受世界的期限。起初,畫廊被視為對他們創造力的最高褒獎,然而,當凱西重遇昔日黑爾舍姆的管理員時,她得知所謂的“畫廊”只不過是一個廢棄的“黑暗之地”,布滿“蜘蛛網的痕跡”,也就是說,根本沒有畫廊。空間的幻象破滅,象征著對延遲捐贈美夢的徹底粉碎。
3.2 表征空間中自我身份的確立
事實是,管理員收集克隆孩子作品的初衷在于她認為這些創作能揭示他們的靈魂本質,或者說,她意在證實克隆人同樣擁有靈魂。“我們對整個捐贈過程提出了質疑。最重要的是,我們向世界表明,如果學生在一個人道和文明的環境中長大,他們就有潛力成長為有思想和聰明的人,就像任何普通的人類成員一樣。”[3]但這個世界充斥著冷漠,人們最關心的是治愈癌癥,許多人拒絕承認克隆人為“生命體”。凱西和湯米終于明白了他們是為器官捐贈而生的克隆人,注定無法被外界所接受。在一次簡單的發泄和一段時間的憤怒之后,凱西和湯米各自踏上了屬于自己的人生旅程。
經歷了無數克隆生命輪回的凱西,終于在心靈深處找到了救贖。在這個獨特的表征空間中,她成功塑造了自己的身份,并領悟到了自身存在的深遠意義。“一個好的照看者可以對捐贈者的生活產生很大的影響。”[3]凱西堅信,盡管湯米已經不再需要她,但新生的“克隆人”還需要她的關懷,這種無私的精神激勵著她繼續前行。如果說露絲及其他克隆人的死亡揭示了無知之死,那么湯米和凱西在了解所有真相后,選擇堅守使命而非逃避,則是他們成熟蛻變的標志,象征著他們已經放下過往,勇敢地承擔起自己的責任。這群“工具人”面對死亡的態度,從最初的恐懼演變為一種平和的接納。伴隨著友誼與愛的力量,他們之間的關系愈發緊密無間。他們相互扶持,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小說的最后,凱西站在一大片耕地的邊緣,平靜地迎接即將來臨的捐贈任務,她沒有哭泣,也沒有失控,只是稍作停留,隨后轉身返回車內,加速駛向人生的終點站。
三、結語
《莫失莫忘》作為石黑一雄的代表作之一,細膩描繪了克隆人的成長歷程。黑爾舍姆、農舍與畫廊,這些地點見證了凱西等人的人生軌跡及其記憶,映射出一條艱辛的自我身份探尋之旅。從空間的角度剖析這部作品,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穎的視角,去理解三位主角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探尋“自我”。
空間不僅是人類活動的領域,更是敘事構成的不可或缺的要素。根據萊文的說法:“不僅僅是我們吃什么,還包括我們所看到的和我們走過的房間。我們的感覺適應我們居住的空間,就像我們改變我們居住的空間一樣。”[5]空間塑造了在這個空間里的人。同時,人們通過在空間中的生活經歷認識自我。因此,解讀人與空間的關系,能夠為我們審視身份提供別樣的視角。
顯然,空間在凱西、湯米與露絲的生活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學校、農舍和畫廊,這些空間與時間交織在一起,給他們一種歸屬感,勾勒出他們的生存狀態,決定他們的存在方式。本文首先解析了黑爾舍姆寄宿學校的空間特性。其地理景觀籠罩在神秘的氛圍中,很少有人進出這個相對封閉的地方。全體克隆孩子都在監護人的監視之下。正如福柯在邊沁的“圓形監獄”概念上提出的“全景敞視主義”和列斐伏爾所說的“空間表征”。福柯的全景敞視主義理論認為,圓形監獄的設計使得中心的監視者可以無死角地觀察到所有囚犯,而囚犯卻無法確定自己何時被觀察,這種不對稱的監視機制導致了一種自我規訓的現象。
教育的目的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啟蒙,而是為了約束克隆孩子的行為。對孩子們來說,黑爾舍姆的回憶是甜蜜的,但這一切源于他們無知。潛藏于空間下的監視機制,令他們對自己到底是誰一無所知,只能遵從監護人的命令。隨后,本文探討了農舍的空間屬性。相較于學校,農舍的建筑與設施都很破舊,但克隆孩子在那里得到了更多的自由。盡管最初很不習慣,但他們不久便可以開車到處轉了。事實上,克隆人仍然處于隱藏力量的控制之下,因為如果他們想出去,必須得到簽字同意。正是在這樣的空間中,孩子們開始意識到自己是特殊的,于是積極地尋求“自我”,這符合列斐伏爾對空間實踐的定義。在經歷了許多事情之后,凱西和湯米形成了自己的想法。第一次得知自己只是克隆人的殘酷現實,以及無法過上正常人生活的事實,令他們對“畫廊”所象征的真相倍感痛苦。在了解了最終的無形表征空間后,凱西和湯米對自己有了全面的認識,不再將自己與其他克隆體或“正常”聯系起來定義自己。在那之后,湯米繼續踐行自己的“使命”,而凱西則知道了什么是愛,什么是死亡,她變得忠于自我。在小說的結尾,即使心中悲痛,她也沒有停下腳步,重新確立了自己的身份。
綜上所述,小說一方面揭示了生物技術濫用與異常文化機制引發的身份危機,以及對倫理缺失和人類異化的批判。克隆人作為悲劇的承載者,遭受主流社會的排斥,致力于尋找自我價值,以期獲得社會的認可。另一方面,作品展現了作者對邊緣化群體的深切同情。作者頻繁在不同文化間穿梭,這導致他的身份碎片化,歸屬感缺失。通過小說創作,作者成功地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中為這一群體發聲,生動描繪了該群體共同承受的創傷記憶與不懈探索。
參考文獻
[1] Lefebvre H.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Blackwell,1991.
[2] Foucault M.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M].New York:Vintage,1979.
[3] Ishiguro K.Never Let Me Go[M]. London:Vintage Books,2005.
[4] 谷偉. 漚浮泡影——略論《千萬別棄我而去》中“黑爾舍姆”的體制悖論[J]. 外國文學,2010(5).
[5] Toker L,Chertoff D.Reader Response and the Recycling of Topoi in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J].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2008,6(1).
[6] Semelak M. The Suffering of Existence in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J]. Ars Aeterna,2018,10(2).
(責任編輯" 余" "柳)